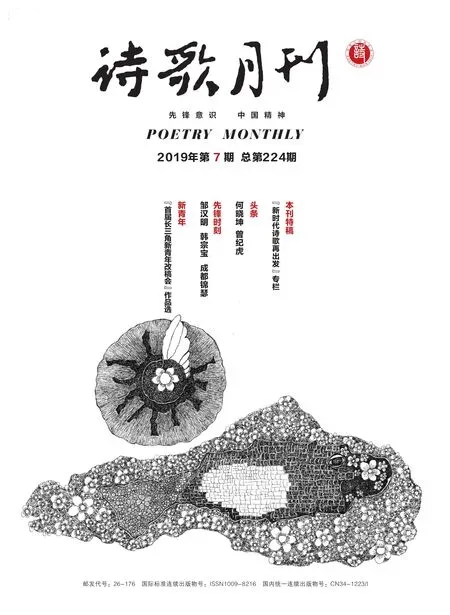陆闵的诗
陆闵
烟
冬天的麦田,燃起了大火
伐木工人走后的树林
散落着木屑。如今春天到来
我与亲人一起苏醒
在这个有雾的早晨,母亲熬着白粥
父亲带我回到那片树林里
我们种下树苗,也带走躺在
地上的黑色树枝
想起我们曾经燃起的篝火
伐木过后的夜晚,工人们与父亲
清算账目。我躺在母亲的怀里
看着远处的麦田
那些因风吹而闪烁的火星
同我一起,渐渐地睡去
雨后
草叶低垂的黄昏,雨早已停了
我们在屋檐下闲坐
面前是偶尔滚下的水珠,一次次地
碎给我们
说起天气尚好的时候,清晨与夜晚
露珠结得圆润,我们玻璃球样的眼睛里
嵌着一枚黑色的太阳
那时候,日子黑了又白,大片的云朵
来回穿行。我们从不知道
水珠的脆弱,更不知道
天空阴郁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会如此灰暗
抚慰
暴雨夜,我们放弃目的
将车停在一棵树下,并拨停了那对
烦人的雨刷器
调整靠背到半躺的程度
眼睛恰好看到顶窗。数着
黑色的雨点落下,渐渐从疲惫中缓过来
于是更多的声音涌入耳朵
闭上眼,从一滴雨往回听,是叶子的
晃动,枝干的低垂
一捧树冠正承受着阴沉的天空
它发出沙沙声
车窗上雾气凝成水滴
使我们很快地睡去
话别
我们在河中的倒影,含糊的
语言,过了此夜
就会变成岸边白墙上的一道污迹
而不久之后粉刷工人会
临河支起梯子。过路人只敢远远地观望
整个过程,危险而具有观赏性
取代
抽丝剥茧之后,布娃娃
白色的内心,散落在我的床上
这是我搬到你身边居住的
第一天。它目光呆滞,侧身躺在我怀里
我花一整天的时间陪它
看着窗外,下雨或者天晴
飞鸟振翅,抑或是垂垂老去。假如
你再不来敲响我的房门
我还要花另外一天的时间
和它订婚,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
在入睡前,把黏在我身上的棉花
塞回它的身体里
雨天随想
持续的雨水使整个地铁站陷入黏湿
袋鼠样的妇人把孩子抱在胸前
伸脚探向下楼的台阶
而与她相反的
是两头年迈的母熊和一只牙签鸟
他们并行而上,母熊肥胖缓慢
而牙签鸟——电话那头的鳄鱼会不会
又驳回他生计的请求呢
小袋鼠开始哭了
周围的荒原下着雨,包围着他的
长直的野草左摇右摆。我这头长颈鹿
不再左右打量,低下脖子
看着他
邀请函
这是我的城市
凌晨也不会熄灭的台灯
若有机会,请到这光中相见
面孔模糊
身后逐渐演变成黑色
我们可以沉默
也可以谈论与光有关的事
我的城市偏爱这些言语
香烟抽出的声音
风吹窗户,月色的响动
都会让它突然地扩大光芒
一个人的时候
我无法把握它会扩大到哪里
一句诗,让我看见鼹鼠钻回了洞穴
自我安慰一声,又看见
从树上跳下来的野猫
若是你来了
我们可以沉默,专心于辨认彼此
也可以为各自的光
无休止地争论
我的城市。如此善变的台灯
还没有找到自己
它只是照着我,日复一日地照着
一张模糊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