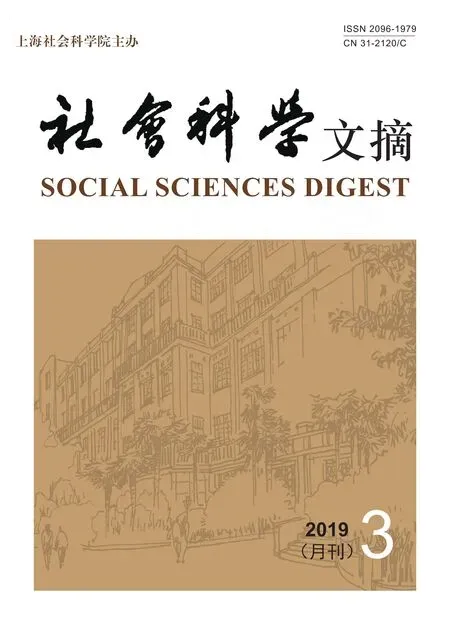刍议文化身份在当代法国流散文学中的表征
自20世纪全球化发展以来,民族文化身份逐渐淡化、世界文化身份不断强化,文化身份研究渐次成为后现代理论研究的显学之一。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一个文化群体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归属的标志及生存的依赖。“流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是指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创作,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呈现分裂、多维状态。流散作家既能在新居住国文化与原生地本土文化两者之间展开文学对话交流,同时又能在居住国内从“异域”的角度、以原生地本土文学作家的身份而创作文学作品。
审视当代法国文学,法国流散文学作家是怎样涉及文化身份主题的?他们分裂与多维的文化身份认同是怎么在流散文学中表征的?他们怎么在居住国的文化与出生地的原生文化之间进行对话的?本文以法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著名作家为例,从本质主义的国族身份认同、建构主义的流散身份认同和国际主义的人类身份认同三重视角来考察当代法国流散文学的发展动态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多元身份认同观。
本质主义的国族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identité)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主要呈现为通过文本来展现和认定作者身份以及小说人物身份的相关研究。一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就是他的文化和社会归属问题。长久以来,本质主义身份认同观(essentialiste)和建构主义身份认同观(constructioniste)一直激烈地交锋。本质主义国族身份认同观认为个人的身份与生俱来,“总是通过你的宗教、社会、学校、国家提供给你的概念(和实践)得以阐述”。本质主义身份认同观认为身份是一种常驻不变的“人格状态”,是赖以确定人们权利和行为能力的基准,人们一旦从社会获得了某种身份,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与此种身份相适应的各种权利,体现了整体、稳定、核心身份、归属感和同质性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这种本质主义身份认同在米兰·昆德拉及其作品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法国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流散书写充满了身份不确定性危机,因国族身份认同缺失而产生的焦虑与苦闷。这一切使得他通过流散文学创作对在流亡情境下的自我生存状态和个人身份认同进行了深刻地思考。其中,本质主义国族身份认同既是他作品永恒的追求,又是他进行流散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力。他几乎使用各类变奏阐释其对本质主义国族身份认同难以割舍的复杂情感。他的作品充满着含混与矛盾,呈现出流散文学作家文化归属的复杂特性,较好地阐释了流散文学中的本质主义国族身份认同主题:流亡生活使流散作家遭遇惨痛的文化变迁命运,他只有通过流散书写而顽强地保留捷克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因为,进行流散文学创作就是他保留国族身份的最好方式。
一般认为,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是身份问题的两个方面。身份焦虑是身份问题的最初表征:它要么触发身份危机与毁灭,要么推动身份建构与重构。作家以及作家的小说人物内心深处的本质主义国族身份认同危机是产生身份焦虑的总根源。米兰·昆德拉中年后被迫移居法国,流亡生活与流散写作充满了艰辛。无奈之下,作家借作品人物之口投射出了旅居异国他乡的自己对法兰西异质文化的陌生与焦虑。这是因为米兰·昆德拉对祖国无比忠贞,当面对时代变迁、空间错置时,他便自然产生了身份焦虑,“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明确的身份定位,那么他生存在世界上就没有归属感,也就无法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和自由。实际上,文化身份问题始终挥之不去,困扰着米兰·昆德拉,始终表现为难以名状的焦虑与彷徨。为了对抗这种痛苦,移民作家常常会努力培养自己对移居地的感情,但在艺术创造中仍坚持寻找自己唯一的祖国。因为,在语言与文化断裂的背后是米兰·昆德拉对自己不懈追求本质主义国族身份认同意志的反复检验。
在身份焦虑之外,身份问题的另一面则是身份认同。米兰·昆德拉时常处在身份认同选择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前。一方面,由于对捷克民族深深的眷恋之情,米兰·昆德拉自觉地充当捷克文化在世界的代言人。他运用流散文学的写作方式,通过回忆个人及国家的历史,实现重建本质主义国族身份认同的目标。米兰·昆德拉希望将流散文学创作当成一扇窗户,让世界人民透过这扇窗户了解捷克的历史文化、风土民俗。另一方面,他迷恋始终是欧洲文化中心的法国文化,把它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事实上,米兰·昆德拉对法国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彻底忘却过去、忘却祖国捷克。在捷克的生活经历作为不忍忆及却又挥之不去的浓浓底色沉淀于他的脑海深处。这种故国生活经历的沉淀是基于他对自身及本民族坎坷惨痛记忆的细致描叙和对那段经历刻骨铭心感受的准确传达之上的。捷克成为米兰·昆德拉心中永远的一个结;离开了捷克的题材内容,米兰·昆德拉作品的灵气也就失去了大半;而完全用法语创作,也实在很难像用母语那样把故事讲得准确生动。因此,米兰·昆德拉更像是一位“法国化的捷克作家”。
虽然移民法国20载,米兰·昆德拉却挑选了“身份”“自我认同”这类带有跨文化意蕴、后现代色彩的主题展开艺术探讨,这不能不说反映了他试图重建本质主义国族认同的固有心态。事实上,米兰·昆德拉对“身份”的关注,不仅仅缘于他自身的移民处境,而且伴随着世界文化交流而带来的“边界模糊”“特征消失”等一系列文化语境问题。因而,米兰·昆德拉小说的遗忘主题就是重建本质主义国族身份认同的有利武器,拒绝遗忘即拒绝遗失本质主义的捷克民族身份认同。
建构主义的流散身份认同
与本质主义身份认同观针锋相对,建构主义身份认同观坚持身份不是天生的本质(being),而是建构的过程(becoming),它“既属于过去,同样也属于未来”。传统社会的人们安居世界的一隅,天然地归属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然而,当今全球化潮流大发展之际,对于移居他地甚或他国的移民人群而言,全新的环境和文化“打破了地点与身份之间固有的关联”,使得认同主体一方面产生了身份焦虑危机,另一方面却拥有了身份重构的机会。学界认为,流散身份认同是一种特殊的双重或者多重国族身份认同,因为“飞散的文化(文学)是跨界的、旅行的、翻译的、混合的(border-crossing, travelling, translational,hybridized);它既是民族的又是跨民族的,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斯图亚特·霍尔(Struart Hall)强调指出,流散身份认同“既归属于母国,同样也归属于他国”,是一种母国与他国之间某个区域的“定位”(position)。这也正是身份认同之所以会因人而异,出现各种不同可能性的原因所在。不同的流散者会作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身份妥协。同样,因为这种身份妥协的存在,移民经历并不一定会建构出一种流散身份认同。相反,身份焦虑使得认同主体可能产生身份危机甚至毁灭,或者也可能导致移民主体更为强烈的反弹,建构出更为稳固的本质主义国族身份认同,因为“流散经历同样也能够再次产生与地点相连的本质主义身份认同,虽然这是流散本应予以超越的”。
如果说米兰·昆德拉在寄居国法国依然坚持个人的身份定位、自我解读、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社会、文化等的碰撞、交流过程中焦虑、失落、彷徨、得不到理解,而只能通过流散文学创作将其转化成为一种纯粹个人化的理念追寻,并将之作为文学艺术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么作为个人主体的程抱一在自我身份、自我解读、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的定位上,与其所追寻的社会大环境的主流价值因素相一致。在此,个体的需求也是“他者”的渴望,能够与“他者”互动,并引起其中大多数成员的共鸣。个体企图获得的大众认同的意愿也就在这个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磁场里得以实现。这些都是由各自内心深处的不同类型身份认同观决定的。显然,较之米兰·昆德拉,程抱一通过流散文学创作重建流散身份认同的努力让他走得更远,取得的成就也更大。
程抱一出生在一个中国的书香门第家庭。大学期间,他获得奖学金选择赴法留学。最初的法兰西生活中,程抱一艰难求学,最终获得高校教师资格,总算在异国他乡扎稳了脚跟。随着知识不断积累,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法国文化圈著名学者的推崇。正是与这些法国当代文化名人的密切交往,才使得程抱一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努力呈现中国实际智慧的精髓”。他从“中国留学生”到“文化移民”再到“法兰西院士”的三种文化身份转变,使得他早期遭遇过文化断裂的痛苦、身份焦虑的彷徨,中期经历了中法文化融合的洗礼确定了未来的身份认同方向,晚年则通过创作小说《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开启了选择建构主义的流散身份认同重构。
程抱一的首部法文小说《天一言》展现了人类共同命运的格局。它不是普通“亲身经历”的如实纪录或是“借题发挥”的政论,而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流散文学作品。《天一言》描述了20世纪曲折多变的个人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展现了华裔文化人的流散漂泊生活历程与心路发展,反映了一代流散飘零者从身份焦虑危机到确立身份认同,并通过对人生与艺术的不懈追求完成了文化身份的重构。程抱一的流散写作刻画了东西方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挖掘表现生命底蕴的细节,思考人类命运的哲学未来。程抱一在东西文化融会贯通之后表现出来的芜杂多姿的丰富性与其所追寻的法兰西社会文化大环境的主流价值因素相一致,既是作者的需求也是“他者”的渴望。在“他”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程抱一的流散文学作品《天一言》使得法国主流文化圈的大多数成员产生思想共鸣。正是作者运用东西文化两种视角来观察,以兼容并包的态度来丰富完善他国文化的心态,最终使得他企图获得法国主流社会认同的意愿也就在这个东西文化兼容并包、拥有共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磁场里得以实现。正是他的流散写作使得《天一言》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强烈的思辨穿透影响力。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天一言》就是中西文化相交汇的硕果。
程抱一以东西方文化交流为目标,孜孜不倦地介绍传播东西方文化的精髓,运用流散写作来提升自我思想格局,并以积淀理论修养以及流散文学创作共同地参与构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最后成功地融合了东西方双重文化身份和双重文化视角,建构了崭新的流散文化身份认同,成就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国际主义的人类身份认同
后殖民理论家认为身份不但是被建构的,而且是依赖某种“他者”被建构起来的一套或者一系列的身份。霍米·巴巴提出了“双重身份”的概念。作为一种身份建构策略,“双重身份”并不是简单地说有两个身份,而是要指出身份协商的重复性,及其连续的重复、修订、重新定位,没有哪次重复与前面的是一样的。后殖民主义否定身份的单一、静止、固定性,而认为身份是个可以协商、变动、有多重因素相互混杂,需要不断重新定位的过程。国际主义的人类身份认同是指个人不再拥有恒定不变的身份认同感,身份成了一个混杂的、不断协商、不断修订、不断重新定位的循环过程。
显而易见,勒·克莱齐奥与程抱一所追求的大方向相同,但前者不局限在更新之后静止固定的身份认同状态,而是随着流散生活经历而不断混杂、协商、修订、重塑自我身份认同。勒·克莱齐奥的终极目标是“国际主义写作”实践,即将身份认同的参照范围突破单一具体的家庭、民族、国家的框架,试图站在全人类的宏观视角来建构国际主义人类身份认同。
勒·克莱齐奥对身份认同的思考,并未局限于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的二元矛盾,而是以其倡导的“国际主义写作”实践,突破了理论界这种二元身份认同观,将身份认同的参照范围从国族、流散拓展至整个人类。“流散”既是作家漂泊的生活状态,也是作家小说中漂泊人物的写照。勒·克莱齐奥进行流散写作的位置是在多元文化杂糅碰撞的法国本土。他一如一位在异域生活里不断艰难跋涉的流散作家,在地平线的一端和另一个时空中不懈地寻觅带有“逃离”与“回归”主题的流散书写生活方式。在各大陆间不断漂移是勒·克莱齐奥流散写作的主要特征。当他把目光转向异域,将其作为他流散写作的转折点时,他的家庭背景和年轻经历帮助他站在“他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世界。面对日趋僵化、虚伪、失去人性的西方文明,他意识到只有转向其他文明才能得救,才能重启文明更新发展的新进程。通过流散写作方式,勒·克莱齐奥试图寻觅现代文明所丢弃的,但被沙漠民族完好保存的原始丰饶的文明记忆。他身处异域文化氛围不是为了沉迷异域情调,而是为了唤醒潜藏的文化身份意识,找回心中憧憬的以多元文化为底色的统一世界、繁荣的大同社会。
勒·克莱齐奥希望通过流散书写的方式,展示了异域民族与众不同的特殊价值。他坚信多元文化能够帮助各民族完成统一,达到人类世界的终极理想。在以流散书写方式来书写边缘生活以及建构边缘生活空间的过程中,勒·克莱齐奥的流散文学创作对文化身份意识的认同与重构,实际上就是其构建多元文化身份意识的内心写照。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勒·克莱齐奥的身份认同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演化发展的轨迹。拥有流散经历的勒·克莱齐奥对小说人物的各种身份认同,即便是本质主义的国族身份认同,都抱有同情和包容的态度。勒·克莱齐奥这种动态发展、包容多元的身份认同观,也正是建构主义和他所倡导的“国际主义”身份认同的题中之意。
结语
当代法国文学涉及的思潮、主题、流派的范围宏大而又宽广,上文主要分析和评介的仅仅是其中的流散文学主题。这些当代法国著名流散文学作家试图从不同层面揭示后现代多元语境下他们内心深处的无奈与焦虑。我们以米兰·昆德拉、程抱一、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倾向为研究对象,既研究流散文学作家以特殊族群的生活方式在异国他乡从事流散文学写作的文学价值,又研究他们及其流散文学中的主人公在文化身份意识上所共同具有的模糊性、流动性和嬗变性的文化内涵。上述三位典型作家都以其独特的视角,生动地描绘了身处异域,在异质文化中艰难跋涉的曲折心曲,深刻揭示了因文化身份意识含混不清而导致内心变化多端的情感纠结。因此,在当代法国流散文学中,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国族身份认同、流散身份认同和人类身份认同的叙述,不仅观照了理论界流行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身份认同观,而且通过勒·克莱齐奥的“国际主义写作”实践突破了已有的身份认同理论框架,将身份认同的“他者”置于整个人类范围之中进行思考,这极大地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进而取得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