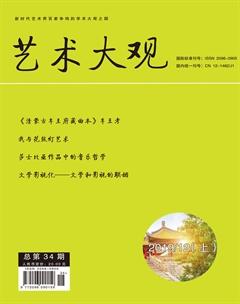浅析中国传统戏曲“大团圆”情节模式的悲剧隐喻
摘要:中国戏曲的“大团圆”式情节模式是在中国思维方式的主导和支配下孕育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戏剧形态。“大团圆”并不能一概被视作回避矛盾、淡化冲突的方式,而是一种特别的矛盾展示形式。这种情节模式设定并不能用纯粹意义上西方的“悲剧”或是“喜剧”来划分,中西方戏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各自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戏剧情节形式,浓缩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心理期待。
关键词:戏曲;大团圆;悲剧
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说:“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间)就有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1]这是针对元杂剧的“大团圆”结局提出的,但也涉及“中国有没有悲剧”这一理论问题。在中国戏曲走出国门或西方戏剧走进中国市场的互动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文化理解上的差异。就中国戏曲的传播而言,多数国外受众以至我们的国内从业者,在西方“悲剧为大”的艺术氛围的影响下倾向于认为中国戏曲是一种较为肤浅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理解差异也会直接影响文化交流的效果。因此,如何客观的看待中西方戏剧中的差异,如何正确理解差异的缘由是十分重要且有意义的一件事。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戏剧艺术,把握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中国传统戏曲“大团圆”情节模式
中国的戏曲肇始于宋元时期,出现于宋代的勾栏瓦舍与不断繁荣的民间曲艺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戏曲自身对说唱歌舞和扮演故事等多种舞台手段的进一步融合,逐渐向成熟的综合舞台艺术形式发展。在元代,“大团圆”式的情节模式不断发展和固化,慢慢定格成了一种创作传统。清代,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与文人士大夫冲破禁锢之间的矛盾,加之世俗娱乐的发展,“大团圆”模式的创作也获得了更充分的存在理由。
朱光潜先生曾指出,“中国人是最讲求实际,是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2],用强烈的道德感代替了宗教的狂热,相信整个世界是充满正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道自有好轮回。也正是因为这种“伦理哲学”的存在,中国人在面对哪怕再激烈不过的矛盾冲突也依旧能寻求到解决之道,或是引入第三方来协调缓和矛盾,哪怕最后的解决之道并不很合乎逻辑,但仍会给矛盾冲突安排上“中和”解决之道来符合自己的美学要求和逻辑认知。
从文化观念上看,戏剧之所以设置悲剧结局,在揭示人生固有的无奈的同时,也暗示着在人世间并没有一个足以协调矛盾的权威——甚至权力本身都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但中国戏曲并不倾向于质疑权力本身,而是更倾向于指向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比如说某一个贪官或是某一位昏君,是偶然的和个别的,权力本身没有问题,甚至于最高权力本身——皇帝,就是救赎者。这样,表面上是批判了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但实际上却又是维护了权力秩序,这种社会功能,正是从宋到清的帝制社会所要求的。
二、西方戏剧的“悲剧”
西方戏剧起源于古希腊,悲剧随着古希腊戏剧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西方戏剧从诞生之初就和政治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希腊戏剧是神谕,反映自然力量与未知的非人力量的抗衡从而显示出人的力量。西方文化在其源头时期,就意识到了悲剧所具有的教育作用,悲剧模仿的是较好的人,而且能够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达到思想的升华。西方戏剧中神、命运、等人世之外的力量往往会参与到事件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可以充分暴露,不用遮蔽隐藏矛盾。同西方神话一样,西方的社会结构一直处于一个颠覆的状态,不断有较大的冲击和革命刺激着社会。因此,猛烈的矛盾与冲突在西方人看来是正常的状态,是真实的现实。西方的悲剧并不介意描绘和展现激烈的冲突后悲惨的结局,相反,西方人认为悲剧让人们灵魂震撼,财富和权力容易被抢劫、精神和意志可以被消磨、感情可以被欺骗和分割,只有悲剧是无法被掠夺的,悲剧中的痛苦是无法被占有和复制的,悲剧主人公的精神气度更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三、结语
不同的生死观念造就了不同的审美心理,这也是西方崇尚悲剧而中国偏好“大团圆”艺术差异的一大原因。但不能简单地从结局的性质来判断中国缺乏悲剧。优秀的戏曲作品即便有着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总能在直面现实的情節中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人情的冷暖。在这个意义上,“大团圆”并不能一概被视作回避矛盾、淡化冲突的方式,而是一种特别的矛盾展示形式。或者可以说,某些“大团圆”的结局设置也正是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诉说着人间的无奈和悲伤。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第一版)[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3]傅谨.中国戏剧艺术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4][德]曼弗雷德·普菲斯特.戏剧理论与戏剧分析[M].周靖波,李安定,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张仲阳(1997.12-),女,汉族,河北省邯郸市,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在读,从事文化产业、戏剧戏曲学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