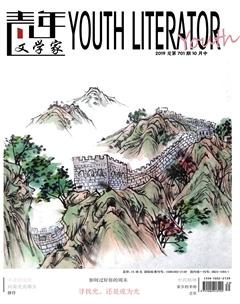从孽缘到救母:沉香救母传说的历史流变研究
赵蕴璐

摘 要:“沉香劈山救母”传说以唐宋“异类孽缘婚恋”这一单一主题为缘起,到明清成为多个主题的综合。经过近现代官方、民間和传播媒介的合力再创造,演变成以“孝子救母”为突出主题的传说,并成为“救母”主题神话的典型。按照主要故事情节的增删,“沉香救母”传说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流变阶段,而传说情节不断流变的根本原因,正是当时的社会风俗、民众主要诉求的不断发展和转变。
关键词:传说流变;沉香救母;华岳神女;沉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9-0-05
自从“孝”成为道德典范,并格外受到推崇以来,以“救母”为主题的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不断涌现,甚至“救母”情节能够栖身到旧有神话传说当中,并顺利融合。“救母”的原因、方式、结局不尽相同。为了神话传说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往往赋予“孝子”神力,凭借种种壮举达成“救母”目的。
《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 能出云, 为风雨, 见怪物, 皆曰神”[1]。古人对自然的忌惮敬畏之情,使得人们对这股神秘力量进行人格化创造,山神成为承载人们寄托的必然产物。“据史料记载,虞舜时就有祭祀山川的制度,泰山、衡山、华山、恒山等四岳皆在祭祀之列。以后,历代天子封禅祭天地, 也要对山神进行大祭[2]。”华山位列五岳之一,民间传统的山神信仰使得西岳华山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情结,产生了大量神话传说。随着人文意识的觉醒,原先神秘莫测的华山逐渐成为人们达成愿望的阻碍,“沉香劈山救母”传说在流变的任一阶段都与华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唐宋雏形期:华岳神女与穷书生的孽缘(相遇-逼婚-另娶-除妖-分离)
(一)凌厉决绝的女神形象
目前可见最早的关于华岳神女的文献,是唐代戴孚的《广异记·华岳神女》篇,讲述华岳神女私婚书生的故事:
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须臾,公主车声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寝,不敢出。公主于户前澡浴,令索房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见某,群婢大骂。公主令呼出,熟视之曰:“此书生颇开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毕召之,言甚会意。使侍婢洗濯,舒以丽服,乃施绛帐,铺锦茵,及他寝玩之具,极世奢侈,为礼之好。
……
如是七岁,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为之娶妇。某甚愕,怪有此语。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为君妇。君亦当业有婚媾,知非恩爱之替也。”其后亦更别婚,而往来不绝。婚家以其一往辄数日不还,使人候之,见某恒入废宅,恐为鬼神所魅。他日,饮之致醉,乃命术士书符,施衣服中,乃其形体皆遍。某后复适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门惆怅。公主寻出门下,大相责让,云:“君素贫士,我相抬举,今为贵人。此亦于君不薄,何故使妇家书符相间以我不能为杀君也。”某视其身,方知有符,求谢甚至。公主云:“吾亦谅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势不得住。”悉呼儿女,令与父诀,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装,即日出城。某问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华岳第三女也。”言毕诀去,出门不见。[3]
神女处于恋爱婚姻中的主动地位,积极求爱,强势要求书生结为夫妻。面对刚毅直率的“华岳神女”,男主人公的表现如下(见表1):
作者间接描写懦弱惧内、惨遭抛弃的士人;直接表述神女的言语,富裕华贵、刚毅果断的独立女神形象跃然纸上,男女性格有天壤之别。妇女妒性的发达和男子惧内之风盛行,说明唐代妇女地位曾一度相对提高[4]。这时的神女不仅可以自己主动选择相爱对象,还有能力给予丈夫诸多财物。神女为了让心爱之人拥有匹配的对象,不惜将心上人拱手让出,退出婚姻,甚至沦为他人婚姻的插足者,险些遭遇伤害。而男子对“伤害”毫不知情,并未作出相应的保护神女的举措,“未能管好内眷”成为男子被抛弃的主要原因。神女潇洒转身、果断离开处事不当的爱人,证明了神女的独立强大,并未成为男子的附庸。
南宋的皇都风月主人在《绿窗新话》中记载了唐代《异闻集·韦卿娶华阴神女》:
韦子卿举孝廉,至华阴庙。饮酣,游诸院,至三女院,见其姝丽,曰:“我擢第回,当娶三娘子为妻。”
……
俄见车马憧憧,廊宇丽严,见一丈夫,金章紫绶,酬对既毕,择日就礼。女子绝艳,真神仙也。后七日,神曰:“可归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匹,使君终身无嗣,不可也。君到宋州,刺史必嫁女与君,但娶之,我亦与君绝。勿洩吾事,事露,即两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与论亲,遂娶之。神女尝访子卿曰:“君新获佳丽,相应称心。”子卿踌躇不自安。女曰:“戏耳。已约任君婚娶,岂敢反相恨耶?然不可得新忘故。”后刺史女抱疾二年,治疗罔效。有道士妙解符禁,曰:“使君,韦郎身有妖气,爱女所患,自韦而得。”以符摄子卿鞫之,具述本末。
……
道士告神女曰:“罪虽非汝,然为鬼神,敢通生人,略无惩责。”乃杖三下而斥去之。后踰月,刺史女病卒。子卿忽见神女曰:“嘱君勿洩,惧祸相及,今果如言。”袒而示曰:“何负汝?使至是乎?”子卿视之,三痕隐然。神女斥左右曰:“不与死乎?更待何时?”从者拽子卿捶扑之,其夜遂卒。[5]
该故事的男主人公韦子卿,为华阴庙中的三娘子的美貌所吸引,戏言要娶神女。最终因泄露神女事迹,被打骂致死。而宋元之际的《异闻总录》,韦子卿遭受同样的结局,只是删去了华岳金天大王的准婚,让故事更接近于韦子卿与神女为爱私奔。
与唐代神女相比,宋代神女愈发大胆泼辣起来——像是因爱人违约而冲昏头脑,误杀丈夫的妇女。但是这时的神女丧失了婚姻缔结的主动权,韦子卿的一句戏言,以及父亲的要求,神女的归宿就此敲定。迫于社会压力,神女又要放弃丈夫以求子嗣。宋代妇女的在婚姻生活并不及唐代妇女那般洒脱自由,开始受到了宋明理学的桎梏,男性在婚姻家庭地位中占据绝对上风。然而这位遵循礼制、未行出格之事的神女,因为韦子卿的失信,惨遭术士鞭打,伤痕累累,极度渴望冲破封建枷锁,韦子卿成为承受神女怨气的箭靶。宋代的神女虽不及唐代神女那般果敢豪迈,但是神女不甘屈居礼制之下,尚且具有反抗精神。在后续的演化过程中,这种“妇女的自由意识”逐渐淡化,到了清代就完全成为为夫、为子、为家呕心沥血的“三圣母”赞歌。
(二)异类婚恋的尴尬处境
“异类婚恋”是“沉香救母”传说雏形期的核心,也是该传说在任何流变阶段的基干母题。通过三则故事中神女劝男另娶的原因,可以窥见唐宋不同时期对异类婚恋的不同态度。(见表2)
尽管唐代的人神恋在世俗中不被认可,但现实的婚姻关系还可以继续,繁育后代这一主要婚姻目的仍可达成,人神间的物种障碍并不显著。忽略神女身份,这仅仅是一个维持了七年的普通家庭,异类并不是婚姻不幸的主要矛盾。这与唐代社会人文意识觉醒,肯定个人价值的社会风气密不可分。即便如此,神女依然觉得与人间男子相配不妥,要求丈夫另娶人间女子。宋代的人神恋受到神女无法生育的阻碍,属于逾矩异类婚姻,为了达成有嗣的目的,不得不让韦子卿另娶以繁育后代。人神婚姻只维持了短短几日,更类似于男性对露水姻缘的性幻想,而现实中“性匮乏”的存在必然促使人们到梦幻中寻求性的满足[6]。虽然神女可以对男子有种种要求,但是婚姻仍受“门当户对”的社会约束。人神物种矛盾是横亘在男女之间的现实沟壑,异类不可长期共居成为社会共识,虽贵为神女,也无法做到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去冲破隔阂。露水姻缘结束后,只得忍痛将心上人拱手相让。丈夫的违约成为失手将心爱之人打死的理由。她渴望一桩美满婚姻,即便是通过逼婚得到的区区几日露水姻缘,但封建的藩篱让女性放弃了对幸福的坚持。增添了封建社会与自由婚姻之间的矛盾线索,就淡化了因男子违约引起的男女婚姻矛盾。在流变过程中,冲破封建压迫逐渐上升为“沉香救母”传说的主要矛盾,社会对异类婚姻不接受的隐性的封建压力,显化为以“二郎神”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对自由婚恋的阻碍。
劝男另娶在唐宋的情节中就见端倪,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步加强,宋明理学对女性德行的要求愈发严苛,“劝男另娶”成为合格妻子的重要标准,也成为清代“沉香救母”传说众多版本中都出现的情节。
(三)道士觉察“神女”真实身份
“唐高祖起兵建唐时,为给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也攀附老子李耳,将其奉为始祖。因此自唐高祖以后,唐代诸帝均尊崇道教。[7]”唐代诸多神话传说中,道士大多扮演着斩妖除魔、匡扶正义的角色。在唐代“华岳神女”传说中,因为士人出入废宅过于频繁,现任妻子“命术士书符,施衣服中。[3]”而这个符对神女产生了威胁,拒见士人。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华岳神女”为了躲避符的危险而作出的防范措施,其真实身份是妖女。婚姻悲剧的原因看似是冷酷封建的道士从中作梗,实际上是道士的职责所在。
宋代“神女”更凸显了妖女的作风:1.威胁韦子卿在另娶后,不许泄露自己的事情,否则“两不相宜”。2.韦子卿在“神女”的要求下另娶刺史女,又不允许他对自己冷淡,韦子卿由此陷入新旧两难的困境。3.新娶的刺史女久病不愈,医病的道士认为是韦子卿身上的“妖气”所致。于是“飞黑符,追神女”,并施以惩戒,但没有处罚韦子卿。道士以为民除妖的正义形象公断是非,杖责“神女”,说明其身份和能力远高于她。看似为奇遇爱情奋不顾身的恋情,始终为道士制止。“书符”的处置方式,暗示了“神女”的真实身份。惩戒直接加剧了男女双方的矛盾冲突,间接造成了妖女的离去、刺史女以及韦子卿的死亡。
男性受到美貌多金的“妖女”蛊惑,并结为夫妻,在享受了短暂的露水姻缘后,走向死亡。表面上看似欢喜美好的爱情故事,却以男性被“妖女”所害收尾。这印证了民间传说的教化功能——以因猎奇而惨死的结局警示世间男性规范自身行为,达到维系现实婚姻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目的,形成民众共同遵守的隐形社会规范。
唐宋时期的“华岳神女”传说拥有两个母题:1.异类婚恋不得善终2.另娶新妇,尚未跳脱神异遭遇传说的范畴,对男性生活作风的警戒是这一时期“华岳神女”传说的主要功能。在后续的口头传承的过程中,不难加入其他母题,进入到更为生动细腻的民间叙事文学体裁中。
二、元代过渡期:劈山故事与孝子沈香的杂糅
(一)劈山英雄的横空出世
古人對河水穿山的华山地貌,产生了各种幻想,流传最广的当属“神灵劈山”。关于“劈华山”的传说,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踏,开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华岩。[8]”在《西京赋》等众多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神灵劈华山”的影子,加重了华山的神秘色彩,成为“圣山”。“山不再高,有仙则灵”,华山因神灵点化得以出现,其社会地位愈发尊贵,成为唐代道教发展的重要根据地,“七十二洞天”由此形成,并位列五岳之一。有“神灵造山”和“道教福地”的加持,华山的文化内涵日益丰厚,以华山为背景的民间传说不断涌现。
随着道教的繁荣和神灵体系的完善,缥缈的“劈山神灵”形象逐渐具体,增强了劈山行为的可信度。有学者称,大概在南宋时期,“神灵劈山”的故事就具化为“二郎神劈桃山”。“二郎神”在道教中举足轻重,现今在众多地区仍流传着“二郎神”事迹:四川灌口地区的“水神二郎”、江苏常熟地区的“斩龙二郎”、青海地区的“战神二郎”,《西游记》中维护天界治安的二郎神等。袁珂认为,“二郎神是南宋时才兴起的一个神话人物[9]”,“二郎神斧劈桃山应该是南宋时兴起的这一神话人物的主要事迹。[9]”而“桃山、华山,也都是当时传说中一地的异名。[9]”西岳华山对民间传说产生了强大的吸附力,与华山本无瓜葛的传说很有可能直接挪用华山为事发地,南宋“二郎神劈桃山”的事迹极有可能讹变为“沈香劈华山”的传说。甚至“沈香劈山救母”这一民间传说在南宋末年就已经以口头方式流传,至元代形成了一部情节完整而成熟的戏剧。对教育程度低的民众来说,视觉传输较之文字更为直观,更能凸显故事的真实性,在茶余饭后,民众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传说受众不断下移,添加叙述者自身的理解,导致故事情节不断重构。关于“沈香”的历史记载较少,或许他本是一个真实的边缘化人物,这为传播者留出了足够的改编空间,为他蒙上层层面纱。中国自古有“英雄崇拜”的情结,沈香被重塑成乐于为听众所接受的完美英雄化身,微妙地上升为“劈山”传说的主角。
(二)“孝子”沈香的形象
孝子沈香(沉香)这一人物的相关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元代钟嗣在至顺元年(1330年)《录鬼簿》中李好古、张时起条目。书中记载,李好古作《劈华岳》,张时起作《沈香太子劈华山》,如今皆失传。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将《刘锡沉香太子》列入已佚戏文。从戏剧题目中发现,孝子沈香成为主角,与华山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孝道在元代极受重视,这从元代风行“二十四孝”的社会现象中可以略窥一二:元代的郭居敬是一位典型的孝子,双亲去世时,哀毁过礼[10],“二十四孝”在郭居敬的改编下被过分夸大,且作为儿童启蒙教材风行于世。培养孩童的孝意识为普通民众所认可,甚至用“二十四孝图”的方式,扩大“孝”的受众面。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元代统治者在宋代理学的影响及全真教的建议下,大力提倡孝道。在元杂剧中也因此受到影响,产生了许多孝子故事的杂剧。[11]”
传播封建孝道的重要途径是编造并宣传与“孝”有关的各种神话传说,“孝”成为民间文学中最常见的母题之一。在劈山“神灵”具体化为“沈香”的同时,另加入了沈香劈山的原因;从单一地分析华山地貌成因的远古神话,转变成为破除自然阻碍以救母的孝道主题传说。把“沈香”进行艺术典型化处理,孝子形象与“劈华岳”相融合,让模糊的“劈华岳”传说有因有果,更富逻辑。虽然戏文缺失,但“寻母”的母题一直延续。可见“寻母”传说依然以各种叙事方式在民间流传,民众不断进行选择性记忆和再重构,“孝子”逐渐神化,且小说戏曲以此为根源持续演绎。元代“孝子寻母”的母题顺利添加到了唐宋“异类婚恋”传说中,甚至“孝子寻母”的母题更为突出,削减了男女之间的感情线,合并为拥有两个基干母题的《沈香太子劈华岳》传说,对后世影响极大,这是“沉香劈山救母”传说流变的关键一步。
元代张时起的几部重要戏剧作品:昭君出塞、霸王别姬、沈香劈山救母等故事世人皆知,均为悲剧[12],与明清和现代“沉香劈山救母”传说皆大欢喜的结局相反,因此仍处于“沉香救母”传说的过渡期。
三、明清定型期:曲折遭遇终获理想结局(相遇-逼婚-分别-救母-团圆)
(一)“神女”对“人性”的期待
明代资料记载的沉香救母相关传说,可参照现今存于西班牙爱斯高亚圣劳伦佐图书馆的嘉靖年间重刊的戏曲散曲集——《风月锦囊》,以及万历年《大明天下春·刘昔路会神女》二文。
本世纪80年代初,该书胶片及影印件流归大陆,受到极大关注[13]。但是该剧仅存“茅店结合”一出。学者郑尚宪将莆仙戏《刘锡》和《刘锡乞火》与现今《风月锦囊·奇妙全家锦囊沉香十九卷》残卷相比对,发现二者如此惊人地相似,二者关系之密切,可想而知[14]。因此,暂且通过莆仙戏探究“锦本”的大致内容。莆仙戏的《刘锡》分为《刘锡首出》《过庙题诗》《李仙奏旨》《乞火结缘》《赠珠哭别》《诸仙嘲笑》《落地哭庙》《闪洞生儿》《土地送子》《沉香救母》《阖家团圆》等共十一出[15]。现存《大明天下春·刘昔路会神女》的情节包括《刘锡首出》《过庙题诗》《乞火结缘》,与《风月锦囊》仅在刘昔的籍贯、曲牌等地方有些微不同,“尽管如此, 此二本有着一定的同源关系[16]。”
明代的“劈山救母”传说,故事性更强,与现实社会结合更为紧密。一家三口的团圆似乎成为刘锡奇遇的终极目的。一反前代的悲剧结局,新增了“大团圆”的“光明尾巴”,并一跃成为“沉香救母”传说的核心母题。“大团圆”结局是明清戏剧的特色,体现着中国人的乐天精神:正义始终得以伸张,才子终会遇到佳人。儒家的“中和”之美是大团圆心理在美学理想上的体现,相信宿命论则是大团圆心理的基石[17]。家族团圆始终受国人偏爱,在远离现实苦痛的戏剧故事中大量呈现家族团圆,是对现实生活中“难得团圆”的真实投射。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人民更需要一个窗口来调剂生活。戏剧作为下层人民娱乐的主要途径,当仁不让地扮演了中和苦痛生活的调味。刘锡和神女相爱不得,孝子沉香得不到母亲的关怀,三圣母得不到人身自由,但苦難的民众最终获得了“大团圆”的回报,平衡了先前生活对三人的亏待。以此来宽慰民众,苦难生活终会过去,理想结局不再遥远。
值得注意的是,在《风月锦囊》中,刘昔的籍贯转变成了扬州高田人(有学者称应为“邮”),而华岳神女假扮为与公公居住的寡妇,意欲向刘昔逼婚。寡居的身份在所有华岳神女传说中为独一份,这与明清江南地区的生育文化有关。那些长年累月终身守节、为夫殉节或戕身守节的明清烈女、节妇们,其实只是明清两代的朝廷和官绅士大夫树立起来的典型人物,这些典型在明清时期的女性群体中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18]。寡妇再嫁在明代婚育压力极大的江南地区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成为没钱娶妻的平民的佳选。《风云锦囊》中,神女以不识字的寡妇身份向刘昔逼婚(神女有能力假扮未婚女子,但却选择寡妇身份),并且最终逼婚成功,恰恰说明了寡妇再嫁的可能性和普遍性。
(二)清代突出的人文意识
清代的“沉香救母”主要以戏本和宝卷的形式留存。在保持了明代的基本情节外,还加入了唐宋时期“另娶新妇”的母题,添加了王桂英/王夫人和秋儿两个人物。二郎神怒将华岳娘娘压在华山下,沉香与二郎神大战,救出娘娘,另救出秋儿,一家五口团圆。
华岳娘娘贵为神仙,无力保护自己的儿子,拜托给与自己实力悬殊的平民刘向和王桂英,见面之后“华夫人忙拜谢桂英小姐,叫一声‘贤妹妹多赖你身!沉香子若不是我妹抚养,怎能到黑云洞搭救母亲?秋香保到秦府替父抵罪,真难得,行孝道盖世难寻!贤妹妹请上坐受我一拜,谢当初收姣儿抚养之恩。[19]”神仙和人的能力并无高下之分,甚至人能够帮助神仙达成愿望。两位妻子都不善妒,互相扶持,阖家团圆。男子另娶已经成为清代婚姻常态,这无疑是对多妻家庭中妇女的道德说教,暗示她们要放弃妒忌,互相包容。这种人神异类间的“大团圆”,证实了清代人神界限已经模糊,双方的特征和能力也走向趋同。因此,人神异类婚姻的民间接受度更强,神富有“人性”,回归为普通家庭成员。
在清代戏文弹词中,无一不将沉香的战斗能力过分夸大。他能够战胜神仙娘娘无法打败的二郎神,帮助神仙重获自由。华岳娘娘无力自保;王桂英深明大义;沉香不畏权贵,每个人都比华岳娘娘更刚毅,神仙成了被动接受救援的对象。人神二方本是异类,能力悬殊,却在清代几近相同,甚至人的能力隐隐有超过神的趋势,比起神仙,更加具备反抗封建势力的决心和能力。神不再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与人一样经历着爱恨情仇,体会着人生百味,华岳娘娘只是一位对家庭重聚有着强烈渴望的普通妇女。“神意消退的同时,人的自我意识增强,这使得清代的人神恋也通俗化、人情化,与世俗中的人人恋爱故事没有多少区别,仍然需要遵从现实中的礼俗规约[20]。”同时,心学强调“心外无理”,理学强调“理即是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心也就超越了天,成了最后的永恒。即便人神差距大幅度缩小,但“异类婚恋”和“孝子寻母”仍是“沉香救母”传说的核心母题,另外还添加了“人神大战”和“大团圆”的母题,其他故事情节由此演发,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
(三)精英文人改编传说
华岳神女对刘昔的帮助,正是清代底层经济窘迫的男性对仕途和人生期待:与神女的露水姻缘;神女赠予大量财物;成为免考状元;娶县令之女;两个儿子;妻贤子孝,这些正是民众对生活的全部愿景。当士人通过科举考试栖身上流社会的理想越来越难实现时,大量未中举的闲置文人为了糊口,顺理成章地成为改编以及传播民间传说的暗中力量。而这些无法实现个人理想的下层文人,迎合了读者的口味的同时,也将底层文人自身的浪漫期待寄托于笔下的人物。“现实中底层男性的婚姻困难表现在民间传说中便是对婚姻的幻想。经济窘迫的年轻男性幻想从传说中走来一个完美的婚姻对象——年轻、貌美、多金,甚至愿意主动示爱。而这一幻想在现实的伦理框架与婚育观念中无法实现,便自然地转而寄托于异类婚恋传说的变异性表达。[21]”在清代“沉香救母”传说中,刘昔本为富二代,貌美的华岳神女不计刘昔对她的冒犯,主动求爱,主动中意这位尚无权势、实力悬殊的书生,并鼎力相助,最终实现其向上层社会阶层流动的愿望。这也解释了“沉香救母”传说在清代社会背景下发生转变的缘由。
四、现代传播期:官方、民间和文人的共同推力(被迫分别-反抗成功-母子团圆)
清代的“沉香救母”是一夫二妻制婚姻,不符合现代法制婚姻,因此“另娶新妇”的母题被率先摒弃。1959年剧作家王昌言的河北梆子《宝莲灯》,将刘彦昌塑造为一位民间医生,在上山采药途中,偶遇手持宝莲灯为人民驱散邪恶的三圣母。这使得男女双方地位更加悬殊,事业更加相似,偶遇更加合理化、戏剧化。该剧由河北省青年跃进剧团派演,集聚了全剧团的精英演员,1962年暑假,在北戴河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表演,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剧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称赞《宝莲灯》改得好,戏演得好[22]。从这时起,因为毛泽东的首肯,名声大振,成为召开重要会议和招待外宾时的必演剧目,《宝莲灯》获得了巨大助推力,由饱受争议的华山传说跃升为具有反抗精神的优秀民间文学。1976年1月,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拍“老戏”《宝莲灯》的彩色录像,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他要看《宝莲灯》[22]。仅仅一个月,河北省梆子剧院就将1962年的原班人马凑齐,并恢复了14年前的功力,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负责,拍摄成戏剧电影。因为国家领导人对《宝莲灯》的偏爱,使得该传说从“寻母”母题的众多传说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现代戏剧电影的先锋。1978年,《宝莲灯》电影作为首批传统戏影片向全国公映,同时《宝莲灯》作为传统戏开禁的第一部,也在石家庄公演。一经开放,观众像开了闸的洪流涌向剧场,涌向剧院[22]。
《宝莲灯》不仅获得了领导人的认可,还有现代传播技术的加持,使得这一传说普及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但在媒体成为主要传播力量的同时,也让剧情趋于固定,变得模式化。口耳相传不再是主要传播方式,音像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影者的想象空间。为了贴近变化了的社会现状和观众审美,编剧对戏剧进行了改编。200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由九年改编,余明生导演的35集连续剧《宝莲灯》,在CCTV8的平均收视率达到5.51%,是该频道2003年以来黄金时段收视率最高的一部电视剧[23]。至2009年,在央视一共播出了38次[24]。可见,对《宝莲灯》的现代改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广受欢迎。
《宝莲灯》的“沉香救母”片段着重体现沉香对母亲的孝,以及对封建压迫的反抗精神,不怕艰辛、爱憎分明的小青年形象跃然纸上。“沉香劈山救母”这一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富有民间性和教育意义。这也反映在电影的拍摄上——1928年,大中国影片公司制作了以‘劈山救母为题材的无声黑白电影《小英雄劈山救母》[25]。1956年上映的《宝莲灯》(中联电影有限公司出品)讲述的也是沉香劈山救母之事。20世纪80年代之后,涌现出众多宝莲灯的改编电影和连续剧。为了进一步扩大受众,传承《宝莲灯》精神,“劈山救母”纳入到儿童教育中。1985年,《西岳神童》的上集由上海美術电影制片厂推出,完整版于2006年公映,获得了极佳的票房成绩。在连环画等儿童读物中也大量出现了《宝莲灯》改编的故事,着重强调沉香的孝顺勇敢,淡化了三圣母和刘彦昌的爱情线。小学语文苏教版第四册中收录了《劈山救母》的故事,使得“沉香救母”的传说在现代基本定型。
小结:
唐宋时期的“华岳神女异类孽缘婚恋”传说,添加了民众偏爱的“救母”情节和山神信仰,在明清时期发展成故事性和综合性极强的“沉香劈山救母”传说。经过近现代官方、民间和传播媒介的合力重构,情节有所简化,成为以“救母”为核心主题的“孝子”传说。透过“沉香救母”传说的历史流变,得以窥见不同时期的民间风俗。
参考文献:
[1]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 中华书局, 2001年, 第670页。
[2]王永莉,何炳武.以《华岳志》为中心的西岳山神信仰研究[J].人文杂志,2012(06):184-189.
[3](唐)戴孚撰.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广异记[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第57页.
[4]鲍家麟.中国妇女史论集续集[M],台湾,稻香出版社,1999年:60
[5](宋)皇都风月主人编;周夷校补.绿窗新话 2卷[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41页.
[6]蔡堂根. 中国文化中的人神恋[D].浙江大学,2004.
[7]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3):83-89.
[8](北魏)郦道元著;谭属春,陈爱平点校.水经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5.第52页
[9]袁珂著.中国神话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第304页
[10]叶涛.二十四孝初探[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1):28-33.
[11]田黎明,刘祯主编;张静分册主编,中国戏曲史研究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06,第180页
[12]许金榜主编,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戏曲卷,齐鲁书社,2005年01月第1版,第41页
[13]黄仕忠.《风月锦囊》刊印考[J].学术研究,1998(03):121-123.
[14]厦门大学中文系编.厦门大学中文系90系庆学术文选 1921-2011[M].廈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第541页
[15]厦门大学中文系编.厦门大学中文系90系庆学术文选 1921-2011[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第540页
[16]李晓.明万历戏曲选刊《大明天下春》南戏散出选考[J].曲学,2015,3(00):331-365.
[17]单有方.大众品位与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127-130.
[18]陈剩勇.理学“贞节观”、寡妇再嫁与民间社会──明代南方地区寡妇再嫁现象之考察[J].史林,2001(02):22-43.
[19]杜颖陶辑.董永沉香合集2卷[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41页
[20]蔡堂根. 中国文化中的人神恋[D].浙江大学,2004.
[21]余红艳.明清时期江南生育文化与“白蛇传”传说的演变和传播[J].民族文学研究,2014(02):123-132.
[22]王德彰.文革中河北梆子《宝莲灯》拍电影[J].文史精华,2011(04):58-63.
[23]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6》,中国广播出版社,2006年5月,第268页.
[24]孟丽:《<宝莲灯>收视夺冠 中国式“雷剧”越雷人越红》,载华商晨报,2009年5月1日.
[25]李霭芬.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影视剧中的再创作[D].云南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