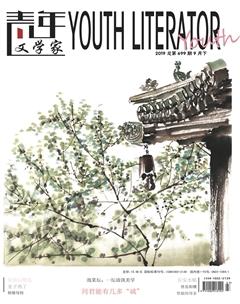李煜词悲剧色彩与佛教思想的关系
摘 要:李煜词具有明显的悲剧色彩,本文主要通过南唐宗教的影响与李煜的家庭、性格和生平经历影响两个方面,探究了李煜词中所表现的佛教思想来源,及其哀伤基调的形成原因。剖析了李煜词所反映的佛家思想文化及内涵,并揭示了佛家思想与李煜词中悲剧色彩的关系。
关键词:李煜词;佛教;悲剧色彩
作者简介:杨希云帆(1993.8-),女,四川成都人,助教,广播电视编导,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7-0-02
李煜親手所作之词现存世共三十余首。从内容上讲,可划分为两个方面,以开宝八年亡国降宋前后为分界线。前期的词大部分在描写宫廷骄奢淫逸的生活写照,限于男女燕婉之私,风花雪月之事。虽离不开花间派的风格影响,用流利笔法写绮丽柔靡之情,但在前期创作的词中依然带着一种悲剧意识,表面上看似生活悠哉,寻欢作乐,歌舞升平,可在这繁华的后背却隐隐透露出一种惴惴不安和浓浓的哀愁。在后期的词中,主要反映了亡国之殇,身世之痛,悲剧色彩全然异于花间词派的风格。
1、南唐宗教对李煜词的影响
南唐君王们普遍崇尚佛教,这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根基,更是对南唐的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南唐的佛教信仰推进了南唐文风的形成。以词体创作为例,南唐和西蜀就有着明显的不同:西蜀道教盛行,更注重的是现实享乐主义,花间词中有很多词调作品都是以描写文人女子风雅放纵的生活为题材,表现文人雅士与女子间的缠绵悱恻,比如《天仙子》、《女冠子》这样的作品。而到了南唐,可以从词作中明显感受到佛教的悲天悯人之颓和对于国家衰亡的伤感,词中处处弥漫着人间疾苦、苦海无边的悲剧色彩和苦闷情怀,饱含士大夫们与朝廷官员对于国家、生命的哀思和忧虑。
南唐礼佛兴始于李先主李昪,自烈祖以至后主,都信奉佛教,尤以后主为最。从南唐开始至尾,佛教的思想贯彻是由上至下的,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到了李后主掌政时期,李信佛拜佛、沉溺礼佛几乎贯穿了李煜整个生命历程。所以无论是其本人,还是他的词作都带有厚重的宗教感。
南唐后期,对于佛教的崇拜已成为举国风尚,以致兴修佛寺,僧尼泛滥,对佛教的信仰甚至已高于国家司法。这样的风尚必然给国家统治秩序带来混乱。南唐供养了千千万万不劳而获的僧尼,长期的供养,对整个国家的财力、物力是极大的负担,使得国库入不敷出,南唐后期的统治摇摇欲坠。据《十国春秋》记载,李煜曾于开宝二年普度众僧,第二年改宝公院为开善道场。由此观之,即便是在南唐风雨飘摇、国库空虚的危难关头,李煜仍在不遗余力地尊佛护佛。陈彭年《江南别录》中写道:“后主笃信佛法,于宫中建永慕宫,又于院中建静德僧寺;钟山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李煜不仅在宫中大修佛寺精舍,甚至偏袒僧人,不顾国法,在国家渐衰的时刻,追崇礼佛给国家带来的无疑是雪上加霜,南唐的佛教风行对于最后的亡国也有着不可推脱的联系。
2、李煜的生平经历与佛教的关系
李后主出生于一个崇尚浮屠的帝王之家,无论是李先主还是中主都对佛教有着炙烈的虔诚,李煜自己更是从小托身佛寺,受佛教文化熏陶。李煜号莲峰居士,以一个佛教信徒自居。从佛家角度来说,意思是居财之士,居家之士,在家志佛道者。名号虽只是个代号,但是我们亦可从中探寻李煜的厌世心理,他向往隐居,渴望归山,透露出对现实的厌倦之情。从他的两首《渔父》中,可见其内心向往——“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李煜无心追求威仪天下,万古长存,只求独善其身,一酒一竿,求个自在。“世间像我这样快活的人又有几个呢。”这虽是词中借渔父之口说出的话语,可更像是李煜的自言自语,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情绪。这便是李煜《渔父》之一的意境。渔夫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游于青山绿山,自由闲适。在李煜眼里,渔父是自由浪漫的艺术家,也是理想中的隐者。他本就无心权力与战争,贪恋在桃李树下享受惬意的浪漫生活。在《渔父》(其二)中李煜写到:“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两首《渔父》反映了李煜对隐士生活的渴求。本就无意做君王的李煜似一个历史的错误,为了避免兄长猜疑,终日隐居在山间,醉心于自然之乐。可偏偏是他坐上了皇位,他过早目睹和经历了家族争权夺利,相互厮杀的惨剧。处于风雨飘摇的南唐给这个多愁善感的词人带来了无尽的困扰。清代词学家郭麐曾感慨道:“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佛祖释迦牟尼一生悟出四大佛理,而贯穿着其中,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苦谛”,佛教云,人生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五盛阴苦。
纵观李煜的一生,几乎尝遍了上述八苦。在他的词中有不少写“病”的词,这是因为李煜本人经历病痛折磨,以“病”字为题的就有《病起题山舍壁》《病中感怀》《病中书事》。其中,《病中感怀》有言:“憔悴年来甚,萧条益自伤。风威侵病骨,雨气咽愁肠。夜鼎唯煎药,朝髭半染霜。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词中反映李煜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本就愁肠百结,雨连绵不断仿佛像自己心中理还乱的愁肠寸断。夜里围着孤苦熬药,一早醒来发现胡子已染冰霜。人之衰败并非日月相推,寒来暑往,一朝一夕间即可崩塌。作这首词之时李后主年过三旬,受病痛折磨,身体日况愈下。加之李煜天生性格懦弱,多愁善感,因而五阴炽盛,受色、受、想、行、识所困,八苦蜂集。《病中书事》云:“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涂侵。”《病起题山舍壁》又云:“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病中的李煜饱受“病苦”折磨,周围又无人可吐露情感,只得将心中悲苦抒发于词中,词中出现“空王”“无生”“空门”这样的佛家用语,可窥见李煜词中所表达的佛家“空观”。李煜的三十余首词中,“空”一字被使用高达十三次。《菩萨蛮》中“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一句,以“事已成空”作为李煜的一生总结也最为合适。从威仪天下,尽享荣华富贵的一国之君到一个毫无尊严的阶下囚,人生起起伏伏恍然如梦,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
李后主除了受病苦折磨,还受老苦之摧残。在《破阵子》中他写道:“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他怎么也无法接受自己从接受叩拜的帝王变成了任人宰割的俘虏,这残酷的现实让他深感自己犹如潘岳一般,年不过四十却早生华发,这一描写表达出自己日益衰老的痛苦。在《九月十日偶书》中:“自从双鬓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虽然他已两鬓染霜,可他已无暇顾及,只能以对酒当歌、抒发胸中愤慨来实现最大的自我超度。这里除了对衰老的体验,更多的是一种对不能掌控人生的无可奈何,悲从中来。
李煜词中还有诸多表现手足别离的伤感,即爱离别苦,例如《清平乐·别来春半》:“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首词是李煜因思念弟弟李从善而作。上片道出心中离愁别恨,在恼人的春色里触景生情。下片中,“离别却如春草,更行更远生。”这个结句意在讲“离恨”如春草,无穷无尽,无法摆脱。而人亦无法摆脱这自然之法。词中似乎参透了自然界的法则,抒发出自身厌世的悲观主义思想,他所描写的这种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轮回又证实出了佛法的奥义。
死苦对于李后主来说,无疑是最深刻的体会。在李煜二十八岁时,仅有四岁的次子仲宣突然夭折离世。“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这是李煜经历了丧子之痛后写下的一首悼诗。句中的“空王”两字为佛的尊称,因佛空無一切邪执。该诗意在表达:佛应该是思念我了,然而我这个“穷子”却在回家的路上迷失了方向。这里又用到一个佛学典故,佛曰:“我爱天下众生,他们都如同我的亲生儿子一般”。李煜将佛家故事放入诗中,是希望借用佛教慰藉自己,虽途穷日暮,却思佛度人。
再到爱妻大周后辞世,李煜写下了长达千字的,也是李煜所有传世之作中最长的一篇《昭惠周后诔》。他在词中详细描绘了与周后的往昔生活,写尽周后的聪颖美丽。最后倾诉了自己肝胆欲碎的悲伤。全文中共用了十四个“呜乎哀哉”,二十二个“哀”字,词中“抆血抚榇,邀子何所?”“吊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无极”等句极言表现李煜的痛心疾首,肝肠寸断。直至最后一句“呜乎哀哉”结束全词,面对爱妻早逝,尽管之后李煜与小周后结婚,生活也比从前更加奢华放纵,但后主依然无法排遣心中困苦,便常出入佛寺。每日下朝之后,与小周后穿上袈裟,念佛一声,罪灭河沙。在经过这些人生中的重大打击后,这一时期中,他词作中的悲剧色彩便愈发浓厚。
随着他身边的亲人、爱人的接踵离世,国家大势不可逆转,所有的悲苦已让李煜措手不及,跌入谷底。家破国亡,无处抒发,这正是他心病所在。佛家的教化在这个时候似一块浮木,使李后主找到了倚靠。佛家教义告知他:只要多多行善,处处积德,佛祖就会保佑。佛家为信仰者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慰藉,因果轮回,报应不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煜如此执迷于佛家,追求解脱。陆游在《南唐书》卷十八中感叹:“呜呼,南唐偏国短世,无大淫虐,徒以寝衰而亡,要其最可为后世鉴者,酷好浮屠也。”甚至在宋军围困,破城之前,李煜还跪在佛堂向佛祷告,对佛像承诺,若是宋军退兵,愿为佛身镀金身修佛寺。可是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暗懦无能的皇帝,南唐王朝终究是在青烟缭绕之中轰然倒塌。
比起病苦、死苦,对李煜来说,亡国之苦想必是最令他痛彻心扉的苦,也是李后主着墨最多的地方。当一个人面临的悲苦到达顶峰时,他的内心的情绪才可以激发他的作品情感达到饱满状态,千古名句就此诞生。“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那回不去的天上人间,这又是多少离合悲欢,多少忧愁惨淡。“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妻子被夺,心里满是愁绪,抑制不住的心乱如麻,如何整理都是凌乱。再到《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作完此词,宋太宗赐予毒酒,《虞美人》也成为李后主的绝唱。小周后悲不自胜,随之殉情,这对苦命鸳鸯最终尘归尘,土归土。面对命运的无奈,李煜束手无策,通过“离”、“愁”、“恨”这样的极富情感色彩的字眼来表现内心的苦,这些字眼是李煜凄入肝脾的写照。
叶嘉莹教授曾讲到:“李后主的词是他对生活的敏锐而真切的体验,无论是享乐的欢愉,还是悲哀的痛苦,他都全身心的投入其间。我们有的人活过一生,既没有好好的体会过快乐,也没有好好的体验过悲哀,因为他从来没有以全部的心灵感情投注入某一件事,这是人生的遗憾。”叶先生推崇的已不仅仅是李煜的文学造诣,更多的欣赏他倾注到词作中椎心泣血的真性情。李煜一生颠沛而又痴心佛学,这份对悲苦的真情体味是同时代甚至后世的大多数书写者无法超越的,也许就是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传唱不绝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陈葆真:《李后主和他的时代 南唐艺术和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宋静:<浅谈李煜词的宗教色彩>,《安徽文学月刊》( 2009年5月).
[3]方立天:<佛教“空”意义解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06期).
[4]赖永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