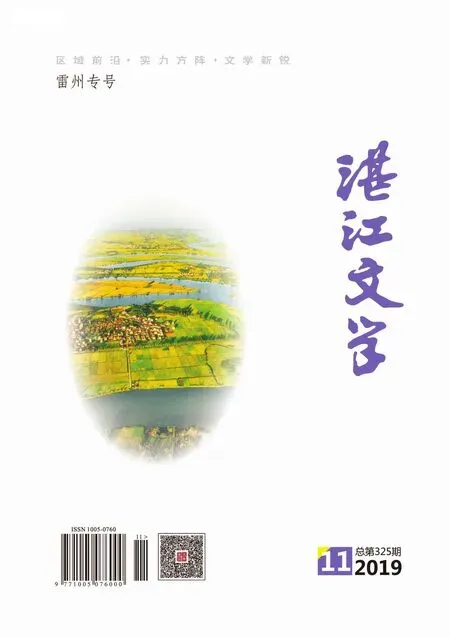老 屋
◎ 砾 央
对家的忆念就是对老屋的铭记,老屋承载着岁月的深情厚意。
老屋是家乡那时常见的硬山顶三间前楼后瓦房。
新年前夕,老屋的子孙们鸟儿一般从四面八方飞回她的怀抱里,吱喳的欢欣驱散了老屋平日的清冷。
房间不够用,晚上睡觉时,孩子们自由配对,竟置我于无床可睡的地步,只好跟父亲一起睡在中堂的大床上,父亲睡在里面,我睡在外面,与小时候的位置刚好对调过来。
晚上九点,在城里正好是最拼的时候,而老家的网络差得连页面都打不开,再说也不想打扰家人休息,也就上了床。生物钟被打乱,一下子难以入眠,记忆兀自活泼泼扑腾起来,依然带着归巢鸟儿的激动。
现在所睡的这张床我是熟稔的,小学四年级前一直与父亲睡在它上面。耳畔又回响起深夜归来的父亲的敲门声,看到我一骨碌掀开被窝小跑着去用力拉开门闩,紧接着一阵风似的钻回被窝,灌耳而来的是门页被打开的啪啦声与父亲哒哒的脚步声。小时候我很怕父亲,怕到与他睡在一起都拘谨的很,脚都不敢磕碰一下,偶然磕上也触电般撤离。冬天夜里,母亲巡夜时老是责备说被褥薄不耐寒,两人之间怎么还保留着可以睡一个人的距离呢。在母亲看来,父子是应该亲密无间的。
上了五年级后,母亲在北边房摆上一张床,北边房之前一直用来堆放家什杂物的,并且把家里唯一的书桌也挪过来给我用,从此我独自在北边房读书作息。农村人不懂什么成人仪式之类,只知道到了一定的年纪,就给孩子腾出一间房,让孩子在独立的空间里自主面对,体味生活,淡化依赖感,这其实是“心理上的断乳”,比什么花哨的成人礼更有仪式感,更有存在感。每逢除夕,我会把一年来收藏的图画取出来,大多数是影视杂志里的插页,利用父亲贴春联剩下的香糊把它们糊到破损的墙壁上,父亲有时候还在旁给予指导甚至帮忙。那些贴在墙上的明星画无一例外是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像一枚枚饱满的太阳,精神抖搂地照耀着我独处的时光,让我忽略了墙壁的斑驳,增加了对人生无限可能的悠然向往。那时的明星给予我的无疑都是正能量,只是不知道那时的我算不算是追星族的一员?
结婚时,住在南边房的母亲与我对调到北边房来,把南边房让出来给我作为婚房。在这样的调换中,我的角色又完成了一次更换。女友第一次跟我回老家看房间,看到了灰块剥落的墙壁的狰狞,担心姐妹们会嘲笑她,父亲获悉便在南边房铺上瓷砖,重新粉刷一遍墙壁,置上一床一柜。南边房的“现代化”与中堂、北边房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有时候我甚至会为自己享受独特待遇隐隐约约感到不安。
南北房侧面都开有一扇窗户,无所畏惧的天光总是从那扇窗户悄悄爬进来的,先是瞧见窗玻璃上浮现光亮,由弱变强,渐渐看得见屋顶的水泥梁。别的人家都是用木梁,我家却用水泥梁,水泥梁沉重得很,记得当年上梁的时候阵容强大,两排人马齐心协力分别吊住水泥梁的一端,叫着号子慢慢往上提。我问父亲为什么不用木梁,父亲说,水泥梁不会有蛀虫,更耐用。一个房间横着十一根水泥梁,都是直溜溜灰扑扑的四棱柱,屋梁上面是纵向排列的椽子,椽子上面覆着鱼鳞状的瓦片。懒床的时候就望着深邃的屋顶出神,灰白的屋梁,被雨水沤黑的椽子与沤白的瓦片共同厮守着一方屋顶,共担风雨,苦乐与共,该有着怎样的默契。
南北山墙顶端各分布着一溜回字形小窗,小窗曾经是麻雀的暖窝。当年我们常常偷爬到屋顶上,侧着身子掏麻雀窝,那窗中间的孔最大,也不过仅容三指,但这已足够。只要有麻雀在里面就在劫难逃。在那尚未实现温饱的年代里,香喷喷的烤麻雀肉的吸引力是难以抗拒的,尽管大人们三令五申不得攀爬屋顶,那可是高出地面七八米的地方呐,但天天劳作的大人们如何管得了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们呢?空子只要钻总是有的。
中堂位于房子中间,两边没窗,好在与南北房连通的过道没有装门,两边窗户的光亮得以映射过来,尽管如此,光线还是暗淡了点,无形中又增加了中堂肃穆的气氛。中堂的正墙上摆放着祖先的牌位,凝重而庄严,我的眼光从来不敢轻易往上扫描,甚至一跨进中堂的门槛都感受到一种威压,关于荣耀梦想的,我只在心里默默激励自己,决不能虚度人生,要活出自己的样子……
家乡是一个有六七千人的大村庄,市场只有一个,要买新鲜鱼虾就得在凌晨四五点起床。
老屋的房门是老式木门,仿佛吮吸了岁月的含混与沉闷,开关时总会发出钝响,母亲窸窸窣窣起了床,蹑手蹑脚把木门拉开一道缝,扁着身子从门缝里挤了出去,不想吵醒儿孙辈。母亲总是说十睡九补,总是设法让年轻人多睡点。而她注定要早起张罗一家人的早餐,她认为作为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在这天经地义中母亲忙碌了近半个世纪。
在母亲的小心里,我听到母爱像深秋的叶子簌簌而下,覆盖了我的心野。我也听到父亲的鼾声,遥远而熟悉的记忆又在鼾声里起伏着——
老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成的,父亲说老屋在当时算是不错的了,总共大约花去五千元,大半款项是借别人的,母亲直至今日还念叨着愿意借钱的那位乡亲的好。
因为钢筋少的缘故,为增加承重力,在前楼设计了两根水泥圆柱。这两根圆柱在童年的我眼里简直就是两棵生机无限的大树,我几乎天天尝试着征服它们,双手环住柱身,双腿上蹭,往往因为手短、圆柱光滑而半途而废,然而正是这种挫折感激发我的征服欲,我不断挑战着自己。等我的双手能够环住圆柱,噌噌登顶的时候,它们对我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人生路上许多事情不也是这样的吗?
当时建造的房子,前墙都是用一面平整的大石块砌就,然后用石灰把石缝填充成阳线。老屋建筑时前后墙用的都是小方块石,砌得很不均匀,仅仅填石缝不够美观,父亲干脆用水泥把前墙抹平,然后再在上面勾勒出阴线,于是前墙便呈现出方格形状,涂成绿色时,这面墙在我眼里便是沟渠纵横的田园,我想象着稻浪翻滚、蕉叶摇绿、瓜果飘香的情景;涂成蓝色时,它便是一片海洋或者一方天空,鱼跃鸟飞的活泼泼画面令我心醉神驰……那面墙简直就是我梦想的画布,斑斓着青春的七彩。
所谓的前楼,只是类似于骑楼的屋檐,大约宽一米五左右,主要用于收获时节晒谷。当年夏天酷热时,一家人爬到上面露天睡觉,父母怕我们睡觉不安分掉下去,他们便睡到外边,把我们拦在里边。仰望着墨蓝天幕上那些星星,眨巴着调皮的金色眼睛,似乎洞悉我的心事,在准备着开我的玩笑。以致后来一看到“星星知我心”这话,脑海里马上闪回那些夏夜温馨的画面,如今想象得到的浪漫也无非如此。
瓦房自然是用瓦片覆盖着屋顶的。瓦片有两种,乡亲们称之为“瓦公”与“瓦母”,“瓦公”窄而拱呈半圆形,“瓦母”宽而微拱,两片“瓦母”拼接在一起,合缝处就用“瓦公”和着水泥拢住。在群众的口头里,“公”与“母”就如传统文化中的“阴”与“阳”一样稀拉平常,相互相成,不同的是它们更接地气,通俗易懂。
从地面到脊梁高近八米,室内长宽各四米,如此高大的房间,夏天凉爽,雨天便近乎一座琴房。小雨沙沙沙,那是小提琴拉的小夜曲;中雨大珠小珠错杂弹,那是钢琴弹的奏鸣曲;暴雨哗啦啦,那是琵琶弹的十面埋伏。狂风暴雨,那是朝天鼓,震天动地的感觉都有了。遗憾的是,我缺少一对善于辨别音阶的耳朵。
半岛多台风,每次重量级台风对瓦房都是一次严峻考验,弄不好瓦片会全部被刮光。台风回南时,屋里的父亲披着雨衣眼光像探照灯一样不停扫描着屋顶,谛听动静,一旦有险情出现就马上爬上屋顶用身体去做补丁,否则,只要狂风撕开一个口子,屋顶就有可能荡然无存。这时候,母亲总是羡慕平楼,就因为平楼有着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坚固。
室内的墙壁是用三合土灰浆抹平后再涂上石灰的,岁月的潮湿腐蚀它平整的表皮,不少地方有气泡状隆起,不久就会剥落,露出里面的三合土来。母亲看见了很在意,有水泥的时候,就着手修补残破的地方,于是墙壁看上去就像打了补丁的衣服一样,一经打眼岁月的沧桑就爬满心头。
地板是水泥铺就的,大雨过后,潮湿的痕迹一团一团的,看上去透着冷气。院子里是泥沙地,鞋子总会把一些泥沙带进来,踩在上面嚓嚓作响,宛若老屋萦绕在耳的故事。
父母一起胼手胝足建造了老屋,老屋凝聚着他们的辛酸与欢乐,也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快乐的天地,从此关于家园的记忆一树树花开,灿烂在心灵深处。
在故乡,建一座新房子是一个男人一辈子的最大梦想,也成为大家评价一个家庭的基本标杆。如今时代变迁,年轻人都往外跑,不变的是祖屋依然是评价一个家族的重要标杆。前面邻居的儿子生财有道,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房子,这给父母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母亲由此有了心结,她说祖屋是我们的根,不管飞多远,都要回来,极力反对我们成为外乡人的想法。我们考虑的是物质上的利益,而母亲更多是考虑精神上的利益,我们不想拂逆母亲的心愿,一起商量,一起规划建新房的相关事宜,母亲在旁边竖起耳朵倾听着,脸上堆满幸福的微笑……
父亲的鼾声停住,摸黑翻身要下床,努力不弄着我的腿脚。我说,爸,我醒了,开灯吧。今天是除夕,得早点去购买抢手的做年必需品菠菜、豆腐,父亲牢记着自己的使命。
父亲说,天还没亮,再躺一会吧。
听见中堂木门咯噔一声打开了,外面黑乎乎的一片,耳鼓里涨满此起彼落的鸡声,我抓过手机,躲在被窝里,记录下我在老屋庇护下的暖暖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