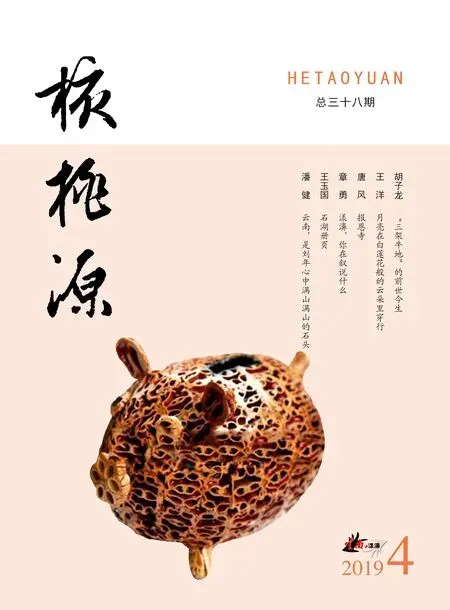漾濞,你在叙说什么
章 勇
漾濞是一座城,我曾经把它想象成如大理南诏国城墙一般的厚度,以抵御外来入侵,高耸旗杆,掩门屯守。或许我不该这样想象,因为想象往往把一个人带至虚妄的地方。若在这样的地方呆久了,势必会影响自己的的判断。
昆明、大理、漾濞,有着共同的特色,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蓝天白云、山河云谷,求大同存小异。长水机场的边缘地带,远望有一处城堡似的沙漠之上的建筑,近看竟然是居民区,当时我很惊讶,那宽厚、深沉与荒蛮的气息,仿佛把我带入充满漫漫的沙丘之地,正如俯向这无比强烈的耀眼的光源,不禁令我视觉紊乱。
高原的路,已经向我展开和延伸,像披挂银光鳞甲的长蛇。抵达漾濞,已是夜晚。彝族风情的夜宴,别有情调。我被漾濞作家的热情与思想所感染、感动。感动是潜意识里发出的声音,真挚且缠绵。
深夜后,小城万籁俱寂,苍山无语,只几颗残星,便把夜色点缀成美丽如同动人的童话。云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从来就不寂寞,壮丽雄伟、豪气苍茫,诸多怀有逐鹿之心的代表人物层出不穷,比如文有姜亮夫、武有龙云等。姜亮夫通晓敦煌,举世闻名;龙云主政云南,修建著名的滇缅公路,堪称中国战时的救国通道。对于这些,置身漾濞,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漾濞城建在滇西高山峡谷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漾濞江流经小城长年不绝。无论清晨或者晚上,这里的脚步,都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有民国时期的作风。当然,在这里人们的笑容似乎就是人生的主题,来去的人们互相打个招呼,脸上总是笑容满面。宛若愁苦与他们无关,就像是弹丸之地的人间天堂。我不用考虑这些,我最关心的是我在漾濞的日子,将带给我怎样的生命感受。
出漾濞城往西是富恒乡,车子行驶在山道,两边的山峰青翠欲滴,就如两个姑娘挽着手迎面走来。妻欣喜地拿着手机,不断隔着车窗玻璃拍着一路风景。她说,这里的景致果然不一般;我说,你不会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吧。妻子是典型的北方人,在未来云南之前,到过的最南的地方就是皖南,所以她对南方具有天生的期待感。
说实话,我们从遥远的北边过来,在老家几乎没有见过如此险峻的山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初上九华山,觉得山道弯弯悬崖峭壁甚是吓人,而今比起漾濞富恒山路的险势,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山路险峻,路面却平坦,加上司机师傅的技术娴熟,任何的担心显然多余。约四十分钟,车子终于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顶上停下,下车后突然感到一股寒意侵袭而来,随行的漾濞作家告诉我,这里的气温较山下温差可达五到六摄氏度。而这里的红杜鹃漫山遍野、盖天铺地,主色为红,丹唇皓齿、眄视流盼。
山谷间,抬眼望天。天很蓝,蓝得像洱海,无一杂质,白云绕在头顶,有如巨幅浮雕。这个地方叫石竹村,自然风光凸显地域特色,草木青青、花香幽幽,让人不知身在何处。杜鹃花如火焰热烈,又像红绸舞动。宋代诗人杨万里云:“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映山红,即杜鹃花。一片红艳,灿若云霞,用心欣赏,会留一春妩媚。
在一处地方,我常把风光与该地的生活联想在一起,尽管这里美不胜收,但因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的确有些滞后,不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里的彝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尤为值得尊敬和钦佩。通过短暂的接触,从他们载歌载舞时脸上的笑容里,便可知晓他们的快乐如何而来。据悉,这样的彝族民歌舞蹈被称为“打歌”,至于为何称为“打歌”,我现在尚未懂得。不过这种以民间自发形式组成的舞蹈队伍,在云南并不少见,只是其乐舞的内涵和原创性,绝对有着地域文化的优势。所以,善良的石竹人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本线装的书,不管生命有多少种形式,但在这个世界上,过自己喜欢过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活自己喜欢的活法,就是最好的活法。
这种活法足够简洁,而这种简洁虽不耀眼,却令人心动。石竹村的男人女人那一颗颗朴素的内心,就是大浪淘沙后在生活的海岸上留下的一份从容与宁静,不忘初衷的守定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即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云南“打歌”,皖南“送春”。在我看来,好像一对姊妹曲,皖南“送春”一般四人一组,挨门挨户唱,见什么唱什么,七字一句,唱声刚落,锣声又起,实在热闹。当然作为珍贵的传统文化记忆,对于每个人而言,是滋养心灵的精神家园,石竹村“打歌”完全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申遗不是手段,而是提高人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更是传统文化研究与保护的索引。
在石竹,红杜鹃宠辱不惊,精彩并不随着光阴而枯荣,它的内敛与娇艳除了欣赏之外,还可以用来思考,其华而不贵的内质,调动着我们最敏锐的触觉,让我们变得诗人般多愁善感,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起努力思索着前世、今生或者来世。早年去过广西博白,那里的乡民“做社”活动十分壮观,生活气息很浓,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它比鲁迅小说里的社戏节目更具现实意义。而石竹的“打歌”相对“做社”毫不逊色,甚至在文化意义上给人产生的激越感要强烈许多。看着这些“打歌”的彝族青年男女们左手牵右手,跳着欢快的舞蹈,很难不被他们的淳朴民风所打动,那一张张被晒出高原红的脸庞所展开的微笑具有浪漫天真的诱惑力,这种化繁为简的生活力量,让路经此地者,当即理解简单就是幸福的道理。与石竹对视,不觉间产生相看两不厌的绵长情意,其至上境界的精神高原就在“打歌”者们跳舞时手指的方向逐步升华……
看中国版图,南方非常遥远,而此刻,我脚下的土地,确是实实在在的彩云之南。春天在这里行走,美丽风月无边,一种宽容的生命情愫,跃然心间。当我在崎岖的山道边,看到写着“滇缅公路”字样的石碑,凝重和激励同时在心中泛起。
抗日年间,日本全面封锁我国所有的海上交通以及主要铁路交通线,战事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主政云南的省主席龙云受国民政府令决定开辟一条通往缅甸的国际运输通道,以接受盟军援华物资。这条公路的漾濞段自下关一号桥开始到漾濞县太平乡和永平县北斗乡交界处的胜备桥为止。漾濞当地掀起爱国热潮,无论妇幼还是老人,齐上修筑工地,极端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一些筑路工人为此奉献了宝贵的生命。
无言抚摸石碑,百感交集,眼前模糊。毕竟它是无数人流血流汗铸就的伟大工程,国难时的一条救国通道。历史不会停滞,只有前行,先来的行者留下脚印,后边的过客沿着脚印走过,于是脚印越走越深,滇缅公路不会在没有硝烟的日子里,形影相吊,独自孤单,即便在新的一个时代,它依然迎风站立成不朽的身躯。遥想曾经金戈铁马、狼烟四起的岁月,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和久远,禁不住感慨万千。民国诗人马佩瑲的《筑路励民歌》写道:
筑路难!筑路难!
切山坡,就平洋,
遇山河,造桥梁。
滇缅路遥数千里,
百日工程不计短与长……
一闻漾濞,隔世沉迷。漾濞的美与自然,对我来说,是一个永久的诱惑。那天下午在去往石门关的途中,蓦然,天道地理从脑壳中闪现。古往今来,一切科学证明人为制造的景观,相较于自然形成的鬼斧神工显然失色很多。
石门关位于漾江东岸,距离县城八公里。何为石门,乃是两座高数百米的断崖峡谷在苍山背后的江边,形如两扇巨大的石门,清流飞瀑,奔泻而出。其形状堪比安徽的丫山,丫山是一座高入云端的主峰中间凸显一个裂口,呈丫字形状,从而得名。据说地藏王菩萨见此美若天界,不意落脚时过重而将山峰踩成一个丫形的口子。我不知道石门关的关口是怎样形成的,或是地表板块发生张裂而导致,或可能拜什么神仙所赐,总之让人神往。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绝对可以无言秒杀同类。石门关的美层次分明,一段小桥流水过去,仰首即见天开的石门;远看石门关,山形美观,峰如刀刃,在阴雨时的半明半暗中,绵延的脊梁依然挺拔伟岸。
站在石门关前,浮想联翩。我很明白,但不能说,原来心里惦念这里很久。我没有和同行的朋友走进石门关的内涵,只停留在关门外独自欣赏千姿百态的石头、溪水和那些深邃而峻峭的线条。许是高山旁,气象瞬时变化,只要一片乌云飘过,天上便下起一阵雨,游人来不及躲雨,全身上下皆被淋湿,这时伞就吃香起来,卖伞的小姑娘忙得脸上堆满亲切的笑容。而风也是这里的常客,来去无踪的风,在游人歇息之时,充当着解乏消疲的角色。在石门关,我坐在一块大石上和一个老人攀谈起来,老者来自台湾高雄,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石门关这个地方的,他说是跟团来的,当时我在想,台湾居然有旅行社组团游玩漾濞石门光,可见石门关的名气有多响。山是大山,关是奇关,体像卓然,殊今异古。明代诗人徐伟在此留一对联“天开石门千古奇卉,寺云福国一往长奇”就很形象地道出了漾濞石门关的仙山琼阁与气度不凡。
在漾濞,难免会触动漾濞江的神经。当我们一行人步行到漾濞古老的街道,与神圣的云龙桥共同谛听岁月的足音时,沉重的时间压满博南古道,一目荒凉的悲绪,一眼宏阔的壮美,就如一种摄人心魄的大写意。这条老街尽管不长,只一华里,却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马帮不断,铺满百代旷世的岑寂。想当年,这路上骆驼成列,驼铃声响,车马喧嚣,雄风浩浩。几处马蹄印痕,像纪念碑似的矗立着厚重和孤独,向历史宣告,这里曾是神秘而又文明的繁荣之地。
而古道沿江,则是澜沧江在云南境内的最大支流——漾濞江,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同为祖国滇西高原的四姐妹。每逢七、八月雨季,亦不逊高原大江之色。它时而满川洪涛,时而一江雪浪,时而若群马奔腾。以摧枯拉朽之势,移山填海之姿,奔流在莽莽的横山断脉的云层中。据永昌府志载:碧溪江,一名神庄江,一名漾水。因黑惠江、源出剑川,经赵赕绕苍山之西,与漾水合流,即谓之漾濞江。同行们已经走上云龙桥,我依然在江岸停留,不停用手机拍下云龙桥下的长年流水,用我的感官、我的心灵和我的情感,记录它的狂放不羁、濞焉汹汹。或许妻生怕我被落下,在云龙桥上不断地喊我,然此刻我似乎被这一条漾濞人民的母亲河吸引住了,舍不得离开,因为我要在心里整理它,把它整理成册,在孤独的时候慢慢阅读。
见过很多桥,但却少见铁索桥。
云龙桥就是铁索桥,位于大理西北四十里的漾濞江上,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铁索桥之一。桥长53米,由九条钢览临江飞跨。传说一日清晨,忽见一缕彩云在漾濞西角绵亘江上,如同蛟龙过江,民众认定是神龙显灵,示应新选桥址就定于此,遂在此江面上建起铁索桥,并形成漾濞一景“铁锁云龙”。三十年跨度的两部电影《五朵金花》和《奇情侠侣》都曾在此取景。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写道:“抵漾濞。居庐夹街临水,甚盛。有铁索长桥在街北上一流一里……渡漾濞之水”。因而,铁锁云龙虽藏在云南大山里的漾濞,却承载了博南古道一部不朽的文化。伫立在云龙桥上,人走过时摇晃的桥面,仿若马帮铃声从遥远的时空中穿越而来,充满着悠悠动听、悲怆激怀的故事。
我从桥上走过去看对岸的漾濞城,希望从这个角度看到小城的波澜不惊和厚实的胸膛,然后返回原点,想象突然交叉于现在和远古,思绪在桥面一点一点的延伸之中逆流而上。我看了下时间,已是上午十点三十五分,此时此刻,我觉得应该留影,留影是为了留个念想,哪怕这个留影在手机里保存一个时辰一个夏季,都不是偶然的一个姿态,虽然云龙桥早已完成它的使命,但永远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它的高度并不因其自身的立体尺码来考量,而是立足在坚实的茶马古道,铺下旷远的情怀,以及冷凝的火焰,把深深浅浅的脚印,伸向高山,伸向一切历史车轮转动的地方。
由漾濞江、云龙桥返程时,在老街走走停停,古老的房子里,已鲜见人居住,斑驳的墙缝里,长出了蓬勃的青草。穿行于漾濞的小街深巷,清风徐来,心情稍趋于平静。我喜欢这样的景致,沧桑尽管是对久远的一种回味,但透出的幽静、安适和气韵,不禁让人沉醉其中。
漾濞是著名的“中国核桃之乡”,盛产的核桃果大、壳薄、仁白、味香,有“全国质量第一”之美誉。在未来漾濞前,早就听说漾濞有个“万亩核桃生态园”,却没想到生态园居然深卧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上,这里有个村庄叫云上村庄,村名很美,坐落在高耸的云端之上,所以叫云上村庄。到过祖国很多地方的我,一入村庄,就被这里飞离尘寰的景致所震撼,四面青山环抱,山体郁郁葱葱,一切是那样的单纯,云雾、山空、绿树、草坪均自成体系。一千多年的核桃树,目能所及之处,比比皆是。天近黄昏,空气依旧清新,像是在一个美好的记忆中涌出,脚下的路仿佛不是在蜿蜒,而是在心头盘绕,随风而起,把人引入到纯朴善良的画面中去……这种美非任何地方可以替代,我不想用“神奇””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云上村庄,因为“神奇”毕竟有些夸张的虚幻成分,若用词不当,势必会给实实在在的人间美景大打折扣。于此,我决不忍心。
当晚,在精致的农家酒庄吃完饭,我们一行人便星夜下山,夜风格外的清凉,挟着绿的湿润。车前灯光吻过光所能及的花木和繁枝密叶,留下斑驳的影子。此时,夜的高原神秘、幽婉。一路上,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应属史学家张继强老师了,他学识渊博,健谈无人能及。他对漾濞地名来历的解读,似乎与漾濞江的漾水和濞水合二为一,微有相似之处,可不同的地方,又让人难解其意。其实不管能否认同,总之听者还是颇为受益吧。
我一直认为,任何的旅行,终究都要告别。漾濞有我看不尽的风景,如苍山西坡大花园、苍山岩画、白蛇下山、平尾古墓和脉地白王城遗址等等。
下次再来,因为这里有我熟悉的朋友,他们从未把我当做高原的外乡人,所以告别没有遗憾。看苍山上的白雪,也不会成为我久存心中的梦!
脉地道上
第一次去云南,就去了神秘的脉地。脉地深处滇西北的一个大山里,若不是友人带领,恐怕只能望山兴叹了。
阳春时节,百花竞放。我随着大理州漾濞县文联主席常建世先生来到他最钟情的地方,这里曾是他和爱人恋爱的天堂。他爱这里比爱诗歌更深重、更痴情。大理是个多民族地区,足有十五个少数民族集聚。而漾濞的脉地以彝族为盛,彝民们热情好客,总是拿出最好的招待客人。
这里四望皆山,峰岭之间,旁开一地。这一地就是漾濞县的脉地镇,距离县城约有二十公里。脉地之名的由来,尚不得知,但一定与著名的苍山一脉相存。春来百花百色,天公一支笔,在大地在山林涂抹,涂一次绿一分,直到绿意无限,看山山也醉,望水水生辉。可能这边的气温略高,当我们行至一个不大的村庄时,路边的油菜花朴素绽放,娇艳扰人。
我问常主席,这里的村民也种油菜?其实我对自己的问话毫无底气,生怕涉有无知之嫌。当然我来脉地的目的并非专门欣赏风光,而是慕名吃生猪肉而来。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都有名小吃,比如邯郸涉县的金丝小窝头和小米焖饭,又比如芜湖的四季春小龙汤包和耿福兴酥烧饼等。小吃就是小吃,理论上可以理解为以素为主。大理的素菜最有名气的可能就属“水性杨花”了,其色为绿,看似像水芹,是一种从水里捞上来的水菜,菜茎翠色欲滴、饱满圆润,看上去特别鲜嫩,吃起来口感很好,并且茎须上的花也可以一并入味。至于称其为“水性杨花”,我想大致是不甘寂寞的意思,一如妖艳的女子四处暗送秋波吧。
上述说的基本与素有关,而生猪肉这一菜名,无疑是一大荤,因此我把这道菜称之为“大吃”。虽然对“生猪肉”一菜产生过从未有过的新奇感,但猪肉前的“生”字,多少让我有些毛骨悚然,既爱又怕。有一种“长坂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眼圆睁”的古战场态势,此刻我能把生猪肉的“生”字与张翼德的霸气等同起来,可见内心对“生”的恐慌,需要培养莫大的勇气。
在脉地,我和常主席一路畅谈,海阔天空,没有中心,没有层次。他喜欢抽烟,我也喜欢。我知道他是一个内心绝对浪漫的角色,对生活对人生充满真善美,客观且真实。一谈到脉地的吃,他的表情郑重其事,说来到漾濞不吃“生猪肉”枉来此行。
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在村口恰逢一位彝族村民,大约五十来岁,黝黑的皮肤,眼睛闪烁着厚朴的光芒。他看见常主席,好像很熟的样子,疾步上前打招呼。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客气地笑着说:“老常,今天就给我一个机会!”话不多,却透出彝族人民的待客之道。
他在前面引路,我们在后面跟着,走过一道绕过一弯,看见一个山坡下一间新盖的两层小楼,小楼别具一格,楼层不高,砖木结构,屋顶清一色琉璃瓦,充满当地的民族风情。门前有两个身着彝服的小孩,在梨花树下,牵着手玩耍,彝服上落满花瓣,在斜射的阳光下,缤纷似雪,风过满地白。
坐在低矮而崭新的小木凳上,村民向我们叙说着这些年来的变化,神情愉悦,只有一点是他自己看不见的,就是他两只眼睛的表情,显出他有一个富于热情的灵魂。不过说话间,他有时会激动,每逢说到坎坷的人生境况时,眼圈竟然有些发红。
与一个彝民面对面坐着,我平生第一次。对于这些大山里的汉子,除了顽强的生存能力外,他们身上更具备水一般的柔情,许是受千柔百曲的漾濞江影响,温柔、平和,宁静和明亮。
聆听着两个彝民的普通对话,我始终处在感动中,尽管感动是莫名的,甚至如水雾一样的飘渺,但起码是清晰的、合符逻辑的。作为政府官员,老常的细心和柔软,这次彻底领教了。当村民一再邀请我们在他家用餐,老常手一挥,不加思考地婉言谢绝。出来后,我问常主席:“老乡这么热情,不怕冷了他那片火热的心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老乡们都忙,还是尽量不去打扰他们的好。”
眼看临近中午,我们出了村庄,乘上车子。车子奔弛在山道上,犹如一只饱蘸浓墨的笔,在崇山峻岭任意挥洒。
来到镇上,常主席约来几个朋友在一家饭庄小聚。
一桌菜,一席情。菜是风味小菜,肉是猪皮和生猪肉。大多我都叫不上名儿,在云南我只知道“水性杨花”,可是桌上却没有,我也不好问。席间,常主席呵呵地笑着,用手指着一盘鲜红的生猪肉说,“这就是生猪肉。”
生猪肉,鲜红细嫩。据说,传统的吃生猪皮、生猪肉必须新鲜,早上八九点杀猪,洗好弄好正好到中午饭的时间。常主席和其他几位云南的兄弟,毫不迟疑地夹着生猪肉放进嘴里,觉得他们神色没有异样,便也鼓起勇气从盘中夹上一块生猪肉,但一想到是生的肉,陡然产生一种抗拒。在座的云南朋友纷纷说,没事的,我们这边男女老少都吃的。
提到吃生肉,我想起水浒中的武松,他肯定很能吃,那种野性的英雄气,恐怕就是吃生肉而来。于是,我闭上眼,壮着胆子将生猪肉塞进嘴里,慢慢嚼了起来,其实生肉就是生肉,尽管吃起来感觉绵绵的、舒爽的,但若想直接吞下去,恐怕依然是件难事。
吃完生肉,我猛然喝了一口白酒,以解压紧张的心理。不过,要是蘸上辣酱、蒜泥、花椒配制的酱水后,再入口,感觉又不尽相同,而是甘之如荠,软烂还香。
大凡有酒的地方,就有诗歌或者酒曲。喝酒行令,即兴而为。云南兄弟们碍于我酒力有限,几乎不劝酒,如此我才能安心倾听彝族兄弟之间的文化交流,不然会很拘束的。我喜欢听歌,即便作文时也要放着音乐。酒兴正浓时,我们不知不觉聊起了音乐,于是大家便要求彝族的民间歌手王学军老师唱一曲。王学军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微微欠了欠身子,便唱起一首《父亲》,他说这首歌的歌词是改编常建世先生的诗歌《父亲》,歌词大意是:“瞄准城市,把笔直的身躯拉成弓,射出我响箭后,你隐居了,隐居到了安全的泥土里。”歌词真挚感人,余韵无穷。
王学军老师中等身材,戴着一顶鸭舌帽,下巴留着一撮胡子,形象具有艺术气质,歌声沙哑浑厚,声音很好听,清唱竟能达到如此境界,尤其唱到“父亲……父亲……”的高潮部分,我们听得眼睛都湿润了,那种心神合一的情景,就像一缕清风掠过我们的心潮,掀起千万层浪花。真正意义上来说,王老师演绎的歌曲还不是酒曲,但我们喜欢听,也就无所谓真伪酒曲了,酒曲可以恣意地唱,而歌曲《父亲》的艺术品质明显高于一般酒曲,这是不容置疑的。
当王老师唱起自己作词作曲的《我的小情妹》时,所有在场的人的心情一个个被调动起来,借着酒劲,大家都跟着忘情地唱:“我的小情妹,明天嫁人了……,心里的苦痛向谁去诉说,就让我再为你为你唱支歌,就让我再为你为你跳支舞,就让我再为你为你梳梳头,就让我再为你为你化化妆,我的小情妹,我的小情妹,你怎么忍心把我丢下……”
歌者心头有爱,心底有伤,一旦唱起来,往往融化忘我。听者亦是心动神摇,血脉膨胀。余音袅袅,绕心三日不去。于是再吃生肉时,已经不那么紧张了。我知道,这是歌的力量,在这块盛产爱情的土地上,以独具时空意念的歌词,涌动着一种生命的脉搏。
在脉地,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彝族人民的柔中有刚,敢爱敢恨的品性。之所以我把吃“生猪肉”称为大吃,基本来由于此。“生猪肉”虽然是大吃,其名字却充满狼性,而“水性杨花”则像一枚蝶,舞姿翩跹。不管怎样,这两道菜在大理美食史上完全可以相得益彰。
窗前的清风飘过,记忆便丰满起来。
脉地有如秀岭山上的梨花,芬芳美丽却远离张扬,更像深藏闺中的明珠,用心触摸才能感受其内在的光芒。
秀玲梨花山
没有一座城池或者乡村,能像秀岭一样对梨花的守望,其无比的坚定性,长期以来牢不可破。在过去的五百年,秀岭与世隔绝,睡在大山深处,单用美丽的词汇来描写它,就未免有些苍白和单薄。
悠悠山道远,骑鹤飞秀岭。在那青翠的、连绵无尽头的山脉,展眼望去,高高低低、蜿蜒千里的山峰,层峦叠翠。我乘坐中巴车驰骋于赋予心灵震撼的高原地带,驰骋于一种从未有过的雄伟和旷达。
我不知道前面究竟会有怎样的景象等着我,不过我的思想早已被苍翠的林莽所牵引。有人告诉我,秀岭是梨花的天下,是王母娘娘高兴时信手洒下的一把花籽。我对这样的传说毫不怀疑,反而以为凡是大美的地方就应该充满故事的神秘性,如此才有存在的意义。再往前,车子已达海拔近两千米的山顶上,前面的断崖路就像一湾流水阻隔了我们的去路,这时才知道彼岸在忽略了行而上的意义之后,可能就是我身体朝着的方向,眼睛朝着的方向,亦或是心灵朝着的方向。
面对眼前的绿山、梨花、蓝天和白云,同行的人们兴奋而欢悦。山已高,云也淡。薄纱般的云雾迷蒙飘渺,缠绕峰峦。数不清的梨树在阳光下坚韧屹立,烂漫陈情。一行人都去梨花树下观花、闻香、留影。常建世先生却席地而坐,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与我相谈起来。他的神情总是那么诡秘,语言不乏幽默。他是我见过少有架子的官场文人,他朴实而敦厚,心灵像眼前的梨花一样雪白。我想写梨花,无法绕开常建世先生,他的诸多文人的品性,即是梨花的又一见证。
在云南,不得不令人折服的是这里的地名,秀岭是一个行政村,隶属大理州漾濞县苍山西镇,无论镇名及村名皆美不可言。而这里的村庄,几乎与村名齐誉,虽不得章法,散落在岭上,星星点点,隐藏在高原深处,让人无法判断它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它可能在任何一条山沟、一面坡地或者一树荫下出现,它们会在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闯进你的视野中,即便是一张比例尺微小的地图也无法详细地标注出这些村庄,甚至令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村庄的存在,就是与其地名而相互印证着秀岭的秀美。
有时候,我真想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真正融入村庄,去聆听村庄最本质的声音,当然由这些声音而产生的主流状态,又可以说与梨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梨花使得村庄在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自得风水。站在梨山的高岗上,我的那颗滚烫的心早已随着那一瓣一瓣的梨花翩跹起舞。云南相对偏北的地方,春的气息更浓一些。且看,秀玲的梨花一簇簇、一层层,像云锦似地漫天铺去,在和暖的春光下,如雪如玉,洁白万顷,溢光流彩,璀璨晶莹。微风轻轻拂过,一些梨花瓣如破茧的蝶儿,于半空中飞舞盘旋,折射出绚丽的色彩。
身临这样的场景,想必很多男人都希望来一场邂逅的艳遇,因为秀岭,或者因为梨花。不仅文学,还有生活,这是个充满许多可能的时代,超出事实的暧昧和传说,以及委婉曲折的情节,也是完全客观存在的。梨花的灿烂,可以阻止一切的孤独,可以抵制所有的忧郁,它永远是春天里一枚永不落幕的棋子。曾经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一个心愿,要好好写一写我的初恋,写一写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牵挂,就好像一个不醒的梦,心湿了,无处晾晒。但在秀岭的梨山之巅,在核桃湾的乳沟里,依旧可以寻找到初恋的笑声,就像我飘摇的一生,从花枝招展的早晨到落英缤纷的黄昏,从容且淡定。梨花一点没有害羞的意思,在众人面前继续开苞绽放,在我三月的梦边,让风中的想象,丰富地膨胀,就像我追随了多年的爱恋,从遥远的记忆中飞来,掀起风暴,卷起云浪。
我忽然觉得,大自然制造的山天一色,使我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欢悦与惊喜。一切美好的智慧,一切的感性和理性,无穷无尽而不能超越。我只有回到现实中,梳理神经,不至于空手而来,虚掷光阴,从而珍惜每一次都不可重复的瞬间。
这时,从山坡下传来两个女声的对白:
“王姐,梨花真好看!”
“李白说,‘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她们的软语,柔和婉约,虽带有方言味道,不过朗诵的诗词我还是勉强能听得出来。
她俩一步一步走上山岗,我认出两位美女,都是当地的彝族小妹,一个丰满,一个纤细,燕瘦环肥,各具千秋。我不敢与之一见钟情,因为缺失完美的背景和词令。她们都十分热情,主动与我打招呼,闪烁的眼眸晃漾着温馨的芬芳。
我就这么近距离看着两个彝妹的丽姿与绰约,及至具象的模样,谓之似曾相识,这种像美文一般的成熟和娟秀,不禁让我对她们的风格给予辨别和鉴赏。
我非常期望温暖的文字能够唤醒四月的天空,幸福地传递梨花的悸动,装饰着我的梦,让我的心流浪归来,一瓣凝望,一瓣托住思念。素面梨花,心怀芳华的女子,倘若上天眷顾,必不坠其志,于生活,于事业,托风、托水、托云彩。
回到家乡,经常听到女朋友说,人到中年,仍然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我跟她说,去云南秀玲吧,那里是互诉衷肠最好的地方,两个人的风景独美,相依相偎,还可以泪如泉涌。何以安慰曾经的沧桑,唯有秀岭的梨山,更容易感受生命热烈的激流。告诉你,这里的一天,约等于上海的一年,悠远的梨香,写满了流云生动的抒情。
很想与梨花私奔,这是我去了秀岭之后的冲动,我的前生今世和她不过就是一篇文章的距离,我最真的希冀,宁愿舍弃一切,也要完成尘梦里的传奇。油纸伞、雨巷、栈道、古桥,有的太遥远,够的着的梨花,就在眼前,我不会在纯净的洁白里走失,也无需刻意的离开。
“满弓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唐代诗人温庭筠借喻梨花表达闺中女子一往情深,在明月相照,梨花盛开之下,月圆人不圆的情景。可见梨花不但能浪漫情怀,还有意拉长思念的影子。
说到温庭筠的“满弓明月梨花白”这句诗,我想到唐贞观年间的樊梨花,她的“梨花”之名必有其由来。据说,其父樊洪原为西凉国寒江关守将,樊梨花出生在一个叫梨花的小镇,小镇盖因盛开梨花而得名,恰好樊洪素爱梨花,便将小女取名“樊梨花”,以期小女像梨花般芳香、雪白。
古语言“玉可碎不可损其白,竹可焚不能毁其节”,樊梨花正是遵守如其名字一般的洁白,独立于世、不垢尘污,这样的清虚淡远之风,便是梨花与梨花的完美对接。梨花是美的,盖世英雄,天下无双,其使用的兵器落影追魂枪,上阵对敌一定也是像《三国》中描述赵云那样:“那枪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
我总是相信,一座花山最好的语言,就是帮助人们提升思想、认知美好。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其它更好的解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其实,诗意地栖居,确有一种诗意的向往或者诗意的等待,事实上,这远不是我的想象,因为我伸手即可触摸到诗人所期盼的美的内涵。
当我从思索中回过神来,秀岭的万亩梨山,正如北方漫天的雪花般敞胸开放。每一朵的绽放,都有其成长的履历,真实、妩媚、风情。由一座梨山进入,即便险峻,也要化风亲吻高原的泥土和这里的大片山色。
心事在此时行走,思绪飘逸,挑开内心,暗香盈袖,抖落一地洁白。人世轮回,万般流转,最美的时光就在看花的那一脉温柔,苍茫尽处,成就一帘幽梦。
秀岭村,梨花山。那个彝族少女,依旧在梨花枝下,听花开的声音,恬静、唯美、安宁。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她侧身的背影像株凤尾竹,婀娜轻柔。梨花若解语,相视入宋词,不要让梨花借走你的欢乐,只要妹妹把开花的季节,好好珍惜。
作为秀岭的外乡人,亲近梨山,寻闻花香,最后带走的只能是彝妹的歌声。我需要梨山把我的情怀留下,更难舍彝妹袅袅的身影与梨花相离,因而我把对秀岭梨山的爱恋,当作生命里随时蔓延的乡愁,恣意、摇曳,点亮清明。
——谨以献给漾濞5.21地震救援的消防指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