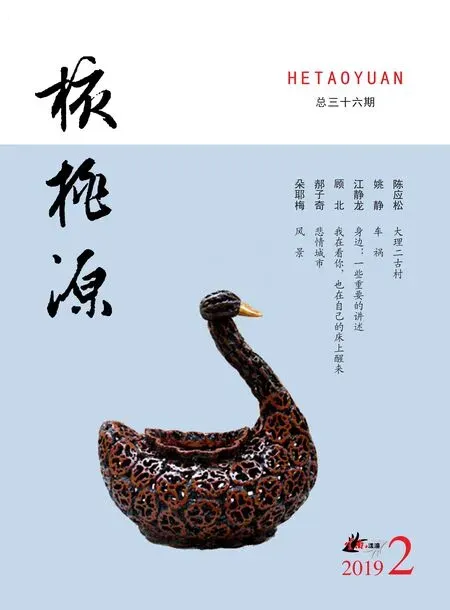明日小雪
李淑琴
不出所料,那天晚上吴老倔的老屋真的塌了。
雨一直下了七八天,刚开始没有雷声也没有闪电,白天晚上持之以恒地下。这屋子迟早是要塌的。所有人都成了预言家,只有吴老倔硬着一把脖子继续进进出出,压根不搭理这雨。垮塌的时候是后半夜,风挟持着雨,雷鸣电闪,朝着地窝村扑来,一次一次席卷吴老倔的房顶。风声雨声裹着吴老倔屋顶的瓦片泥沙倾泄而下,东角屋檐伸出的椽子断裂的残体,随着泥瓦冲到路上。
早起六点钟接到地窝村王天才支书的电话,我翻身下床,嚼了几口饼子,驱车赶到村里。一夜的狂飙,雨又开始温顺地飘着碎星。地窝村地处吕梁山腹地,面前一条断断续续的小河,背后是连绵的群山,几十户人家高高低低土豆一样散落在山坡下。据说这里经历过几次山体滑坡。这次组织派我到地窝村扶贫,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地窝村村民的困难,异地搬迁,让他们远离地质灾害。
我非常清楚目前的形势,扶贫攻坚已经到了冲刺阶段,可也理解村里的工作不好做。这次精准扶贫是一项政治任务,各村都在比着干,扶贫工作走在后面就要问责包村干部,追究包村包户干部履职不力的责任。
吴老的屋子我是在村里调查的时候看到的,西边连接的房屋已经拆去了一半,裸露出原先的泥坯和锯掉的椽头。屋子看起来年深日久,时间抹去了墙砖的棱角,墙角落满粉末状的尘屑。屋顶的瓦缝长出墨绿的瓦松,残缺不齐的屋檐像老去的牙床。地窝村的人叫吴老“吴老倔”,据说他曾强赶着一头驴上梯子,赶了一天,鞭子抽的驴屁股一道一道的血迹。吴老倔老婆前些年去世了,两口子没有孩子,领养了一个儿子早带着媳妇快快乐乐搬到留庄镇安居小区去了。而吴老倔的倔我是动员他搬迁的第一天就领教了的,当时他正追赶一只苍蝇,这苍蝇也很机灵,拍子举起它就飞到高处,围着他的拍子转,又挑衅般落到灯泡上。吴老倔踩着方凳刚举起拍子,就弯着腰咳嗽起来。那咳嗽像是从心脏里吼出来的,整个人都颤。蝇子又飞到碗沿上。快七十岁的人了,从方登上下来一个趔趄,恼火地把那只苍蝇拍得粉身碎骨才罢休。谈到搬迁,吴老倔只有两个字:不搬。问及原因,他把头扭到一边,瞪着窗户上的塑料片子,除了咳嗽了几声,一言不发,直到我们离开都没有转过来。
吴老倔不肯搬迁,拖了村子里整个扶贫工作的后腿,村干部和包村干部非常头疼。加上最近下着连阴雨,要是再出个人命,这就不仅仅是脱贫的问题了。国家拨资金建了安居小区,老区人民的脱贫应该走在最前面。扶贫办卢主任的话不时提醒着我,可是吴老倔任凭好话说尽就是那俩字“不搬”。现在一场雨冲坏了吴老倔的房屋,这纯属自然现象,吴老倔还有什么可说?
“放心!吴老倔还好好的,一点没事。这场雨帮了我们大忙。”我一走进村委会王支书赶紧拉着我坐下,背对着我倒茶,“我已经通知了几个人。一会三轮车来了,咱一起上手把吴老倔的家搬了。就他那点东西,几个人呼啦一下就搬完了。”
“这能行吗?我担心吴老倔的倔劲上来,这办法不灵,还会搞砸。”
“一会他坐你的车。我们把他的东西用三轮车拉走。天晴找个推土机把他的烂房子推了。这老头,国家花钱建了好房子不住,净是作怪哩。”
妇女主任、吴老倔原来的邻居陈俊彦和两个后生开着三轮车到了门口,车斗里放着一大块花色的油布。一行人心照不宣,把车开到吴老倔的屋前。吴老倔的院墙经过这些天的浸泡,好像戳一下就会塌掉,东屋坏掉的屋顶经过雨水的冲刷更加残破不堪,吴老倔搬到了西屋的火房,灶台连接着一盘土炕,旁边摆放着一只大口的缸,他正抡起斧头在灶台边劈柴。村子大部分都搬下山了,吴老倔捡拾了一些废旧木头,劈成一尺长,码在灶台靠墙的一角准备越冬。
妇女主任上前亲切地喊了一声:“叔,今天跟我去看看新家,你要是不想搬再住些日子,先看看地方,走。”她把斧头放在灶台上,拉住老倔的胳膊,陈俊彦也附和说今天专门陪他去看新家。两个人几乎是架着吴老倔上了车,根据王书记安排我立即发动了车,吴老倔夹在中间挣扎,抻着脖子蹬着腿,伸出胳膊拼命去探门把手,不住地咳嗽,憋得脸黑红,被陈俊彦捞着胳膊,像一只挨宰的驴。透过后视镜,我看见两个后生抬出了吴老倔的黑木箱子。
雨天路滑,车子跑不起来,六十里的山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留庄镇安居小区。吴老倔的新房在一楼,是个两居室,他坐在那里,看到随后抬进来的黑木箱子立刻明白了,蹦起来指着亮晶晶的窗户叫骂:“我操他先人的,这是欺负人哩。这真是活人眼睛里插柴哩。”
“甭管咋样,这老倔头是搬过去了。天晴道干就把他的房子推了,再把水电停了,给他断了后路。我就不信缠不过这倔骨头。”王支书在车上频频摸着头发,好像抹去了一桩麻缠事,“一会咱俩喝上一顿。这些天被这个老头累烦了。”
“这不行。组织上有纪律,滴酒不能占,吃个便饭我就回县里。”
晚上伏在桌前,我开始写本年度留庄镇地窝村帮扶工作总结,给扶贫办汇报工作的新进展。写到吴老倔,又想起他佝偻着腰咳嗽的样子。现在总算搬到了新居,冬天就不用受冻了。
可能白天在山里气温低,又淋了点雨,我也有点感冒,捂着胸口咳嗽起来。正在喝妻子端过来一杯姜汤,就接到王天才支书的电话,他有点气急败坏:“这个倔骨头,披着个破塑料袋子扛着铺盖卷又跑回来了!六十里山路,我是没办法了。真是狗脑袋不往盘子里装!”
我老婆说的对,吴老倔坚持不搬家一定有深层的理由。坐在吴老倔家门前的枣树下的一块木墩上,节气已经到了落叶飘零的深秋,发黄的枣叶簌簌飘落,天空已是湛蓝。一只流浪的黄狗柴草堆里觅食,村子里已经少有人走动。我咳嗽得肺都要咳出来,地窝村的问题解决不彻底,我放心不下,如果再来一场雨,我都不敢想。盯着吴老倔的老屋,我反思琢磨这个老头死活不肯搬家的理由。他就像一头犟驴,靠强拉是不行的,他会撞死到南墙不回头,摸一摸顺一瞬也许会拐弯。除了去吴老倔山墙边那个低矮的厕所,整个上午我一直坐在枣树下。吴老倔出来拿着小铁桶舀了半桶水,却权当我是一棵歪脖子老枣树。
中午的时候,我看见他披着旧棉袄夹在门中间,看了我大约一分钟,然后他走过来说:“我熬了两碗黄糖酥梨,对付咳嗽最顶事,看你咳嗽得不轻,给你一碗。”
有效果了。我立即站起来。且不说这梨汤管不管用,能走近老倔就有希望。吴老倔用白瓷碗给我盛了一碗黄梨汤,梨没有削皮,一片一片飘在上面,汤色有点发黑。他用的是黑碗。我迫不及待喝了一口,美滋滋地深吸一口气,表示呼吸很通畅了。吴老倔头埋在黑碗里,闻了一下,用嘴巴直接吃食飘在上面的梨。
“老哥,你咳嗽多久了?”
“我这是老毛病了,喝一碗黄梨汤就轻了。”
吃着热乎乎的梨 ,我忘不了自己的中心任务,探寻吴老倔心底的疙瘩:“我小时候比你还倔,不想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这是咱的个性,改不了!我说老哥,我知道你不想离开地窝村一定有理由。今天就咱哥俩,你的理由要是说得过去,从今儿起我再不动员你搬迁,咱把东边的屋顶修好,你在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在等人。”吴老倔用勺子把最后一块梨拨到嘴边,直直地盯着塑料布蒙着的窗户,指着东边,表情满是萧索。
我逐渐了解到,吴老倔要等的人是东边院子里胡振林。大约是三十年前,胡振林去集市上卖掉了几亩山坡地的玉米和糜黍,准备去广州深圳一带打工。当他卷起空空的麻袋,发现旁边一直袖手蹲着的女人站起来走了过来。女人脸色发黄,脸型消瘦,露出两只大眼睛,请求胡振林将他带走。这女人说她是山后面的,不愿意换亲才逃出来,因为对方是个傻子。如果胡振林有妻子,求帮他找个好人家。
天黑的时候,胡振林把女人带进了吴老倔的家里。吴老倔正在就着如豆的柴油灯搓玉米,漆黑的屋子摆了两筐子玉米。女人站在门口,调不开脚。胡振林指着吴老倔说:“妹子,我这个兄弟老实勤快,好胳膊好腿,就是不爱说话,但能靠得住。现在光景是紧巴了一点,几亩坡地也饿不着。”女人仰起头看看头顶,椽上挂着一篮子草药,晒干的叶蔓一旁垂落,倒是不漏风不漏雨的。吴老倔拽拽自己的衣襟,站起来拘谨地说:哎呀,你看我这黑屋子破厦的,哪能讨得起老婆?
胡振林二话没说,从怀里掏出五百块钱递给吴老倔:“给妹子买两身衣服,把北屋里拾掇一下,赶快成个家。”
吴老倔一看胡振林丢下钱,着急地跳下抗,把钱塞给他说:“你这是要出远门的钱,我不能要。”
“以后你有钱了再还我。”胡振林丢下钱,头也不回地走了。
胡振林刚开始在深圳,后来到了广州,写了几封信,随后再没有联系。吴老倔有了女人有了家,日子变得像模像样的。这地窝村只有四五十口人,多少年来汉子们找个媳妇费劲的很,不是招赘就是出山打工。吴老倔从不敢奢望娶老婆,却娶到了媳妇,更是加倍心疼。女人被日子滋养的肤色红润,房前屋后的空地上也种满了蔬菜,让地窝村的老光棍们眼馋得要死。
吴老倔一直在等胡振林回来,可是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还是不见胡振林的踪影。
我问:“老哥,你就没有找过他吗?”
吴老倔说:“中间胡振林回来过一次,可是当时我老婆正好生病住院,我不但没还他钱,他还又借给我一笔钱!”停了半晌,吴老倔又说,“我知道他刚开始在深圳,后来就找不到了。他姐姐也去世了,但是他肯定会回来的。你不知道,我那时到表哥家里借钱都是空手出来。胡振林是我恩人,我必须等他回来。我不能搬,我还要给他照顾房子呢。”
“你就这么等。万一他不在了呢?毕竟已经几十年了。”
“人死债不赖。他总有后人的,咋说他也要落叶归根啊。”
“你看大家都搬走了,村子里条件越来越差,万一山体滑坡,或者你看这房子撑不了多久了……”我没敢往下说。
后来,吴老倔是在胡振林的院子里吐血送到医院的。
那天,王天才带着推土机把吴老倔原本残损的东屋拱了一下,警告他再不搬家就推成平地。屋子摇了一下,半扇墙体立马消失了。
吴老倔正在胡振林的院子清扫落叶,看到推土机在吓唬他,马上唾沫四溅叫骂起来:“你推!你推!你有本事把老子的房子推平了。”
“我给你说,胡振林已经死了十年了,人家孩子大学毕业不知道在哪里工作。就是找到了,你以为人家会眼热你那点钱?飞机票都要好几千,你高低不要作怪了,不要再折腾扶贫工作组了。你有那几百块钱给根娃子添点啥。过几天就立冬了,再不搬家村子里就停水通电。”
吴老倔举着扫帚朝王天才扑过去,还没有到跟前,一阵强烈的咳嗽使他停下来,他抚着墙不停歇地咳,软软地倒在地上。
我赶到中心医院的时候,吴老倔已经走出了X光室。医生是我的同学秦安然,她告诉指着片子告诉我,吴老倔的胸部显示一片阴影,考虑到吴老倔七十多岁身体不适宜做手术,只能保守治疗。我的一阵揪心。透过窗户,我看见老人躺在窄窄的床上,背对着门的身躯依旧佝偻。
输了几天液后,王天才提议出院以后直接把他送到安居小区。
“送了我就爬回来!”吴老倔坐在床上,黑着脸,射出这句话让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小护士去下掉液体的空瓶和输液管抿着嘴笑着出去了。吴老倔的儿子收拾了一包袱东西,被他一把拽过去。
吴老倔依旧住在西屋里。他拿着一把细蔑笤帚清扫窗台,把柿子一颗颗摆放上去进行晾晒,远远看去两条橘黄色的带子,表明这大山深处依然有人家。他踩着院子里焦黄的落叶,披着一件黑色的棉袄铲下墙角的香菜,埋进沙土里。还在空地上挖了一个坑,把土豆胡萝卜用土埋实在,覆盖了一些玉米杆子。大部分时候吴老倔坐在朝阳的地方晒太阳。他好像全然不知道村子的小路上少有了脚步,也少了羊粪蛋,少了沿着墙头到处乱窜的公鸡和暮归牛羊。
转眼西北风已经成了常客,沿着地窝村那条沟呜呜作响,吴老倔屋顶的瓦松微微颤抖。镇政府安排人员密锣紧鼓寻找胡振林及其后人。一个月后,终于联系到了胡振林的儿子,他现在在广州中山三院心脑血管科。
明天就是节气上的小雪了,天气预报说未来两天吕梁地区气温将要下降到零度,还有雨夹雪。冷生风,热生雨。那天去地窝村,降温前的天气却出奇的暖和,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吴老倔躺在炕头上,盖着崭新的棉被。我坐在炕沿,用棍子拨弄着炉子里的炭块,告诉老倔:王天才支书和李镇长到飞机场接胡振林的儿子去了。
吴老倔的眼睛闪烁着亮光,用衣襟擦着眼睛。手臂伸到褥子底下摸索出一块手帕裹着的东西:“我知道我这病不好,可这下我就能去地下见我老婆和振林了。”
“那明天搬家不搬家?”我知道那里面是吴老倔攒了多年的心意,故意问他。
搬!搬!搬!太麻烦你们了。吴老倔连着说了几声,清泪盈满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