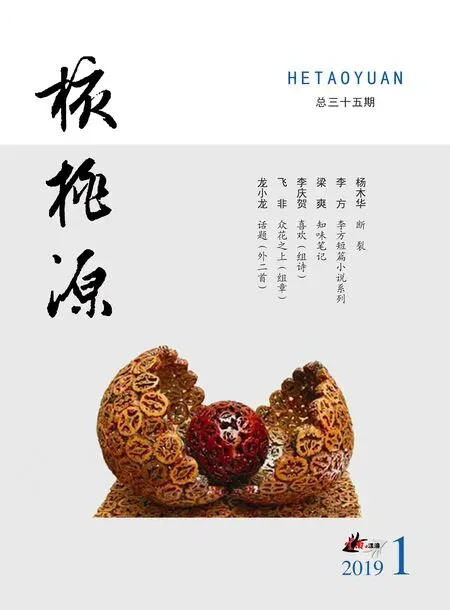秋声与乡愁(组章)
王近松
一
豆荚打开棺口,里面住着斗士,穿着结实的外衣,每一粒豆子都是乡愁的解药。
把一颗豆子掰开,一瓣是春,一瓣是秋;一瓣是生,一瓣是死,母亲同海外的农人们在豆瓣间摸索前行,艰难前行。
父亲背着月色,背着疼与痛,开着一辆红星牌的拖拉机在河谷间发出“哒…哒…哒…”的声音,与上夜班的蛐蛐交流着。
在海外,我不敢揣摩一个男人的心事,也不敢揣怀一只蛐蛐对于秋天的定义。来了昆明,拖拉机已经像历史一样,在教科书里散发着味道,我也时常把偷偷摸摸闯进屋内的风发出的声响当作蛐蛐在叫,也时常从梦里醒来,一夜夜的想着故乡的琐事。
在夜里醒来,总喜欢把一些心事如家乡的河流摆布着石砾一样,在一张纸上铺叙,用一些拟人、修辞、比喻,甚至夸张的手法来描写生活在在春城,描述一些颠沛流离的情愫。
那年那月在海外,拍照时总喜欢把秋天的月亮拍得模糊一些,把夜里的羊群、牧羊人拍得清晰一些,把地上的苞谷杆、以及巍峨的山拍得高耸一些,这样从农村走进城市,乡愁就如这些照片更加深刻。
我的父亲、母亲,收完地里的庄稼,将挎包、镰刀挂在墙上,从此时光被割去一春一秋。
走在空港大道,路灯明亮,却不见炊烟,不见火焰随风而起,听不见犬吠声,一棵树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老长,这就如同余生被测量,生死长短都在月色下。
二
枫叶红,银杏叶沾满泪珠。
秋天的南山,总是最有诗意,草海如同一面镜子,将所有的色彩都装在这滩水中。
十月的草海湖畔,马鞭草在凄凄切切的风中显得憔悴,那些未曾凋落的马鞭草用最后的芳香凝练着余生,这也是除了照片中一生最美的修炼。
在昆明,也有落叶飘落,同样那些紫色的花一直是这里的主剧场。夜里的树,月光靠着、醉酒的少年靠着,而他们也如同这些少年,年年岁岁在成长,岁岁年年有年轮。
一棵树,被移栽到城市,没有人知道它的孤独、寂寞,而他的乡愁都在每一片树叶里,叶子的根茎条叶有春天的细雨,夏天的阳光,还是知了短暂的一生。
在昆明,捡起落叶,就等于捡起乡愁。
杨林的风每晚都刮,杨林的灯每晚都亮,只有月亮似乎被雾虚掩着,除了雾,还有眼前的睫毛与泪水。
我睡在这空旷的夜里,乡愁如同牙痛,一阵一阵在心里搅着入睡前的思绪。
三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莫不都在写秋日的凄凉,这样的思绪我也有,与此同时,在我看来秋天是感性的、壮观的。
在谈到秋风萧瑟的同时,秋风也一样诗意连连。
蝉去了,秋风就在耳边造次,同时内心也因此澎湃。
无数次,我无数次在城市的草坪上寻找那种安逸、清凉的感觉,也试着在路边那一排排树下找寻一份秋意,捡起一片叶子,也会想到:树叶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一棵种子落下,在漫漫雪花中煎熬、容忍,最后接着春雨破土而出。
一个人流浪,背着背包,背着母亲的深切关怀,背着秋天的故事,故事里夹杂着乡愁,风起发丝便在眼角飘舞,就差了一点烟火。
在春城昆明,秋天的气息似乎没有家乡那么明显,记得那是一个下午,一个人吃过晚饭,背着背包站在学校的桂花树下,秋风吹着树木发出的声音越大,内心有许多嘈杂的声音就越多。
在瑟瑟秋风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风来衣服喜欢飘起,那时候的自己是何等的风流倜傥,也是何等轻微。
每次出门,母亲在前夕就会装满一瓶子,那是家乡最清凉、最纯净的山泉,在此时喝上一口,每一个细胞里清凉的水分子都如洪水暴发式的占据我的身体。
林清玄先生在《秋声一片》中这样写道:“生活在都市的人,愈来愈不了解季节了”。特别是像昆明这样四季如春的城市,秋天的讯息更少,而乡愁似乎同弹簧般,将思乡情怀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
写秋天,慢慢觉得田野近了,乡愁深了。
孤独、冷淡如同一层膜,每次有同学的父母出现在周围,高中同学、老乡同学聚会的时候,内心的凄凉就会油然而生。
我喜欢落叶飘飘,喜欢站在窗前看晚霞、拍晚霞,唯有这些能让我找到快乐,找到乡愁。
喜欢溪水流淌,喜欢牛栏江奔腾的声音,听宿舍轰隆的呼噜声,也喜欢在夜里听夜莺歌唱。
18岁,我有两个秋天,一个在诗中,一个在梦中。
碌碌无为的一生种下两块麦田,一块在春天;一块在秋天。
人生有三粒纽扣,一粒叫秋声,一粒叫家,一粒叫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