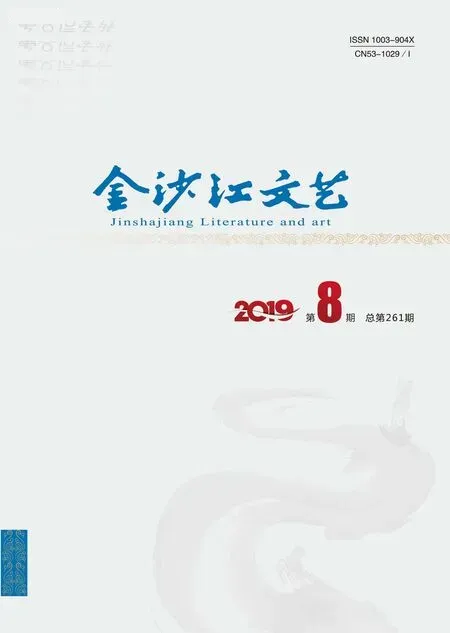千里孤岸的诗
◎千里孤岸
如果诗人思考每一个字
诗人手指上能飞出十只蝴蝶
若他愿意 但凭体力
拿长篇小说垒墙 种些彩色小短诗
他可以经营好一个皇家花园
若愿意放蝴蝶们飞来飞去传播花粉
他就能不费吹灰之力
成为一个好园丁 做另一个克卢修斯
若他愿意 他可以学欧阳修 彼特拉克
或特朗姆特罗斯 用芦苇杆 用鹅毛笔
或者打键盘 诗句会从江西的沙上
从墨水瓶中 或电脑主机出来
古往今来 诗歌的第一题材是大脑
如果一个诗人思考每一个字
大脑灵活一点 作为身体的一部分
它将在纸上开展机械运动
物理运动 化学运动或生物运动
它不断蹦出字来如黑芝麻的爆米花
字与纸之间 一改再改 改了又改
诗歌将三次以上复制灵魂
梦与醒之间 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为主题的诗歌比赛三天前
诗人可以重新怀孕诗句
酒与醉之间 收信者若清早拆阅来稿
诗歌信件会展开双手推开玻璃窗
放新鲜空气进屋 然后双手变双翅 飞去花园
我在世间数数
我在世间数数 第五是红的
起承转合之后 另一个我去帮我行走
三五年的冬天他都穿红色大衣
让满天空的雪无地自容
直到今年我在玻璃山抓住那个我
他的色彩终于有所收敛
但他拒绝回到我内部
我强迫另一个我 如用一块肉体打空灵魂
我数着数字 用阿拉伯传过来的口吻
他拿到过冰岛的右腿离开我
试图用两个人都喜欢的亚热带方式
我不是星期五 你不是鲁滨逊
他大声叫喊如土著 流浪多年
他讲故事的颜色由黑化作苍白
无力打动一只独木舟
那长身躯的舟子曾经行过撒哈拉和刚果
第五年负伤 借自己血液流淌至今
把搁浅当做命运不是一条好船
那条1967年诞生在小说里的除外
它骨架仍在 被马尔克斯称为西班牙帆船
然而西班牙 西班牙
不是一颗含钙元素的撕咬工具
在充满海水的大航海时代
它们尽是无敌之物
直到我拿手指跨过英吉利海峡
一下子数到伦敦
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五大首都
人口八百万却一直孤独如另一个我
虚度年华 白白打了2000年的大笨钟
世界地图
世界地图是地球最大的一幅肖像 是最美的画
青藏高原 亚洲最高昂的头 白发苍苍
里海是肾 黑海是心 地中海是大象
鼻尖在直布罗陀 欧亚两根绳子
结头处在伊斯坦布尔 那地方古时候叫拜占庭
更早是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
古罗马如今叫意大利 是一只长筒皮靴
脚尖为西西里岛 欧洲最碎
英国形象完整 是一只偷东西逃跑的兔子
偷的东西是爱尔兰
非洲像一只地球的左肺
因为抽了许多年草烟 非洲给人印象是黑色的
澳大利亚四方被咬 是世界上最吸水的一块面包块
太平洋在最初画地球时是蓝色画板
加拿大是画家最早用来调色块的地方它右上角呈棉絮状
美国船在上 用墨西哥做锚 钩着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撒满小岛做鱼饵
亚马逊河水流出一把扇子 巴西胖成一个黄芒果
智利是瘦腰的男子
是整块美洲雄性大陆的腰部骨头
来龙去脉清晰 直到冰的南极
一朵雪灵芝长在地球深处
米开朗基罗在石头之内
在西斯廷 米开朗基罗的脖子硬邦邦
教堂天花板花里胡哨 世界在七天齐备
他把七天的故事画完用了四年时间
在高度超过宽度的石头盒子里
他仰面朝天作画 鼻子顶着万能之主
他的那只鼻子 十四五岁时被人打过一拳
他一生都认为他鼻子里有一根骨头
是塌陷的 他相貌平平 不帅不怪
与他所有的男性雕像相比 他是自卑的
直到主持修建圣彼得大教堂
他还在寻求一种暗中补偿
他把教堂圆顶突出于罗马大地之上
绘画和建筑之外 作为诗人的米开朗基罗
第一和最后的荣光都在石头之内
他是脾气暴烈的雕塑家 从寄养的石匠家里出来后
他一生都忘不了打石头 他攻击他的每一件作品
用锤子和刻刀 他把一种痛苦之力注入大理石
像他写诗时把动词注入所有名词
那些石头裹着肌肉与骨头 是热乎乎的尸体
封闭了不安的动感 在最后一锤砸下时
那些尸体渴望再来一锤子 砸碎壳子活着出来
如此说来 他更像一个凶手 拿石头去固定运动者
使其终身监禁 例如在白色大理石中
大卫至今未投出石子 摩西的怒气止于抓胡子
圣马太只挤出右手 左脚和他的三分之二毛脑袋
皮影戏
对白少 有一种孤独是一个人的话剧
一个人演主角和配角
如荒野小学里一个人既是校长又是门卫
白天既要教书又要淘米洗菜
晚饭后才能自己演个小戏
舞台在黑的风上 照明的蜡烛东倒西歪
四个角熄灭了三根 幕布逆风发抖
夜晚太深 连恶作剧的观众也没有
用旁白的方式 喝个倒彩吧
希望隔墙有耳
我把双手凑近唯一烛火
无意中比出了一只巨大的黑耳朵
一把跳舞的钳子咬我
“让很多诱人的舞蹈/把瘟疫传到全城里去”
——(英)威廉·布莱克
当年我能歌善舞 很小就是音乐的神
我的舞蹈有车之双轮 我的歌声有鸟之两翼
我身后有一个世界跟着狂欢
大家都走起了太空步 都用上了机械手
据说那些深夜僵尸们都会护着裆部舞蹈
我又喜又疯 我在人生最浅的地方尖叫
用尖头皮鞋拼命踢踏玻璃钢舞台
又把皮鞋抛向台下的闪光灯
据说众人为争一只皮鞋还叫来5辆警车
我又黑又白 仿佛皮肤上涂满两个大洲
而实际上所有大洲我都去了
包括到南极教帝企鹅跳舞
我从海洋上空飞过一年四季
波音787带我去到众多国家传染
我忘乎所以 不记得来自印度还是埃及
我像一个疯狂的病菌游荡在地球
直到最后一次乐极生悲
那天我在一个废弃的兵工厂演出
有人装成后现代派的工人伴舞
我装扮成一颗吃了摇头丸的螺丝钉
在我手中跳舞的一把破坏钳咬我的右手
如鳄鱼之口咬断一节甘蔗 我用歌声尖叫直到昏死
三个月后我装了假肢
从此上台我戴上了黑手套 只唱不跳
我用两只话筒 左边唱歌 右边讲假话
语言的家
语言的家中应该有个词语喷泉
一块水变幻多端 洒出的句子出神入化
大厅里那些精神的影子反射彩色
走廊宽阔 廊柱玲珑 阳光从玻璃飞进来
如透明苍蝇穿过一道道空气 灵感振翅
屋里闪光的骨头生长 骨头上挂满小巧思
仿佛刚刚过了一场东方圣诞 古典之楼下
院子里满地泰戈尔开放 争先恐后
它们汁液饱满 炸开的浓香传出很远
把四方的汉字都吸引了 这些汉字太热闹
喜欢三五成群组成专有名词 形容词和动词
它们坐过9个站台 从一首诗中下车
最后集体挤在雕花铁栏门外等着通传
语言的家中主人是一位孤独的古典诗人
他深居简出 很少浇水 诗歌四季黑暗
他让仆人把那些黑漆漆的词都轰走了
入夜时 他躺在院子里湿的土上 一个人说话
那些秘密语言朝着天空幸福 整个晚上
发芽 开花 结无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