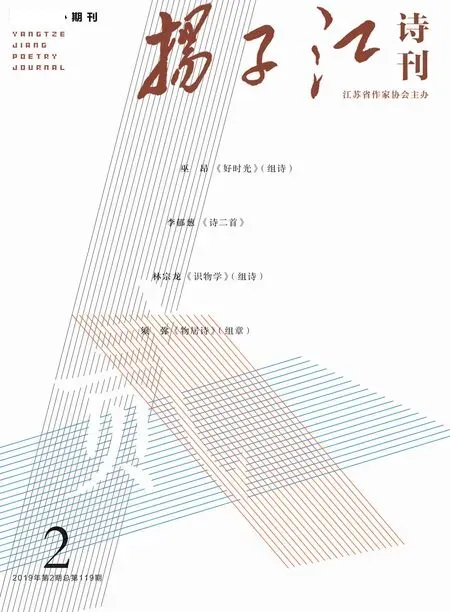送鸟鸣(组章)
董喜阳
时间之外
日历撕到了最后一页,一年的路到了尽头。抚摸着纸面,它体内的温度令我迷醉。每一张上的灰尘,都是时间跑动留下的痕迹。
忽然想,恋恋风尘,或许在时间之外,只是一个转身,一颦一笑,一个颔首,仅此而已。
声音的尾部最难得,它们却不是来自回忆。美好的部分,来自每一天反复被闹钟激励着醒来的瞬间。
送鸟鸣
春来送流水,花开递鸟鸣。
万物的属性恰如时钟,在时间中憋出细小的声音。
这响动和鸟鸣一起,并排站在电线上,像是一种演练。
当流水漫过钟声,花开叶繁,那是我的春天吗?与其说我们在形而上假借春天舞蹈,不如说我们在体内放了一把叫醒自我的钥匙。
一双翅膀,一次煽动的力量。
一种超越一切的旋转。
所以,你总说:春天,一定把鸟鸣送来。
流动的事物
逃离枝丫的叶片在旅行,弥漫在天地间的气体在旅行,跃出海面的鱼群在旅行,精神出走,与肉体之间位移的变化,也算旅行……流动的事物,日常画布上跑动的色彩,宣纸中呼喊的线条,都像是光的繁衍。灵动的事物,总能让世界学会取悦人类的感性器官。
假如你是光滑的水流,那么我要带你去旅行。远方很美,阳光很足。
那些大小不一的城镇、村庄,不再是地图上赶路的斑点。
山河湖泊,长亭短径,一次柳暗花明,一种心旷神怡,一场恋爱……亲近而又背离的红绿灯,恰就改变人生之河的航道。想走就走的冲动,就是自由的幻象。
出走或许不能解决你人生中任何难题,却能在远离的原点,找寻诗意的火种。
你瞧,远处枝头。槐花的芬芳,暗香浮动。
大黑山抒情
如果辽东半岛还有值得驻足的所在,我愿意它是大黑山。
绿意茏葱的肌肤,并不见黑暗的餐布。
围绕它畅想,静享在镜子对面的悠然时光。放下一切,包括此时的自己。我成为另外的你。
另外的你,是古装的化身。
野径、风声、雨滴、雷电都是你的随从。
小脆枣、柿子树、漫山花朵化妆成你的侍女。当你转向我——仿佛一阵风。柿子在树上摇晃,我在地面浮想。
所谓生命的意义也不过是,片刻欢愉,乘以不修边幅的苦难,再除以有人陪伴的青春年华。
茶饮小歇
煮沸的水哼唱的仿佛是童谣。嗯,一滴是一个声部。
遥远的觐见,从白的本质到黄的表象。说不清的是,那么久的光阴,驾驶的人去过何地。
瓷器间有细腻的词语跳出来,和金属器皿的摩擦,不生火。倒像是一首悠闲的骊歌。
我们相互端着自己的茶具,并不言语。或许声音,除了自己是响动之外,什么都不是。
等也是一个动词。日落就是一个结局。
我是一把幽闭而黑暗的锁,一层锈成了保护膜,倒悬于尘世。
手握钥匙的人,那个你,可否在人散时,接我回家?
橡 树
见到橡树,我的内心将要掀起怎样的风暴?从皮肤上渗进的水滴,噬咬着血管,而后是阳光。像钻进被窝,温暖我的周身。
你被露珠洇湿的枝干,散发出木质疏松的气息。一个具有感受力的词,随着叶脉伸腰。
仁义的绿,永不消沉的你——致橡树
致不张扬的革命意志的灵魂。
风吹过你,不系领扣的事物。具有多么迷人的方向,路人闻到的新鲜的锯末味,在你身体中氤氲。摸一把你,仿佛给你带上了钻石般的耳环。
你,终究是自然的化妆师
一场恋爱
光阴待我不薄——请我来认知一座城,一个似曾相识的人。
我们一起做了一件温暖的事儿。饱食一日三餐,持守四季流转。
你,宛如心底小小的城,薄薄的羽翼。一座城留住了时间,一些人退出了光影。未来不是滑道上的飞翔,道路永远没有尽头。
雪可以再多一点,像是我喜欢的事物,轻盈地翔舞。
白色的,不是盐。如果是,请抛向大海,那逐浪的水花,就是海的眼泪。
心的时间,突如其来,也恰逢其时。
一张照片
风请它下来了——尽管它极力靠近书架的边缘。
在众多华丽的封面时代,它自认多余。
何曾想过它之前的锦绣,拒绝与灰尘握手,哪怕是碰头。如今,它和一张张脸,同时埋首。潮水涨了又退,却不见一行金色的诗句,在淡蓝色海面的臂弯里斜躺。
它在地上安静地倾侧,阳光透过百叶窗找到了它。细碎的方格子,把它分割成很多部分。这底色,就是记忆的切片。
午后的时光,突然缓慢了起来。怀旧的锁,嘎噔一下。钥匙在空气中翻腾。
我是不是也会如祖母念叨的那样:年华似水,一切如昨。
我也开始期待明亮的天空,粉红色的记忆如雨滴落。
旅行与读书
旅行,藏青山绿水于胸。文字在方格子中的匍匐,领略的美是沧桑的。
时光延展千载,浩荡春风,流水汤汤。美,倒进回忆的试管。
摇晃的身姿,犹如经史子集上浪荡的秋风。
读书,案头江山锦绣。你吐出的一口气中尽显绵里藏针。
细碎而冒着银光的器皿,混沌初开。
舞动的利器演奏着锋刃的交响。书中的旅行,即是旅行在书中的烂漫动作。
旅行与读书,一对何其古老的互照行动与观念。
在歌德浪漫主义典范和艾柯所称赞的密教式诠释传统之外,世界还是一本大书。
我不选择堵在路上,我要慢慢地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