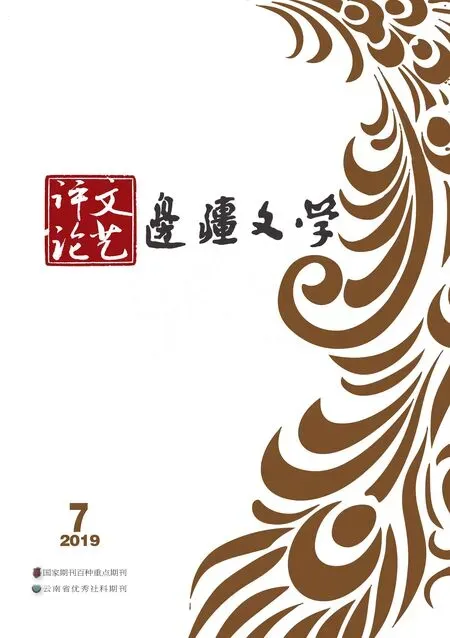“温暖”与“忧伤”
——评中篇小说《妥协》
……………………………………………·余彥冰
爱玲是近几年活跃的山东青年作家中极富才情的一位,在《破落院》《三声炮响》《人与兽》等小说中,她以现实主义的思想情怀,直面着乡土的凋敝,体恤着底层群众的苦难,既有触目惊心的揭露也有发人深省的反思。发表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19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妥协》,是爱玲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一方面作家依然保持着在文学中揭示苦难的美学追求,另一方面苦难书写又被温情所浸润、围绕,“忧伤”的底色夹杂着“温暖”的表达在给读者带来全新阅读感受的同时,也隐现着爱玲创作风格的调整与蜕变。
古老的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传统丧葬观念, 《妥协》的故事就架构在一场墓地争夺战之上。因这场风波,“我”从城市回到了乡村,边方两家的冲突、城乡观念的对垒、人性纠葛的困窘,也都通过“我”视角的流转得以充分展现。虽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围绕着这场墓地争夺战所展开的冲突与交锋,此起彼伏,但在温暖明亮的叙述内核的统摄下,文本内在的精神气场从来没有过任何怪吝、扭曲和分裂,大多为对苦难的理解和包容,对困厄的抗争与超越。并且,爱玲的叙述重心始终被善良、宽柔的情愫所缠绕,它们像一汪池水,在小说中弥漫荡漾开来。也正因如此,爱玲才能翻越重重纷争,关注到那些潜藏于文本细微处的生活细流和零碎片段,并对他们进行了温情的书写和巧妙的拼贴,既成功地淡化了沉郁、压抑的情境氛围,也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基调和节奏舒缓有致,富有张力而不张狂。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的目光逐渐位移到爷爷、奶奶、二叔的身上时,作家细腻疏朗的笔致不断地触摸着他们人性中最柔软、羸弱的部分,发掘着沉淀于悠长岁月中那份令人动容的情义。最终,以死亡、灾难和纷争开篇的小说,在脉脉温情中收尾。爷爷继续坚守着对方姓女人的情义,并帮她重新修缮了墓地;奶奶向固执的爷爷妥协,放下了对墓地的执念;而“我”则触动于爷爷的坚守,理解了奶奶的执念,所有的苦难、冲突和生存的挣扎在倏忽之间,便飘然而逝。
阅读《妥协》时,我们不用担心遭遇人性的丑陋和荒诞,即使面对人生的苦难和生命的缺憾,也会有潺潺温情从那粗糙的罅隙中流淌出来,将苦难和缺憾向着温暖和诗意转化。但继续往文本的内部纵深,我们不难发现,温情的书写并没有遮蔽爱玲文思的凝重与批判的锋芒,没有阻挡她对于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思索与拷问,温情的书写下叠映着现实沉重的忧伤,爱玲的第二副面孔也随之浮现。
深入挖掘人物内心的欲望、恐惧和挣扎,关注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焦虑,是爱玲写作的重要着眼点。《妥协》中的“我”是一个长期蜗居城市,沉迷于虚拟世界的网络作家,“当我从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抽拔出来,现实里的我时常是死亡的。”“我”就像无根的游魂,始终以一种错位的姿态生活在现实与虚拟的夹缝中。在作家的表述中,“我”的孤独、绝望与惶惑,成为了一种拷问,也是一种自省和盘结,令同处这个时代的我们惴惴不安、心悸羞愧。而通过对“我”精神世界的观照,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物质福祉和精神幻象被无情划破,现代人孤独隔膜的生活状态以及进退维谷的生存困窘被凸现至台前,一个充满着隐秘和伤痛的现代社会也被彻底披露。
城市化——是转型期的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变革,《妥协》中的方正、方芳作为城市的“新移民”,则正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方家兄妹是被时代的洪流蛮横地卷入城市化进程中的剩余劳动力,在参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仅获得了微薄的物质收获,并且,不论他们如何默认与妥协于城市的规则,都无法篡改他们由农民僭越为市民的事实,方正与方芳既失去了乡村和土地的庇护,又得不到城市原住居民的认同,只能以一种错位的姿态在城市的竞争与挤压中步履蹒跚、举步维艰。兄妹两在拥挤、破旧的居所中所发出的控诉和诘问,“我们也不知道最后应该到哪里去,银城不见得待得住,现在还没哪家工厂能管工人死的去处。我们想,老了,能回边庄吗?”不正是许多游走在社会底层,生命无所依傍的城市新“移民”的共同心声吗?不正是我们当前城市化进程中所暴露的现实一种吗?
从剖析“我”的精神之殇到揭露方家兄妹的生存忧虑,爱玲的关注点从心灵世界外延到现实世界,从个体的忧伤扩散至群体的忧伤,她的笔墨着落之处无不在感喟这个变动时代的精神逼仄,揭露着社会喧嚣繁华背后的隐秘伤痛。但好在,爱玲始终用文字寄寓着理想,用温情浸润着忧伤,故事的最后,“我”虽然仍无力改变生活的现状,但在为人处世时却增加了更多的人情味。方正和方芳,在爷爷重新修缮了方家女人的墓地后,再次踏上了边庄的土地,为自己漂泊的灵魂找到了寄托与归宿。
如果说“温暖”是爱玲给小说抹上的一层亮色,那么“忧伤”就是支撑起小说内涵深度的基本要素。在“温暖”与“忧伤”两副面孔的拉扯与融合中,《妥协》记录着这个时代最柔软和最坚硬的部分,“妥协”二字也在小说渐次浮现出的一份苍凉,一份被“温暖和诗意”所浸润的苍凉中升华为全文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