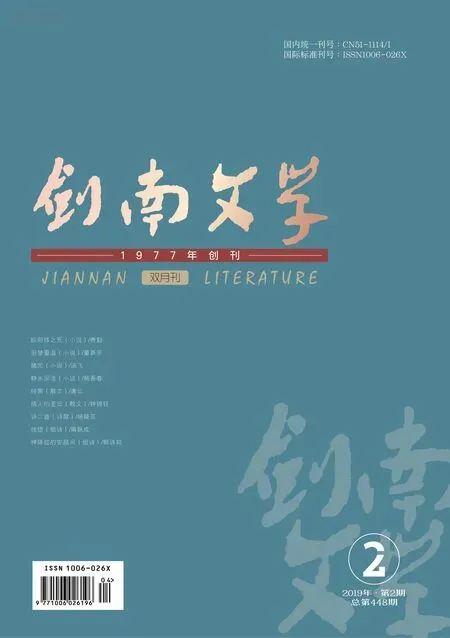寻亲
□ 黄小丽
各色灯光交错的舞台上表演着低级的舞蹈。屋子的一角,一个邋遢的男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画着浓妆的女人。五彩闪烁的灯光变幻着打在她不停扭动的腰上。男子嘴角上扬,吐出一股烟雾。一支舞跳完,她走下舞台,穿上厚重的外套准备离开。
“今天赚够了吗,就走?”她被那个男子抓住了手臂。
她甩开男子快步走向门口,害怕什么追上来似的,不敢回头。
“你他妈跑什么?老子知道你的新住处。”女人听了这话停住了脚步。这是她搬的第六次家,没想到还是被找到了。
她叫谢莹,来到这个城市已经好几年了,是跟这个叫邹新伟的男子一起来的。
谢莹在网上认识邹新伟时她是两个孩子的妈,一儿一女。丈夫是入赘自己家的,因为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没有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于是她就招了个上门女婿。农村的妇女都很辛苦,有永远做不完的枯燥农活,和手上一道道衰老的裂纹。谢莹是村里很多女人羡慕的对象,因为在那里像她这样不用做农活的人本来就很少,何况她还有充裕的零用钱。她的生活就是带着孩子打打牌,偶尔做做家务,宛如城里的阔太。
她丈夫很能干,靠给别人修房子赚了不少钱,却把钱全给了她,自己穿得像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她有钱去赶新潮,在智能手机刚出来没多久时就用上了,整天对着一张屏幕笑呵呵的。别人问她笑什么,她就赶紧捂住手机说没什么。老实巴交的丈夫只当妻子有了一个可以逗她开心的玩具,也从不去怀疑什么。
她在网上认识这个叫邹新伟的男子是在2013年。他总是给她讲各种城里的新鲜事,讲他的不知是真是假的人生经历。她从邹新伟那里得知许多她那个世界所没有的法则,什么灵魂伴侣、蓝颜知己。尽管他们很聊得来,她却没想和他怎么样,牌照常打,饭照常吃。只是对待丈夫有了一些不同,她开始买一些很新潮的衣服给丈夫穿。她丈夫穿上那些衣服走在工地上,宛如一个新世界走来的乡巴佬,新潮中透出土气。
她的父亲看不惯她的做法,支使她母亲去跟她谈。她母亲每次走到她身边,将要开口时又被某种他们自己心知肚明的力量憋了回去,就像对待一个不常走动的客人。谢莹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确实像主客关系,彼此都客客气气的,有一种不敢接近的疏远。终于,她父亲看不下去女儿的反常和妻子的犹疑,在饭桌上提出了意见。“你不要买那些怪模怪样的衣服给周明穿,他穿那些去工地上像啥样子嘛?这家里就你一个人这样就够别人说闲话了。”
周明是他丈夫,一个没有家的孤儿,在父母的撺掇下他们结了婚。婚后五年相安无事,周明什么都听谢莹的。她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后,他更是对她唯命是从。他常常对着谢莹和两个孩子傻笑。他对他们仿佛有一大堆话要说,却常常一言不发只是笑,因为他一开口,就会遭到妻子的厌烦,久而久之他也就习惯了少说话。
谢莹对父亲的话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自从十岁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对父母的话进行反驳,也从不主动向父母要求什么,别人都说她父母教得好,说她懂事得像个大人。
谢莹是在十岁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母亲生不了孩子,他们是在浙江的一所孤儿院把自己领回来的。父母从没亲口告诉她这件事情,而她从别的地方得知后也没问过他们,大家都这样平常地过着日子,只是在这平常里添了一些突来的礼貌。尽管大家都装糊涂,可谁能把这样的事真正藏起呢?不知什么时候起,谢莹对浙江这个地方有了特别的关注。她按照父母的意愿在本地结了婚,日子过得很平淡,但在这个爱做梦的女人心里,好像一切都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果。如果父母没把自己带离浙江会怎么样呢?如果我的亲生父母去接了我呢?也许……她常常在心里对着“浙江”二字发出类似这样的疑问。
在邹新伟提出去浙江时,她那沉寂已久的内心便开始泛起波澜,像春天被蜜蜂蜇了一下的野花,有了对远方的期待。
谢莹带着不安回到她的新住处,想着怎样可以摆脱那个噩梦一般的男人。她当初受内心渴望的驱动,带着证件包和家里大半的积蓄来到这个沿海城市,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回自己,找回属于自己的名字,找到生自己的父母。她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年的光阴早把那个年幼的影子磨灭在风里:孤儿院不知所踪,再没有人知道从前那个小女孩儿的信息。她积蓄花完了仍然没有任何头绪。钱花完后邹新伟就介绍她去酒吧陪酒。最开始她强烈反抗,可在家基本没怎么干过活的她也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就这样,她开始出入于各种灯红酒绿的场合,和各色人谈天说地。她知道自己得靠着这份工作在这个城市生活,邹新伟有意无意地也给她一些情感上的安慰,不久之后他们就住在了一起。她用自己的薪水支撑他们俩的生活。
如果事情就这样顺利发展下去,也许谢莹会找到她的父母,也许她会和邹新伟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但在各种预料中,人往往是最大的变数,没有谁能控制人心的走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邹新伟的脾气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向谢莹要钱,不给钱就打人砸东西。谢莹在悔恨和他一起生活的同时也在想办法逃离,尽管想逃离却没脸回家。她的住处换了一个又一个,无奈于自己工作的地方太容易找,她搬了好几次家也无济于事。她的一个同事有时直接叫她跟邹新伟同归于尽,可她毕竟是个胆小的女人,最多也只敢在身上藏一把水果刀。
当邹新伟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心里闪过无数个念头,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可弱者的逃避带来的结果是强者的肆无忌惮,邹新伟再次住进了她的新住处,她无法无视这样一个流氓的存在。
“到底怎样你才肯走?”她压着怒火问躺在沙发上的邹新伟。
“给我一万,我就再也不缠着你了。只要你给钱我保证滚得远远的。”他的话语中带着几分威胁。
这种话谢莹已经听过很多次,她当然不会给钱,再者,她也根本没有这么多钱给他。
“那你爱在哪儿待就待吧,我没钱了。”她把包扔在地上,径直走向厕所。
“你他妈骗谁呢?没钱你不会找你老公要啊。”邹新伟冲上去揪住了她的头发。
谢莹一边惨叫一边试图把头发从那个男人手里夺回来。她的挣扎换来的是更加残暴的折磨。一个巴掌打在脸上,她立马感到半张脸烧得疼,接着又是小腹上一脚,她被踹倒在地上。等她像只受伤的刺猬一样蜷缩在地上时,邹新伟才停了下来。他用目光扫视着这间不大的屋子,然后就开始了疯狂的翻找,衣服被扔得遍地都是,抽屉里的证件也被扔在地上。邹新伟并没有找到一分钱,只在床垫底下翻出那枚谢莹用毛巾包起来的戒指。他把戒指揣进包里,再次看了看周围,然后甩门而去。
谢莹挣扎着爬起来,看着满地的狼藉,她眼前浮现出孩子的笑脸、父母的身影……她捡回角落里的手机,打开信息,里面还有丈夫和父母发来的话,由最开始的责备到求和再到为了孩子祈求。她是悄悄走的,最开始家里人还以为她出什么事了,后来看见家里的钱不见了许多,她的衣柜也空了,他们才明白过来。丈夫为她的出走伤透了心,准备带着孩子离开那个家,是她的父母苦苦哀求才把他留下来,只是那俩孩子会常常向他要妈妈,他无奈只得发信息求谢莹回家。谢莹从来没有回过消息,却也舍不得把那张卡扔掉。她看着信息说不出来心里是什么感受,只是在心里萌发了另一个想法——搬家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回家呢?她捡起地上的结婚证,仔细地拭去上面的脚印,打开来,里面的那两个人依旧是那么熟悉,丈夫憨厚的样子再次映入她的眼帘。她不想再去想自己离开家的原因是什么,只是默默地收好自己的证件,走进厕所倒出垃圾桶,从里面拿出一个口袋,那里面是五百块钱,差不多够她回家的车费。无论搬到哪儿,她厕所的垃圾桶里总藏着这笔钱。
来到车站时天色已经有点暗,回家的那班车也早已经开走了,车站里全是一些匆忙赶路的人。她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第二天才有车,她还是选择在这儿等。她记得自己初来这里时是夏天,穿着长牛仔裤的她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扎眼。在那个温度计都热得罢工的酷夏,她慢慢试着融入这个城市。现在已经入冬了,她在寻亲失败以后带着满身的疲惫准备回到那个一直以来都不愿意承认的家,她不知该以何种心态去面对。
在半夜的车站,报纸是人们唯一的伴侣,谢莹身上也盖着两张报纸在椅子里休息。她感到脑袋有些混浊,是那种眼皮打不开但意识很清醒的难受。模糊间有人打电话的声音传来,一会儿清晰一会儿又消失,像断了线的珍珠项链在地上跳动。在这种感觉里,她的思想开始胡乱地飞驰,酒吧的喧闹、丈夫的面容、孩子的欢笑…… 她不想去想自己回到家的情景,脑袋里却总是闪现一些再次见到孩子的画面:一会儿是大哭大闹,一会儿是形同陌路。不过几分钟的时间,重逢的场景已经在她脑袋里闪现了千万遍,次次不同,回回泪目。她醒来好像明白了自己真正的想法,其实一直都是自己在执着而已,血缘不过是人们付出爱的一个借口,没了它,爱也并不会变质。在她的飞速想象中,天终于亮了。她来到车站厕所,就着冷水洗了洗脸。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半截火舌一样的红发,满脸雀斑,张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她看了看时间,离发车还有两个小时,她走进便利店,买来一把剪刀,咔嚓一刀剪去了那半截红发,把它们扔进厕所。看着它们像一丝丝血迹一样被冲向人类污秽的集中所,好像自己这几年来的痛苦也被带走了似的,她踏上了她的另一条寻亲之路。
正当她在汽车的颠簸中昏昏入睡时,一个电话铃声把她拉了出来。她看着屏幕上那三个字,发泄似的,把手机掷在了地上。周围的人都以一种耐人寻味的眼光看着她,期待她哭出来并且说点什么,她却什么都没发生似地闭上眼睛继续睡觉。那些人见没什么新鲜事也就说各自的话去了。
转了两趟车,她终于坐上了直通家里的那趟车。车上的人她一个也不认识,可那一口口乡话却使她实实在在地感觉自己回去了。她环视了一周,庆幸没有认识自己的人。或许是这几年她真的变了许多,已经没人认得了,无论是哪种,她都希望不要有人和她说话。这趟车她以前经常坐,因为这是下县城唯一的交通工具。几年过去了,这沿途的风景倒是没变,车上售票的妇人说话仍然会喷人一脸唾沫,她恍惚觉得这次也是一次平常的回家。车开得越久,她越感到近乡情怯,她的怯不是小心翼翼的怯,是内心忐忑的惧,惧什么?她说不上来。
车终于还是到站了,人们都推着彼此往车门涌,她坐在原位并不着急。等人们都下完了,司机开始倒车。可能是刚下车的人群还没有散开,车刚发动就急刹了一下,她的头撞在前面的椅背上,没忍住,她叫了出来。司机听见叫声回过头来看见她,有些不耐烦地说:“大妹子,到站了,快下车。”听见这话她才慢吞吞地站起来往车门走去,走到司机面前她停住了。
“如果你的老婆跟别人跑了,你会怎么做?”她开口问司机。
“她要是跑了就别想回来了!赶快给我下车,你这个疯婆娘!”
“如果是你女儿呢?“她有些不甘心。
“我没女儿,不过要是有的话,我会把她抓回来,打断她的腿,让她乖乖在家待着。”
她仿佛从这句话中听出了安慰,没再犹豫,大步跨出了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