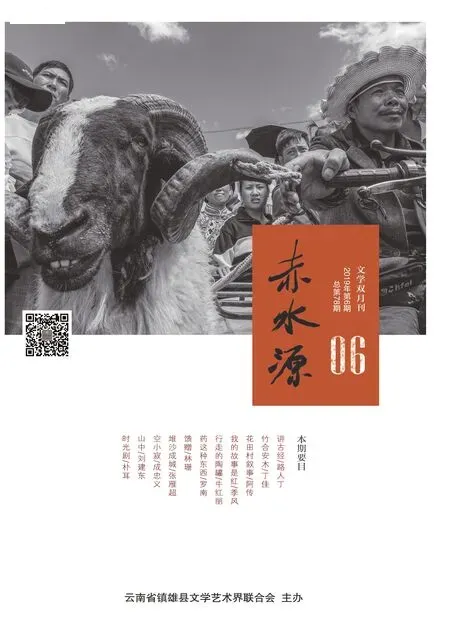大木桥散文
汪天慧
爱人兑现了承诺,亲手为我建起了独门独户的房子,最可爱的,是有一个可以任我尽情遥望四面八方的开阔露台。于是,我流浪漂泊的心,实实在在地走进了名叫“家”的地方。
但是,盛满喜悦的心最是贪得无厌,刚刚安定了几天,又繁衍了刻在骨子里的浪漫。
我的浪漫也不奢侈,不过是和夫君在露台守望月亮和数流星;或者,剪烛西窗共读书;偶尔,也会强迫他听我朗读诗歌。只有到天气晴好的周末,才一再邀他去我遥望了千百遍的山上旅游。
这种花费不多的旅游最是让人陶醉。包容、大度的爱人时时刻刻拍得下风情万种的我和我欣赏的美景,并且,纵容我随心所欲的脚步。
每次从山上回家,我总是收获颇多,有时是散发山野清香的野花野果野菜,有时是我山泉般源源不绝的灵感。
每次从山上回到家里,我总是把房子打扫了又打扫,清洁了再清洁。然后,做夫君爱吃的饭菜,先讨好他的胃,他就不好拒绝我每个周末与山水的约会。
这次与我有约的是大木桥。大木桥没有人家,也找不到古色古香爬满青苔的木桥。有的,只是一个波平如镜的水库,库里的水,来自四面八方的山泉。大木桥水库,曾经如母亲饱满的乳房,日夜流淌的甘甜乳汁喂养了县城十万的百姓。后来,县城扩大,进驻人口增多,饱满的乳房渐渐干瘪,政府投资建起了第二水厂,大木桥水库,退居了二线。
但是,大木桥,并不寂寞,它成了县城百姓最终的归宿。套用一句阴阳先生的话来说:大木桥,是一座阴间的城市。
从出租车上下来,两个在路边玩耍的小女孩说:“去大木桥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大路,有狗;一条是小路,要经过看不见天的森林。”我与爱人相视而笑,选择了泥泞的小路。
说森林看不见天,实在没有夸张。林外是炎炎的夏日,林中却凉意透寒,即便那条纤细的小路,也时有树上的冷露滴滴湿透。我对爱人说:“快!去找一块可以仰望阳光的空地,搭你日日不离口的小木屋,我准你的假。”
爱人果然一转身,偏离小路,隐进了粗壮的林木深处。看着幽暗的林深处,我只听见爱人遥远的渺茫声音:“站在原地不要动,我一会就回来!”我故作轻松地向树林怪叫,没有回声,我的歇斯底里竟然被树林轻飘飘地吞掉了。我只好轻轻唱起歌来,歌声很小,与林间慢慢行走的微风响应和,很快乐。
没有桥的大木桥,因为干旱,水库里的水只剩下小小的一潭,却有执着的垂钓者执着地守望他垂向潭水的鱼竿。
来大木桥的人不少,甚至有大大小小的私家车和堆积如小山一般的刚刚炸过的爆竹。远处,有一副黑黝黝的棺材在等待下葬。站在大木桥水库的堤坝上放眼望去,竟然是一座又一座高出茂盛的树木的已逝者的村庄。村庄里的房子很豪华,一幢又一幢,静静地显摆钱多。
“去拜拜这些睡着的人,以后也做他们的邻居。”我对爱人说。
“整天把《红楼梦》的‘好了歌’挂在嘴上,看到这么多死人的豪华别墅,还没有自己的思想。亏你说认识以日月星辰作陪葬、以天地为棺椁的庄周!”我的爱人,眼睛盯着那些雕刻精美、价值不菲的墓碑,根本不买我的账。
边说边走,听见了男女老少的谈话声和笑闹声。转过一个山头,就看见一大群或坐或站的兴高采烈的人。见到我们,一个熟人热情地捧出新鲜的荔枝,说:“来迟了,你们,至少要排两个钟头的队。”
这是一群宁静淡泊的城里人,不相信广告,每天来大木桥背山泉的养生者。那一眼琼浆一样珍稀的山泉,筷子般粗细,从半人高的山肚子里自自然然地流出来,流进了城里人形形色色的塑料桶。让塑料桶去排队接水的养生者们随缘更随和,没有城里人的冷漠。我和爱人,告别了他们的热情与微笑,向人迹稀少的林深处走去。
说是人迹稀少,逝者的村庄却不少,一座又一座,冷不丁,就堵住了我们的脚步。我想,再过一百年,现在水源已开始枯竭的大木桥,会不会连这些茂盛的树木也枯了,剩下的,是密密麻麻、挨挨挤挤的墓碑林。
终于,再也找不到路了,满山满谷两个人合抱都不一定抱得过来的松树静静地站立着,聆听自由自在的鸟鸣和无休无止的蝉声。
在欢歌笑语的溪水边,我从背包里拿出柔软的坐垫放在石头上,先邀请请腰酸腿疼的爱人休息,接着就去找连理枝。连理枝很多,形形色色的,每一对,都是树干相互依靠,任树枝和树根向四面八方扩张。我最喜欢一对连理枝,它们的根部,仿佛被当初恶作剧的种树人故意缠绕了一圈,这两棵树就自自然然地成为了连理枝。因为缠绕的树根,连理枝的根部像极了弯弯的弓,放上一个柔软的坐垫,就成了自自然然的枕。我把背包挂在树上,在厚厚的松针上铺开床单,又把丰盛的午餐摆在床单上,大声喊爱人吃饭。
吃过午饭,把剩下的食物装进背包,我就开始午睡。
午睡前,我没忘记对爱人说:“你给我站岗,我要快快走进梦乡,走进连理枝浪漫的婚姻。”
从美梦中睁开眼睛,细细碎碎的阳光透过密密层层的松枝洒落在绿绿的草地上,鸟鸣声异常婉转,蝉的歌声自由散漫。我的爱人,着一件贴身的白背心,枕着连理枝弯弯的树根轻轻打鼾,他的腿,做了我实实在在的枕,他的红衬衫,是我自自然然的夏凉被。
“前面没有路,我们顺着来路倒回去。”我说。
“倒回去,无非是再看一遍已逝者的村庄。不如往前走,也许可以看到更好的风景。”爱人说。
一直往前,果然看到“树云山庄”高高的牌坊。走过牌坊,是林场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黄墙青瓦的两层大房子,抬头仰望那些结实安稳的木柱走廊,我一下子退回到花枝招展的十来岁。
房子的前面,是一大片开阔地,和如假包换的青山绿水。沿着纤尘不染的水泥路,一幢又一幢盖着琉璃瓦的精致的小房子,童话般,隐藏在繁盛的花木丛中。门楣半掩、窗户敞开的小房子,都没有主人,很是寂寞。
走过树云山庄,我们又走进更大也更高的森林。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见远处热闹喧哗的县城。爱人一边拔深入手臂的刺一边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能不能大声些?”
“我和刺说话!”
“刺说了什么?”
“刺说:因为爱你,所以深情款款的挽留你,想不到,反是伤害了你。”
“我现在要摘一朵花,你过来听听,花要对我说什么?”
“不用过来,我已经听到花儿大声说的话:你如果是爱我,就请给我浇浇水;你如果是喜欢我,就请把我摘下带回家。”
“花儿啊,我是真的喜欢你,所以摘下你。但我不会把你带回家,怕你成为家里的第三者。”我一边说,一边把美丽的花摘下来,插在帽子上,摇摇头,花,就落到地上。
回到家里,我又开始站在露台上,遥望大木桥。
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喝一口那眼从山肚子里流出来的甘美的泉水,温暖又安详,养心更养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