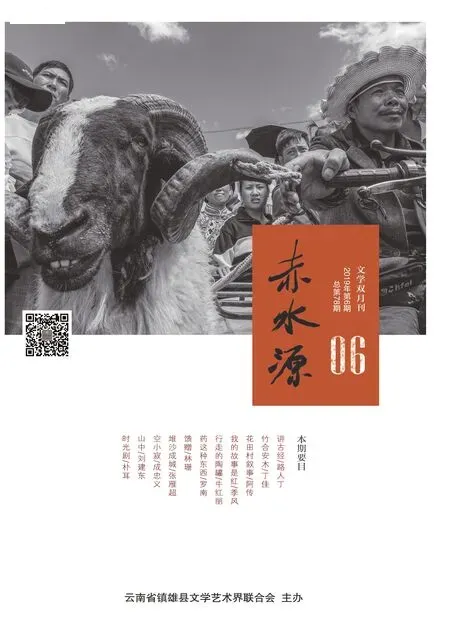竹合安木小说
丁佳
竹合安木
“睡不着吗?”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伸到了牧时的眼前,大拇指和食指间夹着一片包着绿皮的绿箭口香糖。牧时从座位角落里抬起头,眯着疲惫的双眼,看了看这只皮肤细嫩,血管绿得有些俏皮的手,坐直了身子。他接过口香糖,看向一直注视着他的年轻男人。
“我叫沈尧。”年轻男人嚼了嚼口香糖,吹了一个汽水瓶盖大小的泡泡。他仰了仰头,像一滩水泥一样四肢瘫软地贴在座位上,“火车上真闷。”
牧时捏着口香糖,眯眼看了几眼,随后揣进了衣袋里,拿出了手机。
“你是要去竹合吗?”沈尧将手臂交叉搭在颈肩处,将头枕在上面,他歪着头看向牧时,嘴里又吐出一个泡泡。
“嗯。”牧时翻看着手机,眉头紧锁着。
“巧了,我要去安木。”沈尧说。
牧时滑动手机屏幕的手停顿了一下,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似的,他快速翻看手机,找到了黎的话——他在早上八点拿着车票离开。屋外下着雨,他拿了一把黑色的伞,他的脸像弦一样紧绷着,我看得出他连假笑也笑不出来,他连再见也没说,轻轻把门关上,消失在门外。我给他洗衣服时从他衣袋里见过那张去竹合的票,他神情慌张地抢了过去,悲怆地告诉我说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我知道我不是他想要的,我们的生活也不是他想要的,我同意了让他去他想去的地方的乞求。
“怎么不考虑去安木转转呢?” 沈尧仰头看着车顶,细长的脖子喉结滚动着,车厢里柔亮的灯光照射在他的脖子上像光滑的颈瓶。“那里是我梦想的天堂。”他说。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去,但我要先找个人。”牧时说。
“找谁?”沈尧从肩上拿下手,一手搭在座椅上,一手支在桌上撑着脑袋,他对着牧时挑了挑眉,露珠一样水灵灵的眼睛注视着他,像是在观赏一幅奇异的画。
“一个叫黎的有夫之妇。”牧时说。
“你爱她?”似乎有点冷,他将两只手缩了回来,伸进衣袋里藏着。
“嗯。”
“她现在哪?”沈尧问。
“你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吗?”
“都可以。”
“她在这辆火车上。”牧时说,“现在晚上23 点31 分,黎在望着窗外想他。”
“想谁?”沈尧问。
“她说,‘他给我发了条短信,问我过的还好吗,还有,对不起。’”牧时拿着手机照着念,“‘我以为他再也不会和我联系,没想到他依然愧疚着想要得到我的谅解。可是这种事我该怪谁呢?全怪他一个人吗?他已经承受了太多我不知道的痛告,我无法与他感同深受,我已经下定决心来竹合找他,我只要知道他自由并快乐着就放心了。’”
沈尧的目光从牧时的脸上挪到了车窗外,窗外一片漆黑,玻璃窗上映着车厢内的一切,人们在灯光中昏昏欲睡,警醒着的人们百无聊赖地看电视剧,打游戏,对面相互依偎着睡觉的两个女生鼻里发出轻微的鼾声。温度越来越低,沈尧吐掉口香糖,将衣服拉链拉上最顶端,将下半张脸藏进衣领里。
“你父母知道你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吗?”他问。
“我是孤儿。”牧时说。
“真幸运。”
“有时也挺不幸。”
“我忍不住想要夸赞一下你的胡渣,它让你看起来很有魅力。”沈尧说。
“可能吧。我不知道黎会不会喜欢留胡渣的男人。”牧时说。
“既然她在火车上,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她?”
“我只能追赶她的步伐,她去哪我就去哪。”牧时说,“我无法真正拥有她。”
“你可以拥有她。”沈尧说。
牧时摇摇头,看向窗外的目光遥远又悠长。
“她活在过去。她在一个信箱软件里记录了她的所有生活,时间地点都标记清楚,我是无意间发现她的,她乐观,深情,有时还挺可爱,虽然她以及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还是对她动了心。”牧时说,“可能我也需要去一个适应我的存在的地方。”
“还能去哪呢?”沈尧问。
“这个谁也说不清。”牧时说。
朝阳
腊月的霜雪包裹了整个城市,像储放了一段时日后的豆腐,干瘪的身躯被毛菌披上一件毛绒绒的外衣。
靠窗的座位空了整整一周。林音说她转学了,杜若怎么也不肯相信。
“她确实转学了。”走廊里李老师停了下来,见杜若眼里的光渐渐淡了下来,她叹了口气,“关于四月的比赛,你和林音可以再重找位新搭档。”
杜若看向老师身后,阳台外飘着漫天的飞雪,她记得昨天这暗沉沉的天空也只是虚张声势地刮刮寒风,原来季节更替只在一夜之间。
她告别老师,快步走进教室。教室的窗前挤满看雪的同学,他们大张着嘴,明亮的眸子里映着晶白的飞雪。多数同学还是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书,偶尔与周围人交谈几句。她斜眼看了看那些看雪的同学;她讨厌冬季,她认为冬是个狡猾的姑娘,她将花草凋零,再把纯洁的雪覆盖在它们的残骸上编织一个凄美的谎言为其洗白,最后留腊梅独自美丽。简直虚伪至极。相比冬季她更喜欢万物充满生机的春天。她将目光从窗外挪进来,目光掠过每位同学的脸——颜悦不在座位。她坐回位置,耐心等待着。
林音进教室的时候头上的雪花还没溶化,她手里握着一个雪球兴致勃勃地想要给杜若看,杜若到达她身边的速度比她头上雪花溶化的速度还要快。“你去了哪里?”她的语气有些急不可耐。
“我去了钢琴室啊,怎么了?"林音手中的雪球慢慢地溶化,雪水沿着她发红的手指间的缝隙滴落。
“颜悦转学了。”她的声音沙哑,神情温怒,“你还去钢琴室做什么?”
“准备四月的比赛啊。”林音握紧着雪球,“我,你,还有颜悦,我们三个的约定你忘了?”
“我没忘!” 她声音发抖,大声地说,“是颜悦忘了,她离我们而去。带走我们的约定。”
“不, 这不是你选择放弃的理由。”林音手中的雪球碎了一地,她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是你忘了我们,只是你一直都不明白!”
“够了!到此为止吧。”杜若咬了咬毫无血色的嘴唇,伸手抹了抹发红的眼眶,“到此为止吧,我从未忘记过你们。颜悦就是个大骗子。”
她转身走回座位,从抽屉里抽出书包,一股脑地将桌上的书本扫进书包里,拉上拉链,甩上后背,与林音擦肩而过,头也不回地离开。
大片大片的雪落在她的头上,她拉了拉围巾,将一双通红的眼睛露在外面,呼出的白雾在空中一次又一次地消散。她快步走着,发泄似的往没有被人留下脚印的雪地上踩,使劲踩使劲剁脚,好像将这雪白的表面踩个大窟窿,露出它发黑腐败的本质,她内心的愤恨就能有所缓解。她真希望这该死的冬天和那狗屁约定能够到此为止。
她在一户人家的院子外停了下来。一个小孩在屋檐下挥动着竹竿敲打着屋檐上凝结成冰的冰锥。每当一个冰锥掉在雪地上摔个支璃破碎,小孩的脸上便会露出一抹狡猾的笑容。一根约莫25 厘米的冰锥从屋檐上掉下,刺破空气,截断了一枝绽放着殷红色梅花的枝丫。小孩扔下竹竿,仓皇而逃。
她看着那被截断的枝丫,脑袋昏昏沉沉的,就好像那被截断的,与身体分离的是她的脑袋。头上是冬日里透不出光,阴沉沉的天空,一瞬间天旋地转,像是过了一个世纪般漫长——她闻到了医院里消毒水的刺鼻气味。
“砰”的一声,教室门被打开。
杜若猛地从桌上抬起头,她睁着睡眼惺忪的眼,目光聚焦了两次才看清教室外的人——穿着蓝白色的校服,一手插兜,一手扶着门框,乌黑柔顺的高马尾搭在肩上,柔和的五宫皱得像南瓜灯一样搞怪——是颜悦。
“你没转学?”她难以置信地看着颜悦。
“谁说我转学了?”颜悦歪着脑袋, 满脸鄙夷地看着她,“原来你躲在这儿偷懒啊,我和林音找了你好久。”说着,她走了过来,“快点和我去音乐教室训练,我们没时间浪费了。”
她们走在学校的雪地上,在洁白的地面留下一长串脚印。花坛里的万年青被雪花戴上了一顶厚厚的帽子,肃条的柳条结了一层光滑的冰衣,柳树苍老的身躯像是背负着整个严冬。
“我做了一个梦。”杜若说,“我梦见你转学了,四月还没到,一切都结束了。”
“那是假的。一切还没结束。”颜悦仰着头,呼着热气,将飘落至眼前的雪花溶化在空中,“听着,杜若。”她扭头目光坚定地看向她,“我们三个人中,就算有一个人打退堂鼓,选择退出,那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唯有你不行。
“因为你爱的春天就要来了。”
刚踏进走廓,她们便听见走廓的尽头传来悠扬的琴声,像是熄灭的火堆遇到了猛烈的大风,忽明忽亮的星星之火立马进发出明亮的火焰。她们欣喜地奔跑起来,冲声源处跑去,轻轻推开了音乐教室的门。林音坐在钢琴旁,手指跳跃在黑白分明的琴键上。她朝她俩微微一笑。颜悦拿出背包里的小提琴,迫不及待地搭在肩上,蠢蠢欲动着,杜若也从书包里拿出乐谱。她们兴奋地笑着,像朝阳生长的向日葵。
一个又一个动听的音符飘出了教室,萦绕在教学楼的四周,静谧的校园沉浸在了音乐的海洋里,她们像水母一样在海里肆意荡漾。
杜若张着嘴轻唱着,握紧了手中的乐谱。
刺鼻的消毒水味再次袭来。世界像雪一样一点点地消溶,最后只剩无穷无尽的黑暗。
杜若在夜里睁开眼。她像一只即将干涸而死的鱼儿回归到冰凉的湖水里,她大大口地呼吸着空气,张皇地望向四周;窗外浓稠的夜色往屋内透进些许微弱的夜光,她的身旁支架上吊着药水瓶,细长的塑料管伸延到她手腕上的针头处,她躺在一张窄小的病床上,身上盖着充满消毒水味儿的被褥,母亲靠在床边,头枕在臂弯里熟睡着,鼻子里发出轻微的鼾声。在母亲的身后还有一张病床,床上躺着位瘦骨嶙峋的老头。
她感到眼角冰凉。她伸摸了一下,满手泪水。她用另一只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坐起来,怕惊醒母亲,她的动作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你醒了?”身旁响起一声低沉的声音。
她刚坐好,被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她转过头,见老头将头偏向她的方向,两个黑洞似的眼睛盯着她。她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苦难的孩子,”他轻叹,”你沉睡了好久。”
“有多久?"她小声地问。
“大概一周。”
“颜悦和林音有来看过我吗?”
“她们一直陪伴着你,一直都在。”
她轻轻松了一口气,嘴角微微上扬。“外面是不是还在下雪?”
“应该还在下,” 他眨了眨眼,“冬季还没过去。”
“老伯,” 她说,“我做了很多个梦,我梦见我没有病倒,没被送进医院,颜悦的爸妈也没有离婚,她不用跟随她的妈妈改嫁去其它城市而转学,学校的音乐教室里林音不是一个人在弹奏,她还有我和颜悦,我们每天都在奋斗,共同期待着春天的到来,这一切真实得不像一场梦。
“这一切是真是假?”她问。
老头将他瘦得只剩骨架的身体翻了个身,和头保持同一个方向。但他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如果那些梦是真的,现在的我是在梦境里的话,那我就要继续躺下睡觉了,我想回到颜悦和林音的身边。”她又小心翼翼地躺下,“我们还有约定没有完成呢。”
她躺了下来 ,阖上眼,过了一会儿又眼开眼,她逼迫自己入睡,反反复复闭眼又睁眼,最终她睁开了眼,她目睹这寂静的夜张着一望无际的大嘴像是要把她吞噬般。她赶紧求救,“老伯,我睡不着了。”
“怎么了?” 老伯的声音暗哑低沉。
“我好像回不去了。”她抓着被褥,怅然若失地说:“难道这就是现实吗?我真的病倒了么……原来她们说的是真的。可……可是 颜悦和林音她们在等我啊,我该怎么办。”
她想起在梦里和颜悦、林音一起排练的日子,抬起了插着针水的左手,鼻尖涌出一股酸涩的刺痛感,她忍不住用被子蒙住脑袋,在被窝里嚎啕大哭起来。“我该怎么办。”她说。老头闭上眼,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惜,晶莹的泪珠似流星一样划过他枯瘦的脸颊。
夜在悠长,空气在寂静中无声地喧嚣着,痛苦像条长蛇,攀爬上她的全身,紧紧勒住她的脖子。她感到自己就要室息。
“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她无力地说着,“我感到我的生命像河水一样奔流而逝,我恐怕熬不过这个寒冬,等不到四月了。”
在最后的一瞬,她的灵魂钻入到一个白色光圈里,那里阳光明媚,白雪褪去,柳条抽新,学校里的樱花粉嫩嫩的,颜悦的笑声和她的琴音一样悦耳,林音穿着白色长裙,她纤长皙白的手向她挥舞着,她们在去往四月赛场的路上。她追赶在她们的身后,大声呼喊,大声求救,无论她如何歇斯底里地呐喊,她们像是听不见,毫无察觉地继续向前走。她放下手,停了下来。
“杜若!不准放手!坚持住,我们等你醒来,在充满好运的春天里!”恍惚中,她听见回响。
在肃穆的手术室里,医疗仪器发出“嘀、嘀”的令人胆颤的磁音,被医生杂碎的脚步声踢着走。杜若躺在手术台上,各种手术工具在她的身体上方交换,她戴着氧气罩,呼吸微弱,刺眼的手术灯打在她的脸上,她紧闭着双眼,意识沉入一望无际的汪洋。
一只麻雀停在了窗台上,又跳跃上积雪消溶的水仙盆裁里,准确无误地啄食了一只刚冒出头的虫子,似是不够满足,它扭头看向被新绿色点缀的城市远方,展翅飞去。
杜若睁开眼,鼻尖仍旧是熟悉的消毒水气味,手上的针管还在,吊瓶里的药水还剩一半。母亲坐在病床边,日日夜夜积累来的焦虑在这一刻间烟消云散。林音坐在一旁撑着脑袋打着瞌睡,而颜悦站在窗边,看向窗外的目光遥远又悠长。
“老伯呢? ”杜若看向另一张空着的病床。
“什么老伯?”母亲奇怪地说,“那张床上从没住过人啊。”
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她呆立在床上,迟迟缓不过神来。
窗帘突然被拉扯开,耀眼的阳光倾泻了进来,金灿灿的,暖洋洋的,涣发出无穷的生机,带来初春清冽的气息。大家都朝光源看去。
“春天永不迟到。”颜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