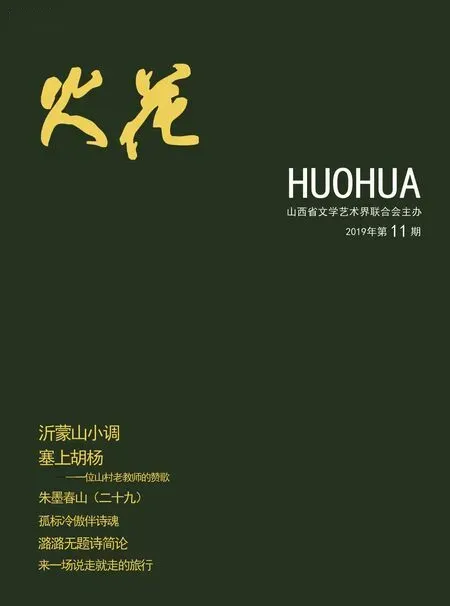朱墨春山(二十九)
王克臣
阳光普照大地,天空布满彩霞。
高鹏远和高桂珍父女俩,很快来到董凤才家的地头。
地头一袋烟,这个约定俗成的老规矩也免了。
拉墒,高桂珍从小干惯了的农活。她牵着小毛驴,走在最前面,不时回过头来看看父亲。
高鹏远一手扶犁杖,一手举着小鞭儿,只在驴背的上空轻轻地摇,一下也舍不得抽在它的身上。
高桂珍每一次回头,心里都“咕咚”一下,她真想扑上去,大喊一声:“爸爸——”然而,她只是牵着小毛驴的缰绳,默默地往前走。
高鹏远手扶犁杖,手里摇着小鞭子,一声不响地犁地。
一遭,一遭,又一遭。董凤才家的麦茬子地,耕了一小片。
日头升到一竿子高了,忽见一个女人从远处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高桂珍回过头说:“爸爸,那是谁?”
高鹏远说:“我看出来了,是你孙大妈。”
高桂珍说:“是她,是孙大妈。”
孙秀英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地边儿,待高桂珍和她爹走到地头时,颤颤巍巍地说:“歇会儿,歇会儿吧!我听连汤嘴说你们来给我耕地啦。这娘儿们,属兔子的,耳朵真够长的!”
高桂珍说:“孙大妈,您家董大伯有病,咋不在家里伺候,跑这里干嘛?”
孙秀英说:“他在家躺着他的,本来就干不了活,还再耽误一个!”一面说,一面牵过驴缰绳,“珍子,你坐地头儿歇会儿,我来拉墒。”
高桂珍看看通身是汗的小毛驴,把驴缰绳交给孙秀英,说:“好吧!”然后说,“爸,把偏缰解下来,拴到拨浪鼓上。”
“干嘛?”
“我拉偏套。”
“有小毛驴拉犁杖,用你干嘛呀?”
高桂珍用手掌抚了一下驴肚子,说:“您看,这小毛驴通身是汗。我拉偏套,它也省点儿劲呀!”
高鹏远知道,珍子这孩子犟,她认准的理,十头牛也休想拉回来,只好说:“就依你!”
高桂珍把偏套的缰绳,一头拴在拨浪鼓上,另一头勒在肩膀上,低下头,用力拉。
一遭,一遭,又一遭。小毛驴似乎很懂人心,身上淌着汗水,眼里滴着泪水。
远远的又有两个年轻人,朝这里跑过来。很明显,一个是双喜,一个是小艾,这俩人干嘛来了?
小艾喘着粗气说:“珍子姐,帮助志愿军家属耕地,不叫我们一声,对吗?”
高桂珍抬起头,笑笑说:“这丫头,小嘴儿真厉害!”
孙秀英说:“谁家的闺女像谁!”
小艾说:“孙大妈,说什么呢,干嘛提人家大人呀?”
孙秀英说:“我们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提提不好,我正想她哩!”
小艾说:“我们是来帮您耕地的,不是找您抬杠的。”
双喜说:“小艾,你替珍子姐拉偏套,我替小毛驴。”
高桂珍急忙说:“不行不行,小艾精精瘦瘦的,一阵风能把她吹倒,她拉不动,再说你咋能够替小毛驴呢?”
双喜拍拍小毛驴,说:“珍子姐,你看,小毛驴的身上出了多少汗了,把它卸了,歇会儿,拉它到路边啃会儿青草,再套上拉犁,也不迟!”一面说,一面解开夹板,牵着小毛驴,“孙大妈,您把小毛驴牵到路边,让它啃点儿嫩草,就势儿也歇会儿。”
孙秀英无奈,只得牵上小毛驴,刚要走,高鹏远说话了:“老嫂子,你怎么听小孩子的?这小艾能顶得上珍子,双喜能顶得上一头驴?这地还能耕吗?”
这下,可把孙秀英给难住了,试探地说:“要不,就叫他们俩试试,不然的话,这俩孩子也不服气!”
高桂珍说:“爸,您也就势歇会儿,我来扶犁杖。”说着,从高鹏远的手里抢过犁杖,说,“双喜、小艾,拉犁!”
小艾把缰绳绷得紧紧的,脸憋得红红的,铆足劲儿拉。
双喜当然也不甘示弱,再说,为了让小艾省点劲儿,就越发卖力。
高桂珍喊道:“双喜、小艾,使劲儿!”
耕地的犁杖往前动了一小段,停下了。
高桂珍继续叫道:“使劲儿,小艾、双喜!”她一走神,犁杖“呲”的一下子,钻出了地面,一下子被拉出好远。双喜和小艾双双趴在地上,来了个嘴啃泥。
小艾站起来,大声说:“双喜,来,我就不信,连一垄地也耕不成!”
双喜也站起来,连身上的土也不拍,重新把缰绳搭在肩上,猫下腰,喊道:“珍子姐,来吧!”
双喜和小艾拉着犁杖,使出吃奶的劲头,好歹拉了一遭。到了地头,一个个汗巴流水的。
小艾的刘海粘在前额上,汗水流进眼眶里,喘着粗气说:“都因为双喜不使劲!”
双喜确确实实为了让小艾省劲儿,暗暗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累得吐血,不吭一声。小艾却赖他“不使劲”,实实在在被冤枉了,可是,为了哄小艾高兴,他默默不语。
事已至此,小艾和双喜都无话可说,只好认输,一切重新开始。
到中午前,孙秀英家的地,好歹耕完了。
在回家的路上,小艾才发现珍子姐右肩的汗衫上,渗满了血。
小艾刚要叫,被高桂珍慌忙用眼神止住,示意她不必声张。
双喜走在最前面,唱唱咧咧的,听不出词,拿不准调,说增色也行,说烦人也并无不可。
小毛驴一路拉着犁杖走,一面吃路边的青草。
高鹏远一行人,冒着酷暑,耕完了孙秀英家的地,虽然,一个个累得烂蒜一样,可心里痛快。大家心里明白,这不比干自家活儿,这是自觉自愿地帮助志愿军家属,解决家庭困难,光荣!
高鹏远卸了小毛驴,正牵着往外走。
孙秀英跑过来,说:“别走,谁也不兴走。擎人擎牲口还擎肚子,都得吃完饭再走!”
小艾说:“吃完饭再走,行,饭呢?等吃上您家的饭,还不得等到老爷儿落!”
双喜也趁机说:“大热的天,谁等得起呀,各奔前程吧!”说罢,拽着小艾,一路小跑儿早飞出了院子。
高桂珍笑笑说:“这个双喜!”言罢,也随着爸爸走出栅栏门。
杨来顺越来越感到珍子姐的的确确了不起,于是,给双喜出了个主意,叫他写一篇纪实文章,就写珍子姐如何在村里搞宣传,如何帮助志愿军家属解决生活困难,题目就叫《河南村人民的好女儿》。
双喜知道杨来顺的画,画得确实不错,原本就喜欢听他的话,他给自己出的题目,说心里话,他也确实愿意写。可是,一想到珍子姐干了那么多好事,都写吧,嫌堆砌材料;精选一些吧,又担心不够全面。这些天了,拿起笔,放下;放下,又拿起,愁眉紧锁,呆头呆脑。
世界上的事,做也就做了,一拖下来,就不知道拖到何年何月。
杨来顺在这点上,比双喜强。凡是他想干的事,当机立断,毫不迟疑,说干就干。从顺义县城的四月二十八庙会回来之后,就在高桌上铺好纸,像农民下地,何以等到当午锄禾,那还不汗流浃背?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照猫画虎,模仿《清明上河图》,动手画起了《谷雨大河图》。
高桂珍总是闲不住,稍有闲暇,就想看看这老几位,祥林、双喜、小艾、石头、满囤。可是,她最关心的还数杨来顺。她知道,顺子正在谋划《谷雨大河图》,她总想给他出点儿主意。
吃过晚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摇着蒲扇,有的端壶凉茶,断断续续来到老槐树底下,坐在大青石上,你一句,我一句,山南海北地聊。出过远门的,南山打死一只虎,北岭活捉一只狼;城内年糕粘住嘴,村外西瓜甜掉牙。吹呗,都是些没影儿的事。闷在村里的,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六只眼;孩子睡觉尿屁帘,媳妇炒菜忘搁盐。俗不俗,雅不雅,咸不咸,淡不淡。初听有趣,再听乏味,老听心烦。也确有小伙子仰卧在凉丝丝的大青石上,看幽幽天空中的繁星,然而,却连一丝一毫“卧看牵牛织女星”的恬静也没;也确有大姑娘拿着芭蕉扇追打萤火虫,可是,却连一呼一哈“轻罗小扇扑流萤”的雅兴也无。
高桂珍不想在这人堆里闲聊淡扯,白耽误工夫,她要去看看杨来顺。她走着想着,想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杨来顺家的门口。她站在栅栏门外,刚要推门,可巧,杨二嫂手里拿着杌凳往外走,高桂珍笑笑说:“您是不是知道我来,给我开栅栏门呀!”
杨二嫂也笑了笑,说:“那是,那是。我还知道,你不是找我,是找顺子,对吧?”
高桂珍学着杨二嫂的口气,笑笑说:“那是,那是。”
“本来嘛,什么人找什么人。”
“顺子在家?”
“他不在家干嘛去?他呀,哪儿都不去,一丁点儿工夫也舍不得耽误,整天价画呀画呀,不知道他瞎画什么?你来了,正好,顺子听你的话,你帮我劝劝他,干点儿什么不好,非得画那破玩意儿!”
高桂珍听杨二嫂摆了一通,这才说:“年轻人,就该有梦想,有追求,哪儿能稀里糊涂混日子!”
杨二嫂说:“你也这么说!好吧,这么说,你倒能跟顺子聊到一块儿去。好吧,好吧,你去找他吧!”说完,“噔噔”走了。
高桂珍也不客气,直接进了屋。她掀开门帘看看,杨来顺正在聚精会神地作画。此刻,高桂珍真怕打搅了他,有心悄悄退回来,但又一想,不妥,到人家屋里又悄悄退回去,作贼似的,太丢人。于是,她鼓足勇气,干咳了一声,杨来顺依然作画,仿佛一丁点儿不知情。高桂珍又干咳了一声,杨来顺仍旧安详作画。高桂珍只得轻轻地走过去,小心地说:“顺子,这么专心致志?”
杨来顺对高桂珍的出现,感到十分惊讶,说道:“珍子姐,什么时候进来的?我正作画,你给看看!”
“我哪里会看呀!”
“珍子姐,你是劳动人民,人民最有权力评说。人民认可,就好;不认可,那就是不好。”
高桂珍笑笑说:“我只是人民中的一份子,只当瞎说,不要当真。”
杨来顺说:“在河南村,我第一个想听的就是你珍子姐,第二个想听的就是孔令洲。我认为,孔令洲可以代表知识分子,从艺术角度;珍子姐可以代表劳动人民,从思想高度。”
“什么艺术角度、思想高度,我是什么‘度’也不懂。”
“太大的道理,咱们不懂。可是,一件艺术作品,总得表现什么,表达什么?如何表现,如何表达?这些总得弄清楚吧!”
“甭说旁的,就先说说你打算画的《谷雨大河图》。”
杨来顺伸手搔了搔头皮,不好意思地说:“这些日子,我正做草图,这不,我打算这样安排,珍子姐,你看:这是戏楼,唱京戏的、拉洋片的;这是石幢,踩高跷的、变戏法的;东街,打铁的、缝鞋的;南街,焊洋铁壶的、镟笸箩簸箕的;北街,开药铺的,开饭馆的;西街,卖唱的、习武的;孔庙前,吹打拉唱的,吟诗作画的;高庙后,饮酒的,品茶的。另有,潮白河边,摆渡的,乘船的;田野里,放牧的,耕田的。远处,幽幽的狐奴山;近处,静静的潮白河。再加上半截塔、水簸箕、娘娘庙、罗锅桥,这些顺义特有的景观。五行八作,文武双全,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总之《清明上河图》上有的,我有;《清明上河图》上没有的,我也有。场面之大,人口之众,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至于用色,红黄蓝白黑,各种颜色有序搭配,色彩纷呈,流光溢彩,定然美丽无比。”杨来顺越说越来劲,妙语连珠,唾沫星子满天飞。
高桂珍一面看着杨来顺设计的草图,一面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解。
杨来顺讲完了,得意地望着高桂珍,似乎等待着她的夸奖。
高桂珍说:“讲完了?”
杨来顺说:“讲完了,就等着珍子姐批评呢!”
高桂珍笑笑说:“我早知道你志向远大,敢于向经典挑战。精神可嘉,精神可嘉呀!”
杨来顺讪讪地说:“莫非只是精神可佳?”
高桂珍说:“你的构想,当然可以。可是,你想没想到,搞艺术,除了敢于挑战经典,还要脚踏实地。看看你做好准备没有?”
杨来顺说:“这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上等的胡州画纸,苏州画笔,大中小楷笔,整整两套,一得阁墨汁,各种颜料,都是我舅舅从外地买来的。珍子姐,你看,做了这么多准备,还不充分吗?”
高桂珍望着杨来顺,说:“来顺,你说的这些,都是物质准备。”
“那么,还需要精神准备吗?”
“首先,需要准备的,就是基本功。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那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珍子姐提的标准太高了。”
“咱不要求那么高,最起码得画什么像什么。没有扎实的写生功夫能行?你瞄着《清明上河图》,并没有什么错。我只想说,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把眼前的事做好。”
杨来顺听了珍子姐的一番话,感到佩服,心说:珍子姐,真不简单,她怎么懂得这么多?
高桂珍说:“顺子,我想,你不妨就以《清明上河图》为样子,画一幅大画,要表现顺义县翻身解放的新气象,反映潮白河儿女为支援抗美援朝努力生产。”
杨来顺又搔搔头皮,说:“这、这大概不好表现吧?”
高桂珍说:“听我给你出出主意。戏楼唱戏,把演《龙凤呈祥》换成《小二黑结婚》,是不是就表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
杨来顺点点头。
“把拉洋片里头那些光胳膊露腿儿的大姑娘小媳妇,换成志愿军打美国鬼子,行不行?”
“唔。”
“田里,耕地、播种、锄草这些都行。能不能在地边坡岗上,添上兄妹开荒;在农家院子里,加上夫妻识字?”
“能。”
“教室里的黑板上,写着:天亮了,解放了;大街上的宣传栏里,画着:黄继光舍身堵枪眼、邱少云烈火中永生、张积慧击落戴维斯、严伟才奇袭白虎团。”
“中。”
高桂珍越说越兴奋,她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百鸟飞翔;宽宽的河面波浪翻,百舸争流。”
杨来顺激动万分地说:“啊呀呀,珍子姐,你提示得太好了,太有时代气息了!”
“我听说你要比着《清明上河图》画一幅大画,真为你这种敢想敢干的精神所感动。正因为你要作大画,费时费力,我总想找个工夫,赶紧跟你聊聊。”
“当然了,我不一定画得好。可是,我想,这样画,即使画不好,也有实际意义,能起到宣传作用。”
“我就怕你们走弯路。你听说没有,双喜要写我,还要给通州专区的《前进报》投稿。我立即制止他,劝他多读书,别瞎耽误工夫。你知道,作为庄稼人,一年到头,有空闲吗?没有,春夏秋冬,忙忙活活,急急匆匆,赶路搭车,月牙河的芦苇荡,潮白河滩的杨柳岸,多么美丽的景色啊,没有心思细细琢磨。回到家里,抱柴做饭、喂猪打狗、推碾子拉磨,哪里有一丁点儿空闲呀!我对你、对双喜说这么多,就是怕你们浪费极其宝贵的时间,却走了弯路。”
“珍子姐你叮嘱的话,太宝贵了。可是,你对双喜说不让他写你,那几句话,说得不对。他写成了,真能登在通州专区的《前进报》上,那不仅是双喜的成功,也是河南村的光荣!”
“这事,我往后再找双喜谈。现在,先说你创作的《谷雨大河图》,你先琢磨好了再下笔,做到一笔不少,一笔不废。”
“珍子姐,你咋懂那么多!是不是都跟孔令洲和他的老父亲孔大学问学的?”
高桂珍笑笑说:“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谁有学问,就向谁学,这话无论出自谁的口,都是对的。”
高桂珍和杨来顺正说得热闹,只听栅栏门“啪嗒”一响,顺子妈回来了。
杨来顺说:“我妈到外面乘凉回来了。”
高桂珍说:“那好吧,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该回家了。不能太晚,那样的话,我爸妈又该不放心啦。”
杨来顺说:“那也得等我妈妈进来再走。”
高桂珍笑笑说:“你呀,二姑娘梳头———多一抿子。哪有那么多事!”
话没说完,杨二嫂掀开门帘进来了,叽叽嘎嘎地说:“珍子,谁是二姑娘呀,你说小艾吗?”
杨来顺急忙说:“您别打岔,什么大艾小艾的,有她什么事,这都哪儿挨哪儿呀!”
杨二嫂说:“妈知道你喜欢小艾,可是,那丫头眼拙,瞧不出好赖。你就说双喜那孩子,蔫头巴脑的,哪有我家顺子招人疼。当然了,这话不好说,是得托你珍子姐当着小艾的面好好说说。”
高桂珍哈哈大笑,说:“猴吃麻花——满拧!”说罢,抬腿就走。
杨二嫂心里好生纳闷,心里说,这事闹的,是不是嗔着我回来早了。
“您咋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回来了?”
“什么事当着妈的面不好说,不就是小艾嘛,就算她跟连汤嘴娘儿俩一块儿来,老娘我怕她啥哩!”
月牙河的拐弯处,长着一大片芦苇,芦苇深处的苇扎,叽叽喳喳地叫唤,连绵不绝,吵翻了天。
从苇塘里流出来的水,凄凄凉凉,像一条青蛇在草丛里钻。凡是它经过的地方,小花颤颤巍巍,野草哆哆嗦嗦。是惊,是怕?谁能说得清!
大概青蛇也有爬累的时候,爬出草丛,在盆底坑盘踞休息,这就形成了月牙潭。
月牙潭的水清,透过水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潜底的鱼虾。在月牙潭的世界里,也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激烈争斗。
到月牙潭里打水仗的小孩子,扎猛子不必合眼,在水里也能看见对方,好开心呀!
可有一宗,要是远远地看见来了女孩子,不管他们其中的什么人,只要随便叫唤一声:“快,女孩子来了!”他们就会从月牙潭里“扑腾扑腾”跑上岸,抱起衣服,钻进芦苇荡,慌手慌脚地穿上裤衩,披上褂子,然后,再人模狗样地从芦苇荡里走出来。
高桂珍吃完了晚饭,打算先坐在罩灯下,看一会儿孔令洲老师推荐的《李家庄的变迁》。可是,刚刚打开书,满脸的汗珠子,就“哧啦哧啦”往下滚。她索性合上书本,站起来走到小姨的跟前,附在她的耳畔轻轻地说:“小姨,出去走走,行吗?”
珍子跟小姨要好,路人皆知。可是,高桂珍几乎从来不跟她一块儿散步,嫌她走路慢慢腾腾,嫌她说话吞吞吐吐。这次,珍子主动邀请她“出去走走”,而且还挺客气地征求她的意见,这很使李兰荣喜出望外。于是,她慢慢悠悠地站起身,面带微笑地说:“出去走走,咋不行?”
李兰英手拿蒲扇撵过来,把手里的蒲扇递给珍子,说:“上哪儿溜达去,天太热,拿着蒲扇,一边儿走着,一边儿扇着点儿,省得出汗。”
高桂珍推开妈妈的手,说:“不热,不热,哪儿那么娇嫩!”
李兰荣一把抄过来,说:“她不嫌热,给我。本来嘛,有偏有向咋的,到底是亲妈养活的!”
高桂珍笑笑说:“妈,您看,我小姨还吃心了!”
李兰英撇撇嘴,说:“她呀,就爱犯小心眼儿。”
李兰荣不再搭言,拍拍珍子的肩膀,轻声说:“走吧!”
高桂珍和小姨走出院子,消失在暮暮夜色里。
李兰英走到高鹏远跟前,小声地说:“珍子咋想起跟她小姨一块儿出去了,不知道憋着什么屁!”
高鹏远说:“什么话,珍子这么大了,你还把她当小孩子,说话没深没浅的!”
“本来嘛,这么多年,也没见珍子跟她小姨一块儿遛过弯儿!”
“那也不能顺嘴胡沁,牙碜!”
“你看,你看,我这一句话说的,倒招出你一大片话来,这都哪儿挨哪儿呀!”一面说,一面走进堂屋地,涮盆掸碗,“呱啦呱啦”,故意将坛坛罐罐磕碰得叮当乱响。
高桂珍和小姨一块儿,绕过老槐树的一排青石台阶,穿过小树林,出了村子。
李兰荣说:“走慢点儿,遛弯儿,又不是串亲戚,走那么急干什么?”
“你呀,比我才大一岁,摆什么老谱呀?你也就是一个又细又小的萝卜,长在背儿上了。要不,我干嘛管你叫小姨?”
“没大没小的,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高桂珍笑得更厉害了:“来呀,看,你的小胳膊,细得跟麻秸秆似的。还敢跟我动手,我慢慢一掐,你的小细胳膊就断了,你信不信!”高桂珍说着,就想动手。
李兰荣连忙说:“我信,我信还不行?”
娘儿俩一面说说笑笑,一面顺着弯弯曲曲的蚰蜒小路往前走,说是信马由缰,也不是,说是有个准确的落脚之地,也不像。总之,她们鬼使神差般地在月牙潭边站住了。走了老半天,累了,乏了,不由自主地就想拣块干松的地方坐下来。
高桂珍先坐下,抻抻李兰荣的衣服下摆,说:“还站着干嘛,又不是打站票。坐吧,还等着我给你搬一把交椅呢!”
“你这丫头,跟谁学的。你记着:嘴尖脖弯,撅着尾巴够着天!”
高桂珍笑笑说:“瞧我小姨,俏皮话还真不少!”
“说正经的,你勾引小姨出来这么远,到底想干什么?”
“这话说得真没劲,世界上,有哪个外甥女勾引小姨的?”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
“是你说的,又不是我说的!”
“好了,好了。越说越不上道!我只问你,约小姨出来干嘛来了,你要不说实话,那我可就打道回府了!”
“那好,这阵儿黑灯瞎火的,你一个人回去吧,看不叫狼吃了你!”
李兰荣听外甥女这样一说,真吓坏了,赶紧说:“哪儿有狼呀,真有狼吗?”
高桂珍大笑,说:“到底有没有,谁能说得清?”接着,她转了话题,“哎,小姨,你能不能给我拿个主意?”
李兰荣说:“看你叫我拿什么主意了?要叫我把你跟成子的恋爱关系揪断了,这主意我可不能拿!”
高桂珍听了,半晌不语。
李兰荣望着珍子,在幽幽的月光下,显得那么楚楚动人。她心里想,我要是成子,说出龙天榜来,也得娶她!可是,等了半晌,珍子也没有开口说话。她不耐烦地说:“咋了,哑巴了?”
在幽蓝幽蓝的天空中,弯弯的上弦月,挂在头顶上。金黄的月光,照在高桂珍的脸上,她的眼窝里,充盈着泪水。
是的,高桂珍争气要强。她深深感到,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有作为的中国青年,不应虚度年华与碌碌无为,而应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把整个青春,以至生命的全部,献给亲爱的祖国。
李兰荣看到珍子饱含泪水的一双眼睛,反倒勾起了自己的心酸往事。她说:“珍子,你是知道的,我一生下来,就没了亲娘。爹给我续了个后娘,虽说,她的心眼儿不是很坏,可是呢,砍的没有镟的圆。再说,当初,我那么小,没有奶咋活?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好你娘生了你,我爹把我送到你家,合着咱们娘儿俩,都是吃你母亲的奶长大的。”
“小姨,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我早就知道了。”
“你以为在亲戚家生活好受吗?小时候,小孩子家家不懂事,等我长大了,我可知道寄人篱下的滋味。”
“这么多年,难道我娘对你不好吗?要真是这样,我找他们去,给你评评理,叫他们无地自容!”
“不是,不是,你可千万不能做出那样的傻事。要那样,真正无地自容的不是他们,倒是我了,准得骂我没有良心。其实,这么多年,你爹娘对我一直很好。吃的,穿的,你我分不出两样。这还不好,还要怎么好?他们对我可真是一百一,一丁点儿旁的也说不出来!”
“我看你刚才眼泪汪汪的,还以为你受了天大的委屈!”
李兰荣说:“姐夫姐姐越是对我好,我越是过意不去。我干什么活,也别叫他们看见。干什么他们都会说,你放着吧!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总还把我当小孩子,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我不成废物了?”
“那好,他们不让你干家里的活,你跟我出去干。比如,帮助志愿军家属……”她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
“说呀,我听你的,你说帮助谁家,我就跟你去,还不行?”
高桂珍说到这里,仰脸望着幽幽的天空。
天上有什么呢?说怪也不怪,说不怪又怪。正当高桂珍仰脸的时候,一朵白莲花般的云彩,遮住了上弦月。漫天的星斗扎成堆,一个个眨着眼睛。
高桂珍心里骂道:“讨厌,有你们什么事,眨什么眼睛!”
“珍子,你好像憋着什么话要说,说嘛,小姨又不是外人。憋着,又不能下小的!”
“小姨,说什么呢,不嫌寒碜!”
“本来嘛,你看,小姨就不憋着,有什么心里话,都往外掏,哪儿像你。”
“小姨,我约你出来,就是想让你帮我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李兰荣笑笑说:“我外甥女也太抬举我了,我要是管不好,可别说我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高桂珍想了想,说:“从哪儿说起呢?又怎么跟你说呢?”
“你也犯不上跟我弯弯绕,绕弯弯。我是你小姨,又不是旁人。”
高桂珍清清嗓子,说:“新社会主张婚姻自主,以往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属于旧社会的臭礼法,应该扫除。你知道的,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双方父母就订了‘娃娃亲’,把我许配了成子。我这么小,就由大人们给定下终身大事。你说,这个属不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礼法?”
“那还用说!外甥女的鞋带儿——姨订的。”
“我作为河南村的团书记,应不应该带头破除这个旧礼法?”
“肯定应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切切实实属于旧社会的旧礼法。”
高桂珍望着小姨的脸,说:“前些天,我还就真的跟董大伯、孙大娘,直截了当地解除了我跟成子哥的‘娃娃亲’。当时,董凤才、孙秀英两口子一听,都傻眼了,哭着求我,可我一直坚持说,你们给我跟成子订的‘娃娃亲’,属于旧社会的旧礼法,我是河南村的团书记,应该带头扫除。”
李兰荣考虑半晌,这才说:“那你是不是又打算找旁人?”
高桂珍低下头,说:“其实,我解除跟成子的‘娃娃亲’,并不是想找旁人。谁都知道,我从小就喜欢成子哥,成子哥也喜欢我。”
“就是说,你还准备嫁给成子,是不是?”
“是,咋不是?”
“你不想嫁给旁人,就想嫁给成子。可又找人家父母解除‘娃娃亲’,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费二道手嘛!”
“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你前脚解除‘娃娃亲’,后脚又去说做成子的未婚妻。董凤才、孙秀英那老两口子,是省油灯嘛,就那么听你的!再说了,就算他们回心转意,答应了,不还等于‘娃娃亲’吗!”
高桂珍低下了头,她后悔当初不该那么冲动,匆匆忙忙解除“娃娃亲”。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转念一想,既然“娃娃亲”属于旧社会的旧礼法,咋就不应该扫除?她在这个圈子里,来回来去地绕腾,像是走入迷宫,懵懵懂懂,迷迷糊糊。她真的没了主意,真想扑进小姨的怀里,痛哭一场。
溶溶的月光,洒在高桂珍的脸上,点点泪痕,闪着光亮,把李兰荣的心刺得好痛。她轻轻地拍拍高桂珍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好吧,从头再来!”
高桂珍扬起脸,看着小姨,声音轻得不能再轻地问:“咋叫从头再来?”
李兰荣说:“你既然跟人家解除了‘娃娃亲’,就不该还回去说,你还愿意做人家成子的未婚妻。人家以为你把他们当猴耍。”
高桂珍说:“那怎么办?小姨,你是我的亲小姨,你倒是给我出出主意呀!”
李兰荣说:“这事闹的!”
双喜为了写《河南村人民的好女儿》,整天价吃不香,睡不着。他感到,像高桂珍这样的好青年,早该好好宣传宣传。双喜心里当然明白,无论写谁,即使是同乡、同学,要写得真实感人,必须得采访。可是,八字没一撇的事,双喜又不愿意叫街坊四邻都知道,倘若毫无结果,不了了之,岂不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笑料。嚷门打鼓的事,他不愿意。可是,不经过采访,这篇文章又该怎么作?双喜为此愁眉不展。
王发知道儿子心高,不管田里的农活多忙多累,回到家里还照样在油灯下读书写文章。在田里农活忙不过来的时候,王发也想跟儿子发脾气,可是,又一想,儿子这么争气要强,当爸爸的应该为此感到自豪才是。可是,生活是非常实际的东西,田里的农活,一样也少不了。春不种,秋不收;春争日,夏争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所有这些农谚,说的都是一个理,庄稼人,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磕头撞脑,没有空闲的工夫。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双喜还要抽出工夫读书,容易吗?当爹的不多担当点儿,等谁哩!
王发从房檐底下,轻轻地取下锄头,手里提着,慢慢地走出栅栏门,这才扛起锄头,往田里走去。
阴错阳差,王发在半路上,可巧遇上高桂珍。
高桂珍说:“二叔,去耪地?”
王发说:“地里的棒子苗都到腿肚子了,早该上二遍了。”
高桂珍说:“哦。”
王发扛着锄,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出老远,不知想起了什么,糊里糊涂回头看看,他看见高桂珍正推他家的栅栏门,心里说:“这个珍子!”边说边大步流星地朝庄稼地走去。
高桂珍轻轻地推开栅栏门,不声不响地走进双喜家。
双喜正在专心致志地看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被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弄得神魂颠倒。
高桂珍掀开门帘,看见双喜那精神专注的样子,又觉得不该打搅。
正在犹豫,突然,双喜发现了她,惊喜地叫道:“珍子姐!”
高桂珍呼啦挑开门帘,蹿到双喜的跟前,说:“双喜,看什么哩?”
双喜说:“珍子姐,你看,这就是小艾说的那本‘小火夫啃处女’!”然后,哈哈大笑,震得四壁嗡嗡作响。
高桂珍笑笑说:“笑啥哩?”
双喜说:“我在笑小艾,就为这本书,我怎么纠正,她都不相信,非说成‘小火夫啃处女’,疑心我不务正业,整天蹲在家里啃这种不正经的书。珍子姐,你说小艾这人,咋那么小心眼呀!”
高桂珍说:“女人的心男人不懂。姑娘的心,你更不懂。我告诉你,越是喜欢你的姑娘,越挑剔,那是担心你往坏里学。”
双喜说:“可是呢,我做什么事,读什么书,到什么地方去,她都问你个底儿掉,就像盘问汉奸似的,真让人受不了。”
高桂珍笑笑说:“你不会也盘问盘问她,看她受不受得了?”
双喜说:“我盘问她什么?问她做什么,她说,做鞋呢;问她读什么书,她说,不读书;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到苇坑边儿薅苗去。还问她什么,没的问了。”
高桂珍说:“小艾对你可真是一百一,你可不能没良心!”
此刻,双喜真的没得说了,双手不住地抠弄着对襟上的纽襻。
高桂珍说:“哎,你看看,孔令洲老师向我推荐一本书,你瞧瞧。”一面说,一面从兜子里把书掏出来,递给双喜。
双喜接过书看了一眼,说:“《李家庄的变迁》,这本书是山西作家赵树理的长篇小说,就是写《小二黑结婚》的那个作家写的。他的书,特别受到农村年轻人的喜爱。你看过之后,借给我看看,行吗?”
高桂珍说:“你先看。前几天,我跟杨来顺聊聊他画画的事。他总想画一幅大画,名字都取好了,比着《清明上河图》,叫《谷雨大河图》。”
双喜说:“顺子就是好高骛远,老想一鸣惊人。其实,弄文学也好,搞艺术也罢,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打好基本功。老想一口就吃成个胖子,哪儿有那么便宜的事!”
高桂珍说:“是这样,哪能还不会走,就想跑。不过,我看他画得还可以,像那么回事!”
双喜说:“文学艺术这玩意儿,可深了,你说齐白石、徐悲鸿的画就到头了?不是。你说孙犁赵树理的小说就写到顶儿了?也不是。珍子姐,我向你透漏一个秘密:我总想写一篇人物通讯,就叫《河南村人民的好女儿》。”
高桂珍急忙说:“不行,不行!”
双喜哈哈大笑,说:“瞧把你给急的,我也没说写谁呀,你着哪门子急呀!”
高桂珍说:“喜子,你也甭跟珍子姐玩儿里格楞,写别的,不许写这个,听见没有?”
双喜狡黠地笑笑,不说写,也不说不写。
高桂珍换个话题,说:“双喜,你这儿还有旁的书吗?”
双喜说:“我这儿旁的没有,就是有书。”说着,他打开书柜,“看,这些书都是从旧书摊上买的,还有就是我爸爸的爷爷留下的。这本《水浒》,前没头,后没尾。别看它破破烂烂,我还一直当作宝贝,连借都舍不得往外借。”
高桂珍笑笑说:“那么金贵的书,我也不借。我看看你还有什么别的书?”她把双喜的破书柜,翻了个底朝上,终于说,“把这套《红楼梦》借给我看看吧!”
双喜无限感慨地说:“这套《红楼梦》,是我姥爷从顺义县城的废书摊上得到的。古人说‘韦编三绝’,说的是,连接竹简的皮绳子,都给掀断了三次。再看看我姥爷的这套《红楼梦》,两层牛皮纸书皮,都翻腾烂了。这叫什么?这就叫‘书皮两烂’!哈———”
高桂珍笑笑说:“耍贫嘴,是吧?”
双喜说:“不说不笑不热闹。这回说真的,珍子姐,你真想读《红楼梦》吗?你看,《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都带个‘玉’字。两块玉合在一起,就成了‘和氏璧’,人间至宝。可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掺乎个薛宝钗,就把贾宝玉和林黛玉这块‘和氏璧’,给拆散了。”
高桂珍说:“你呀,醉雷公发疯——胡批。”
双喜眯起眼睛,半晌才说:“珍子姐,你看,你叫高桂珍,成子哥叫董世贵。你的名字带个‘珍’,他的名字带个‘贵’,合二为一,珍贵者也。就像两块铁矿石,投入熔炉,凝铸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