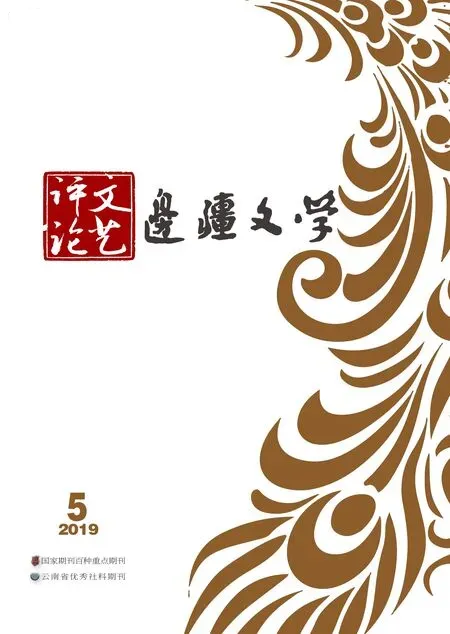用作品抵达一个民族的心灵,并非易事
——范稳访谈录
刘大先 范稳
受访者:范稳,1985年毕业于西南大学中文系,同年到云南工作,现任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发表各类题材、体裁的文学作品近600万字,已出版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十六部。含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代表作为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已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翻译成英文出版。《吾血吾土》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新近出版了第二部反映抗战历史文化的长篇小说《重庆之眼》。曾获第七、第八、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诸多国内重要文学奖项。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在欧洲、澳洲和美洲地区出版发行。
访问者:刘大先,1978年生于安徽六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Part.1
刘大先:范老师,我知道您是四川人,在重庆读了书之后,到云南省地矿局工作。我注意到您是1985年毕业,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而1985年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往往被视作是有着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在那之后是现代主义观念和手法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最突出的莫过于先锋小说。所以避免不了要问一个略显俗套的话题,那就是你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文学教育中更多接受的思想资源和美学资源有哪些?当时的风潮有没有对你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范稳:我虽然毕业后在地质部门工作了五年,但我上的是中文系。诚如您所言,20世纪80年代是个各种文学新观念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应该是介于接受传统教育和追逐现代观念之间的一代人,虽然那时的大学教科书以传统教育为主,从中国的四大名著到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都是教科书的要求。但西方现代文论的输入已经初露端倪,只是那是课堂之外自我阅读。记得是在上大三时(1984)开始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萨特、戈尔丁、加缪等名家的书。没有老师解读这些作品,尽管自己看得囫囵吞枣,半懂不懂,但凭着年轻人对新鲜玩意儿的热衷和追捧,已经隐约知道一场文学革命正在到来。我是在大二时就立志要当一名作家,开始尝试写小说(主要是写些短篇),所以也就不认真上课了。我写得也不算多,不过只是写“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东西,自然是稚嫩得可笑。那时的校园里有很多文学社,把文字变成铅字是那个年代许多文青的梦想,一首在校刊上或者油印小报上发表的小诗便可赢得漂亮女生的青睐。我差不多闷头写到毕业,一个铅字都没有发表过,只是收获了一纸箱的退稿。我已经知道自己短板——没有生活阅历。那时特别佩服那些77级、78级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的经历就像一笔带进校园的财富。所以,到毕业时,我本来可以留在重庆当高校老师,但我想一个要终生从事写作的人,应该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先贤教诲。于是我自愿要求去了云南,到地质部门工作虽然专业不对口,但让我有了接触社会、走向原野大地的机会。我至今很感谢我在地质部门工作的那五年。它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社会,甚至如何在野外生存。多年后我在藏区漫游,田野调查那一套就能驾轻就熟地运用了。我想一个作家的文学教育既来自于书本,更来自于社会历练。尤其是后者,会决定他写什么和怎么写,以及采用何种写作姿态。一个作家可以没有大学文凭,但是一定要渴望生活,拥抱生活。记得年轻时欧文·斯通写凡·高的传记《渴望生活》对我影响很大,作家就是要做凡·高那样固执坚韧、热爱生活和艺术的人。
Part.2
刘大先:一个作家在获得声名之前,往往有着有时候甚至是漫长的蛰伏期。我看您早期就写了大量作品,比如长篇小说《骚宅》《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中短篇小说集《回归温柔》《男人辛苦》,还有报告文学和文化大散文。但批评家和研究者往往是势利的,这些作品很少有人评论。这些不同的体裁和题材可能是您在进行一系列的尝试和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摸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寻找和建立自己的风格,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您就这些早期的作品做一些介绍和自我评价,我想很多读者可能并不熟悉。
范稳:早期的作品应该都是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大学毕业第二年我就开始发表作品,那个阶段主要写校园生活,或许离开了校园以后才能看清青春的飞扬如何灵动、诗意以及必须为年轻付出的代价,然后我又写了一些地质题材的作品,不算很成功,90年代开始写都市题材,年轻人愤懑、嘲讽、反叛、忧郁、彷徨等等的情绪弥漫其间。9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写长篇,先是应书商之邀写,那时是书商的黄金岁月,他们一本书可以包发几十万到上百万册,发行一本书在北京买一栋楼的传说比比皆是。有些有文学情节的书商也会来找到我们这些还未成名的写作者,几万块钱就买断你一本书的著作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呢。我将之视为学习写长篇的初步训练,你得讲一个好的故事,学会结构文本,写好自己的人物传奇。《骚宅》和《山城教父》,这样的书名你一看就知道是书商起的,写了两本之后就不再写了。当然纯文学写作也没有放下,毕竟是受过传统教育的人,对经典的东西还是深怀敬畏。我还在坚持写一些中短篇,在《上海文学》《十月》《大家》《萌芽》《青年作家》等刊物上都发表过作品,还得过“萌芽”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纯文学奖项。《冬日言情》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一本青春题材的小说。大约从1996年我开始研读明史,写了第一部历史小说《清官海瑞》。这应算是我进入历史题材创作的发端吧。材的作品。其实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云南的文学史,就会发现近现代最早的云南边地书写都是由汉族人完成的。从20世纪30年代艾芜的《南行记》,马子华的《滇南散记》,40年代西南联大的那帮大师和他们的学生们,到共和国建立之初以冯牧先生为代表的一帮军旅作家,白桦、公刘等军旅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领悟到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巨大创作推动力,就像水有了落差就会有动力一样。文化差异让人既有审美的距离感,又有求知欲和表达欲望。当然得首先克服文化背景不同所带来的障碍,但我认为这是可以通过学习、观察、体验去沟通和掌握的。有利的一面是你可以将不同的文化去比较、思索,产生某种对比之美,不利的一面当然还是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误读、图解以及浅尝辄止的呈现。至于在地域性写作中的遮蔽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表达能力不够精准、透彻、生动形象造成的。在现在这个网络化时代,似乎一切都很透明便捷,但能用作品抵达一个民族的心灵,还是不容易。
Part.3
刘大先:在您生活的川滇藏一带,是多民族混居、多民族文化碰撞交流的地区,云南也是一个文化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的大省,这实际上不仅存在着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也有少数民族文化与国外文化之间的接触与变迁。您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也会接触到许多少数民族乃至国外的作家和朋友,就您切身体验而言,您觉得民族文化在云南地域性的写作中有何遮蔽与呈现,有何利与弊?
范稳:我大约是在90年代末期开始接触到少数民族文化,之前不甚关心,认为我是一个汉族,与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骨子里流淌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因此无法写好民族题
Part.4
刘大先:“大地三部曲”是厚重而浩大的鸿篇巨制,是什么契机促使您进入到这样三部关于藏滇地域历史与文化的书写的?确切地说,当您在着手《水乳大地》写作的时候,后面两部有没有同时构思?还是在写完一部之后意犹未尽,又激发出新的人物、故事与主题?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外部来看比较松散,但又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您在最初的设想中,各部的侧重是什么?
范稳:1999年我参加了一次“走进西藏”的文化采风活动,有扎西达娃、阿来等人。那时是一个倡导作家行走的年代,有走黄河的,有走新疆的。我们七个作家从不同的线路走西藏,我走的是滇藏线。这是一次民族文化发现之旅,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才发现许多隐匿在崇山峻岭中的文化遗产,它们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广袤的大地上。尤其是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各种民族文化相互映衬交融、砥砺前行。我开始关注民族历史、文化交融、宗教信仰这样一些问题。不仅仅是在书房和典籍中关注,而是在大地上实实在在地考察、学习、体验。参加完这次活动后,由此和西藏结缘,我又回去了,把其中的几个点作为自己重点观察采访对象。这样一跑就是十年。过去我的写作几乎用不到采访本的,也不需要到处跑;开始做田野调查的工作后,我一年要用到两三个采访本。这种转变让我的写作走上一条新的路径。2000之前可以说我是一种没有目的性的写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没有根据地(生活基地)。开始写《水乳大地》后,我基本上把自己的写作锁定在滇藏结合部的澜沧江峡谷那一带,年年都在往那个方向跑,2003年还主动要求去那里挂职一年。当时也不知道写这样的题材出版社会不会出,有一些东西在当时还比较敏感。比如对外国传教士的评价以及他们在西藏传教的定性问题。《水乳大地》出版后反响不错,给了我更大的信心,才开始有构建三部曲的想法。《水乳大地》我想反映的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与信仰的交融和砥砺,是展现那片地域文化的万花筒;《悲悯大地》我写了一个藏人的成佛史,试图以此来诠释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大地雅歌》我写的是一场被信仰改变的爱情和因信仰而获得拯救的命运。
Part.5
刘大先:关于宗教文化与信仰的书写,必然会遭遇到的一个现实是,写作者必须要面对着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这种世俗化不仅仅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外部转变,在心灵和情感层面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并且人们在谈论和思考信仰的时候也已经无法再恢复到一种天人合一、灵肉一体的“纯真”状态中。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当代社会中的信仰问题的?这个问题有点抽象和浮泛,如何不好回答,那就谈谈您是如何看到您所遇到的普通藏人的信仰,以及您本人对待这种信仰的态度。
范稳:对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族来说,信仰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我特别注重一个人的文化背景,你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必然具备了那个社会的文化滋养。一个乡村藏族小孩童年的故事总是与大自然中的各路神祇有关,山是神山,湖是圣湖,喇嘛是受人尊敬的,活佛是带有神通的,是来到人间的佛。他们从小听到的乡村传说与故事都跟神佛有关。他们一出生就被喇嘛或活佛命名,他们的名字跟各路神灵有关,跟藏区的大自然有关。他们从小跟随大人去寺庙进香拜佛,去转经路上朝圣。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对信仰的认知而逐渐加深、牢固。这并不是一件刻意为之的事情,而是生活就是如此,也就很容易达到你说的那种“天人合一、肉灵一体的纯真状态”。而我们并不是在一个有信仰的环境中长大,我们从小读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里的神话故事并不能给我们宗教文化的滋养。尽管唐僧去西天取经是为了弘扬佛法,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孙悟空。因此,要论及现代人的信仰,我们大多数人是先天缺失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现代物质社会的高度发达和过分喧嚣中,渴望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片净土,于是他们找到了信仰,净化灵魂,克己利他等等。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高于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人,更好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遇到人生困难了才想到信仰,这不是对信仰的追求,是对信仰的索求,是和信仰做交易。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宗教,其实都有世俗化的一面,关键只在于信奉它的人,采用何种姿态和什么样的心与自己心中的神契合。
Part.6
刘大先:抗战题材的写作在这几年成为一个小小的热潮,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有很多作品。这当然有着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召唤在背后起作用,但一个有着明确创作意识的作家显然会有着自己的考虑的主张。《吾血吾土》涉及到远征军题材,也出现了许多纪录片、电视剧、小说乃至学术研究,您在选题和构思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写作区别于其他人的作品?
范稳:我是从2011年开始介入抗战题材的研究和写作,我所生活和工作的云南是当年滇缅战场的发生地,也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所在地。关于滇缅战场,我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知道了,滇西抗战战场的遗址都去参观过,史料也接触到一些,但那时兴趣点不在这个上面。2011年我去腾冲参加了一次迎接战死在缅甸的抗战老兵骸骨回乡的活动,并结识了一批抗战老兵。于是,一段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在我的面前豁然打开。诚如你所言,抗战题材写的人已经很多了,它不像我先前从事的藏区题材的写作,有某种陌生化和神秘感,这让作者会占一些题材方面的先机和优势。在做《吾血吾土》的田野调查时,我采访了约50多名抗战老兵,他们的抗战经历和人生命运让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他们走向抗日前线?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愿当亡国奴,哪怕他是一个被抓的壮丁兵。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家既是国,国就是家,国家都亡了,又何以为家?这是那个年代任何一个善良、正直的中国人普遍的想法。他们这个想法来自于我们有着数千年文化传承的家国情怀,来自于那些有良知、有责任、有道德、有文化的爱国者的奔走呼吁、身先士卒。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为抗战摇旗呐喊最为积极踊跃的是学生和他们的先生们,他们在抗战中的作用不容低估。更何况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学子投笔从戎的感人故事,促使我在思考抗战题材时,更多的是从文化抗战方面去着手。因为我们的文化,在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面前,既是值得骄傲的,也是保持了尊严的,更是支撑我们坚持了长达十四年抗战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强大基础。
Part.7
刘大先:“重庆大轰炸”和战后索赔方面的文学创作为数不多,《重庆之眼》无疑是一个重大题材的创新。我觉得在小说的历史观对于此前已有的叙事史观而言,是一个突破,既有别于革命史叙事、英雄传奇叙事的主旋律套路,又没有落入个人史与家族史叙事的“新历史主义”窠臼,它让一度处于文学暗角的尘封往事重新浮出水面,将个人遭际与更广阔的社会语境变迁结合在一起。那么请您谈谈个人对于当下历史题材写作的观察心得与体会吧,不一定局限于抗战历史。
范稳: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一方面虚构历史、戏说历史大有市场,另一方面真实的历史、有价值的历史又常常被遮断和遗忘。比如重庆大轰炸这段历史,即便是土生土长的现代重庆人,直到20世纪末期,除了老一辈人还有记忆,新中国建国以后出生的人们仿佛才恍然想起,自己的城市居然也有这样一段悲壮的历史。我80年代初期在重庆上学,对重庆的文化抗战竟然也一无所知。我的母校的前身,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抗战时校址在沙坪坝,也曾遭受过惨烈的轰炸,师生无辜殒命,校舍断壁残垣,而我在读书时对这些史实浑然不知。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的寓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其实就在我们的校门外走路不到十分钟的地方,但我那时居然都没有去看过(当然,那时也不像现在,都恢复重建成相应的纪念馆,上现代文学课老师也不会更多地将教科书上的东西与历史现实相结合)。历史的河流太容易被阻断,被尘封。我认为,文学的功能应该有恢复历史记忆的责任,这应该是我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初衷。当然我希望自己笔下的历史再现是具备了文学性和艺术欣赏性的,是在尊重历史基础上的虚构和再创造。历史的真相本来就在时间的纵深处,我们要去发掘、梳理、研究、再现,并归纳出可以观照现实的文学真实出来。比如你提到的战后索赔,就是我们回望历史中一个不能回避的战后遗留问题,我们也完全可以将之上升到反思战争的高度。应该承认,战争文学是最好的战后反思形式之一。过去我们所见到国内的战争文学,更多的是从家国命运、人性、人的命运等方面来反思战争,或者描述随着战争一同而来的革命。我们是个多么善于内省的民族,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对战争责任的追问,在我看来,甚少于对战争残酷性的描写。西方世界从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从哲学、文学、历史学等方面来反思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深重灾难的法西斯主义从此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大海对面那个给我们带来深重战争灾难的侵略国家,现在却期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把自己的战争罪行洗白得一干二净,能狡辩的则狡辩,能抵赖的则抵赖,能遗忘的就刻意地遗忘,甚至不惜把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中国人忽然发现,铁证如山的事实,譬如南京大屠杀如此巨大的民族创伤,居然在某些日本人口中并不存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甚至连被国际法庭判处极刑的甲级战犯也俨然成了大和民族的“英雄”。他们否认历史,拒绝谢罪,其最终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逃避战争责任,重启日本的帝国梦想。
在重庆的采访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朋友们。中国的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运动始自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然觉醒的中国人再不能容忍自己的父辈祖辈所遭受到的苦难被忽视、被歪曲、被不公正地对待,再不能漠视日本右翼对历史的歪曲颠倒和一再挑衅中国人民的尊严底线,对日索赔运动在华夏大地方兴未艾、风起云涌。从中国劳工索赔案、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细菌试验案、慰安妇索赔案、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平顶山大屠杀、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等,共有二十多起对日索赔案直指那个应负起历史战争责任的政府。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相关新闻报道,而文学的书写却相对较少。战争索赔是一个复杂的国际问题、法律问题,可对一个战争受害者来说,却只是讨个说法这样简单的道义问题。在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们的接触中,我才慢慢地发现,这群白发苍苍的战争损害索赔者,实际上在向我们这个社会传递着某种久违了的精神气质——维护民族尊严的勇气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自信。一个受害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去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些日本人不会晓得他们在重庆犯下的罪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过去普通日本人只知道东京大轰炸,不知道重庆无差别大轰炸。可是天下哪里有作为加害者不受到惩罚并为自己的加害行为道歉的道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对日索赔,我认为是一座城市的声音跨越了国界的呐喊,是一个个普通平凡的中国人自觉肩负起来的民族尊严和世界正义。中国人到日本,并不仅仅只有游客和买电饭煲、马桶盖的扫货大军,还有这样一群肩担道义的人,他们是21世纪的“抗日远征军”。
我自认为是一个对现实缺乏把握但还有点历史感的人,这种感觉让我对自己的写作还不至于失望。过去我在提笔写作前总是行走于大地,现在我更多地穿行在时间的经度和纬度里,寻找那些遗失的珍珠和还在闪闪发光的记忆碎片。而一个作家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碎片”连缀起来,使它们成为一部好看的小说。
Part.8
刘大先:新世纪以来当代长篇小说的写作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现实主义的回归。这种现实主义无疑汲取了现代主义艺术在形式、手法和美学上的经验和教训,这在您最近的两部长篇小说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人称您的《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是对历史的“正面强攻”,其中可以看到您下了很大功夫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在将史料转化为文学的时候,您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的?当然,真假、虚实都是相对而言,没有某种本质性的真与假,这其实也是关乎小说写作的一个根本性命题:何为“现实”,怎么样呈现“现实”?您怎么样看?
范稳:我相信对于每一个从事历史题材的写作者来说,他的一个梦想或者说终极目标就是期图用文学的真实来再现历史的真相。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历史的真相常常被搞得皂白莫辩或者模糊不清。历史题材的小说首先它是小说作品,我们就得遵循小说创作规律,其次它又为历史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所界定,让我们在创作中必须尊重历史,以历史为基础来进行文学创作。一个作家也许很难回答在他的作品“真实”与“虚构”各占多少百分比,就像难以回答其中的某个人物或情节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我们只需看他是否尊重历史就可得出自己的判断。“尊重”一词说来简单,真正做到却不那么容易。就如你说“尊重”一个人,但难免也有误解、抱怨,或者伤害。历史那么宏大的一个词,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怠慢了,就误读了,甚至亵渎了。在历史题材的书写中,任何一个写作者的认知都是有局限的,他只能尽量地消弭、缩小这种局限性,让他所反映的那段历史,更接近真实和真相。而一部历史题材作品让人有真实感,或许就是你提到的“现实”感,即让人有回到历史现实的感受。所谓“身临其境”,这个“境”可能是过去——历史现实,也可能是现在——身边现场。至于作家该如何去合理有效地呈现,那真是各显神通的问题,难以一言蔽之。
Part.9
刘大先: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有着充沛创作欲和高效行动力的作家,您下一部作品的计划是什么?
范稳:我还想沿着自己文化抗战的思路再写下去,以构成自己的“抗战三部曲”。现在还在通读相关史料和酝酿构思中,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完成,因为越往后写,压力越大。尽管我进入这个领域已经有些基础了,但超越自己,总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