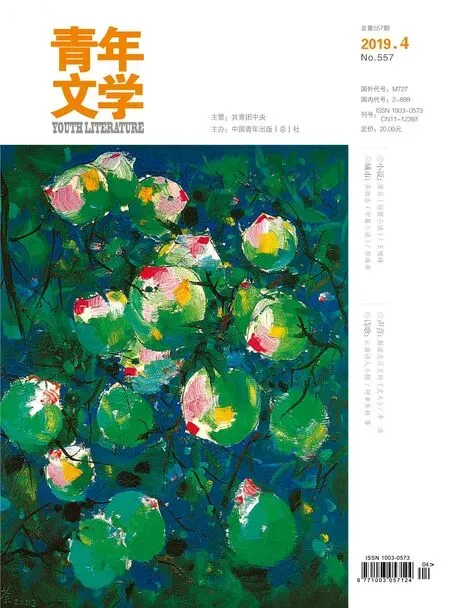歌 声
⊙ 文/草 白
一
傍晚时分,他才手脚发僵地从驾驶舱里爬下来,穿过黑暗中的停机坪,沿着那条看不清的沥青跑道,步态摇晃地往宿舍楼方向走去。在林的身后,在那些空旷而黑暗的地方,仍有引擎转动发出的轰隆声,炸弹的爆炸声,以及人世间的各种声响,持续不断地发酵着,无意识地推搡着他,似永不会终止。
他的记忆和头脑一片空白。——有一瞬间,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
几乎用尽所有气力,他才靠近那树影下的宿舍楼。尽管疲惫不堪,他的身形仍是直挺挺的,好像在他体内有一根支撑物,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他松垮和懈怠。他走进那个房间,屋舍里的摆设照旧,被褥齐整地叠放着,似在等待他的归来。他走过去,走到那张椅凳边,战栗着坐下。衣物早已湿透,靴子里也全是水,如往常那样,他有条不紊地处理完这一切,就在那狭窄的床板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好似,那过去的三个小时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那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闷热,酷暑,浓烟滚滚。刺鼻的硫黄味,无名的呐喊声,在所有尘世的空间里回荡。
飞行员林在那天的日记里如此写道:
……今天,Y驾驶着他的飞机朝敌机俯冲而去。他的身体和那架霍克式驱逐机,如今都成了碎片。他死了。尽管我们都已做好死的准备,但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我还是不能接受。如果死的人是我,他大概也会这么想的吧。明天一早,我就要把遗嘱和照片交给荻小姐。这是Y生前嘱咐我的。我一定要办到。如果她要我回想Y生前的最后一幕,我不知该怎么说,没有人可以体验那种感觉,那些地面上的人是不可能体验到的。他们会痛哭流涕,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
林和Y是从北方校园一起过来的。有一天黄昏,他们在灯光昏暗的大礼堂里遇见了。演讲者一个个走上台去,带着悲愤和热血。那些悲愤和热血在扩散,形成一股冲击波,使得更多的人从角落里走出来,走到那舞台上去。
礼堂很大,灯光永远不够明亮。年轻的声音在回荡,在消散。几乎是一夜之间,学校里变得空荡。很多人离开了。没过多久,那些牺牲者的消息像风一样吹来。他们感受到了某种变化,但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不知道那些消息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天清晨,未名湖结了冰,湖畔的草丛里落满霜花。在湖边,他们再次相遇了。
Y望着他说,我们要去吗?
他点了点头。
——那我们去吧。
于是,他们就这样“去”了。杭州东郊,一个叫笕桥的小镇,中央航空学校的所在地。第一次看见那么多飞机,那么多轰炸机和战斗机。他们的生活严肃而刻板,训练场、宿舍楼、食堂,三点一线,后来,他们就开始飞天。在接受飞行训练的同时,他们也接受了死亡训练。只要需要,他们随时可以奉献出自己的身体,让它成为炸弹,成为武器,与敌人的飞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一起变成碎片。
没有人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去,为什么如此义无反顾,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解释那个真理,而引导他们前往的正是那个真理。
现在,Y为这个真理率先牺牲了。
林熟悉Y所去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弥漫着云朵、彩霞,充斥着无边的寂静的地方;那个地方不在地上,而是在空中,在云朵之上,一个永不会坠落的地方。
“他牺牲了,叫我把这些东西留给你。”这话像是台词,是他在脑海中排练过无数次的。可当见了面,他什么话也说不出,那个叫荻的姑娘早已哭成了泪人。
在“宣布”完Y的死讯后,他匆忙逃走了。盛夏的午后,整个河上镇俨如一座空城。那位哭泣的姑娘站在桥上,整个人浸泡在泪水和汗水之中。
他甚至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说。
后来,当再次回到天上,他时常想起那一幕。他把死亡这个沉重的包袱丢给那个姑娘,把所有的绝望都给了她。他不愿想死亡的事,自己的死亡并不可怕,因为真到了那时候,他什么都不会知道。
黑夜里,他在云层的内部飞,引擎的声音在耳边轰响,不知道那些积云到底有多厚,要飞多久才能飞出去。他让飞机上升到两千五百米的天空,又下降到一千米的地方。黑暗中,只有机翼上那盏灯,闪烁着微弱而湿漉的光芒,始终陪伴和照耀着他。
机舱里有美酒。那些被携带到高空的酒液,在回到地面后变得清凉、甜润,有一种婉转流淌的气息。带着那些美酒,他和同伴们去醒村张太太家参加聚会。
每个星期六晚上,那些年轻的飞行员聚集在那幢充满音乐和美酒的23号别墅里。别墅一共有两层,砖木结构,外墙为黄色。台基上开有防潮孔。房子门前有一棵桃树,两棵桂树,三棵银杏。花园里种着栀子花、绣线菊、美人蕉、茉莉,还有成片的绣球花。
它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人们要踏着台阶,走完最陡峭的几步,再经过一段平缓的坡地,才能走到那块台地上,进入那个美妙的屋子里。
第一次去,林和Y便喜欢上了那里。一楼客厅很宽敞,暗红色墙面,瓷砖也是暗红色系,靠墙有立式钢琴,一长排欧式沙发,还有壁炉。
他们的座位在壁炉与通道相连的地方,既可以随时望见进出的人群,也能将屋内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那是冬天,火炉里的干木柴噼里啪啦地响,松枝的清香四处漫溢。所有人脸上都浮现出一种沉醉的表情,眼神迷离,不知今夕何夕。他们听着音乐,喝着美酒,轻声交谈着;或仅仅是坐在那里,在众人之中缄默不语。
那时候,战事还未大规模爆发。客厅角落里那架木质留声机总是循环播放着那些动人的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费加罗的婚礼》或者《塞维尼亚理发师》,那些灿烂而高亢的声音,从那个山坡上的房子里飞出去。
作为曾经的声乐系女生,张太太最喜欢的还是意大利歌剧《拉·瓦利》中的《再见,我将去远方》。兴致起时,她也会跟着留声机里的意大利女歌唱家大声歌唱。那些高音像泉水从高处的山谷里飞溅而下,中音又非常雄浑,最迷人的是中低音区,气息深而下沉,音质通畅、明媚,毫无阻隔。
谁也不会像张太太那样注意女高音歌唱家低音部分的迷人之处。歌声在房间里缭绕着,穿过窗户和门厅,飞到屋外的竹林和绿荫中去。
当他们都在天上飞的时候,美丽的张太太就斜倚在卧房那张高靠背酒红色丝绒的沙发椅上,美容师坐在脚边那张矮凳上,替她修剔指甲,与她闲聊。
自从来到醒村后,作为随军家属的张太太一刻也没让自己闲着,组织牌局、音乐会、酒会、给年轻人牵线搭桥。她顶喜欢热闹,喜欢那些年轻而活泼的男人、女人围在她身边。
那时候,张先生的飞机还在天上飞,南京、上海、武汉到处飞,去执行他的军务。
夏天的黄昏,张先生终于飞回来了,并获得一个完整的休假。为了庆祝张先生的平安归来,张太太决定在他们的房子里开音乐派对。她邀请了许多人。醒村里的年轻飞行员,带着各自的女朋友,都赶来了。
山坡上,23号别墅灯火通明。江南的夏天虫鸣蝉噪,闷热不堪;那个屋里却一片清凉。他们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听着音乐,喝着美酒,听从女主人的安排。派对要到午夜之后才结束,音乐会之后是舞会,中间会供应自助餐,既有西式点心,也有中式小吃。
谁都知道,醒村最好的厨师在23号别墅里。
时间慢慢过去,那些冰块在木桶里一点点融化。Y和他都注意到了那位姑娘。她坐在角落里那只几凳上,微侧着身,似乎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月白色短袖旗袍,鹅蛋脸,一对清炯炯的大眼睛。一侧头发微微拢在耳根后边。当与人说话时,更显出稚气未脱的神情。
那晚,她唱的是李叔同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在学校里,Y和他也唱这首歌。他们无数次唱过这首歌。可当他们聆听着这位江南姑娘的清唱时,还是流下了热泪。那个夜晚,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
那些无法回首的往事,在彼此的记忆里翻滚。
Y在林耳边喃喃自语,说那个唱歌的姑娘很像他的妹妹。那时候,林还不知道Y的故事,并不知道他的妹妹已在北方的战事中不知所踪。当他知道这些的时候,Y已经不在人世了。
姑娘的名字叫荻。
二
那些夜晚,他们带着任务,飞得很高很远,就好像在夜晚的海面上航行。——天空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夜航,让林和Y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星星。那些闪烁的星群,那种旷古恒久的寂静,就好像时间从没有流逝过,世间万物不曾开始,也不会结束。
有些时候,他们忘记了航标,好像正在执行的任务变得虚无;对天空来说,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而地面上正在进行的战争和杀戮,只不过是一个玩笑,很快就会被纠正过来。
机舱室里回响着马达的震颤声,仪表盘上的指针在转动、变化,发出预警信号,告诉空中的驾驶者时间正如何一秒复一秒地前进,即使在天上,他们也无法摆脱它的控制。
有些夜晚则漆黑一片,他们在那空无一物的云雾之间飞行,没有目标,没有参照物,与地面世界忽然失去联系。在完全的黑暗中,他们飞了很久很久。耳边只有引擎发出的轰鸣声。当飞机终于穿透云层的刹那,眼前忽然出现光亮,来自遥远地面上的灯火,让他们有一种接近家园和真理之感。他们来自那里,亲人们都生活在那里,最终,他们还是要回到那些房屋里,田野和大地上去。
有一天,Y偷偷地告诉林,他将荻带到天上去了。林对Y的疯狂感到惊异。不过,他很快就理解了。那应该是荻第一次近距离地望着舷窗外的云雾和蓝天吧,同时,她还会看见地面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像血管那样四方辐射的城市和乡村的道路,忽然变得遥远的大地和日常生活,听见耳边呼啸的风声以及发动机的转动声……他们虽然处在那么一个高速飞翔的空间里,却比在地面时还要感到安宁和静止。——那种感觉是地面上行走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当Y的身躯从地球上消失,林常常想,当初他将她带到天上,或许就是为了有一天让她可以想象那个地方。他要让她知道,他最终将消失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机舱里摆放着成箱的葡萄酒,那些美酒在寒冷的作用下,变得格外清冽而甘甜。他们在23号别墅里饮过那些酒。在酒精的作用下,Y开始像孩童那样手舞足蹈。他有一张漂亮的脸,还有灵活而文雅的举止,但这些东西一旦与他职业性的严酷和冷静结合,便让荻感到陌生和吃惊。好像她从来就不认识这个年轻男人,这个二十一岁男人有时候会变得如老人般缄默不语。
事实上,出入23号别墅的年轻飞行员,都有一张相似的单纯而冷静的面容。只有在音乐和美酒的刺激下,他们才会容许自己进行激烈的娱乐。
Y的敌人,那些驾驶九六式战机的年轻人在上天之前会喝一种叫“航空元气酒”的东西,喝过那种酒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活着回来——他们也没打算活着回来。
死亡是什么呢?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关于死亡的任何事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都是活着的。他们在对活的恐惧中,邂逅了死。可以说,是死亡安慰了他们,将他们的身体接走。
飞行员林的文字之旅,其实在Y于地面上消失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种东西与其称之为日记,不如说是回忆录。因为里面的叙述时间是错乱的,次序是颠倒的。关于吞噬Y的那场大火,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并无任何记载。当时间过去很久之后,那一幕忽然在他的日记里反复出现。
……那一刻非常短暂,短暂到我只记住了那张脸庞,因肉体痛苦忽然抵至巅峰,而扭曲的脸。但没有声音。我没有听见那个方向传来的任何声音。然后飞机就往下坠落了。
现在,我甚至想,在那一刻,Y并没有任何痛苦。所有的痛苦都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昨夜梦里我再次看见了那张脸,这一回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张极度扭曲、静止的脸上显示出的却是强烈的镇定感。那是一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情绪。好似那一刻的到来,是那张脸期待已久的,它在回味那种感觉,只为了永久地记住它。
而当到了另一时刻,当飞行员林执行完任务回来,他对Y临死前的记忆又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死亡簇拥在他身边,他自己也在此队列之中。战友们在起飞之前平静地告别,或者只言片语的遗嘱,有些人再也没有活着回来。
后来,他们连告别的时间都丧失了,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一天之内不断进行的起飞和降落,好像非要把这具肉身白白地抛掷在天上不可。
23号别墅成了真正的军中乐园。留声机里的意大利歌剧早已换成周璇的《西子姑娘》,那一首曲子被反复播放,除了饮酒、唱歌、跳舞外,他们之间很少有人高谈阔论。
在别的场合经常进行的时事谈论,在这里很少出现。那些年轻人显得格外安静;因为当他们在天上飞的时候,也没有人与他们说话。当某个人起身清唱某支曲子时,他们也会跟着哼唱起来。那种集体合唱所发出的声响,那几乎相同的神情和举止,充满着热烈而持久的欢乐,好像死亡并不存在。
那天晚上临近散场时,女主人张太太忽然从座椅上起身。人们这才发现她喝醉了,她身体前倾,有些站立不稳。他们之前的担忧得到了证实。
年轻的飞行员犹豫着是否要上前去搀扶住她,可那个身影已经飘移到留声机前。那一刻,人们感到她的身体忽然变得干枯、轻薄,好像一阵微风就能将她吹倒。灯光下,她颧部发红,汗水涔涔。整个晚上,她一个劲儿地往喉咙里灌酒,好像已经渴得不行了。
她开始大声而含糊地说话,说你们都别走啊。但没有人听她的。场面有些混乱,他们正在整理随身携带的衣物,准备离开。有人已经穿过客厅,来到外面的露台上。深秋的露水沾湿了植物的叶片和花瓣,湿漉的凉意从前厅的玻璃窗外渗透进来。
客厅里忽然响起歌声,那是留声机的声音关闭很久之后,他们第一次听见有人在唱。那些已经穿过露台,走到花园里的人不由得停下脚步,站在原地聆听着。
这是乱世,天空呈隐隐的血腥红,月亮内部蒙着一层淡淡的荫翳。山河大地,正在沦陷。
更多的人还留在客厅里,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像在等待着一桩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女主人低声唱着那支《西子姑娘》,声音像珠玉一般滚落。所有那天晚上在场的人都说,从来没有谁把这支歌唱得如此轻柔、婉转,充满着柔情蜜意,好似天使的光辉照临人间。
他们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消息已经得到证实,飞机残骸被找到了。最后的时间到了。23号别墅的灯光,要永远地熄灭了。今晚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柳线摇风晓气清
频频吹送机声
春光旖旎不胜情
我如小燕
君便似飞鹰
轻渡关山千万里
一朝际会风云
至高无上是飞行
殷情寄盼莫负好青春
……
一曲终了,女主人微笑着道晚安。她说,再见了,年轻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她的酒已经醒了。灯光下,她美丽的脸庞上带着一种热烈而绝望的表情。
众人鱼贯而出。他们脚步齐整地穿过门厅,走下山坡,走进那片黑暗之中。头顶传来轰隆的声响,不远处的沥青跑道上灯火闪烁,飞机正在穿越云层去往远方的战场。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这群从欢宴上返回的年轻人,带着酒精和醉意,很快进入睡梦之中。
三
飞机迫降在一座丘陵上。
林睁开眼睛,四周一片漆黑,除了头顶上的星空,眼前一无所见。他干脆闭上眼睛,双手交叉着放在脑后。黑暗中,他意识到自己躺在一块庄稼地上,脚下大地的松软让他感到安稳而踏实。他感到自己的腰、背和四肢,都紧贴着地面,中间没有一点空隙,整个身体被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力量深深地吸附。
很快,他就体验到了一种美妙的依托,那么牢靠和安全,再无坠落的可能。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可能相当危险,没有现成的食物和水,或许需要很多天才能回到他们中间。如果是在沦陷区的话,那后果更不堪设想,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等待他的将是酷刑和死亡的威胁。
但这些可能到来的危险并没有进入他的脑子。此刻,他并不受那些还未发生的事情的困扰。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危险,好像永远也不会出现。他并不在意它们。他的思绪在别的地方,整个人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所包围。这不是劫后余生带来的。他很明白,从那一刻起,自己的生命被改变了。即使此刻是世界末日,他脑海里的那个东西也不会被驱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驱散那种感觉。
一开始,他并没有意识到幸福感的来源。随后,当再次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形象。他马上明白了一切,对那个人的回忆和思念占据了他的脑海。为着这个惊人的发现,他忽然想大吼一声。这个世上的事情总是出人意料。他的手在短暂几秒钟之内触摸到了那些尘土,想到已经丧失在空中的方向盘,想到他和他的飞机都被摔到了地面上。
但他并没有想飞机的事,也无法回想那一刻是怎么发生的。他的心完全被另外的东西占据了。
那个小镇上,她站在一家裁缝铺门口,好像是在等人。头发剪得更短。她瘦了,尖着下巴,那张鹅蛋脸不见了。远远的,他只看了她一眼便匆忙走开了。
在许多天之后的日记里,他回忆了那一幕。
她就站在那个台阶上,那些人从她身边走过,他们都是附近镇上住着的人,他们是来赶集的。我不知道她为何而来,她在等人吗?可她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等待的表情,我无法从她脸上读出任何表情。Y的离开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已经忘掉他了吗?还会有人和她提及他吗?她怎么能忘掉他呢?
就这样,我无意识地从她身边走过,走到离那个裁缝铺很远的地方,我才忽然想起应该过去和她打个招呼,问问她过得好不好。
即使那时候,我还是有机会回头的,她应该还在附近,不会走远。可我并没有那么做。我甚至没有感到从此之后可能再也不会遇见她。事实上,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离开了笕桥。
后来,他们被派遣到别的地方,南京,武汉,重庆,到处飞,到处去执行任务。有时候,林会忘记自己身处何地。所有地面之上的天空都如此相似,不同的是,飞机打乱了云朵的聚散,炸弹爆炸产生的烟雾充斥着那个空旷的地方,引擎的轰鸣声震碎了天空的寂静。
地面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到处都是饥寒交迫的面孔,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会什么时候结束,或许当结束的那一天,很多人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获救之后,当林返回队伍之中,发现有更年轻的生命永远离开了。人们对他的归来并不感到吃惊,也没有人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头盖骨和身体的碎裂每天都在发生,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显得疲惫不堪,根本没有精力去谈论什么事。当他们在天上飞的时候,脑子里也只有那些罗盘和仪器。
林开始给那个叫荻的人写信。他在信里说着那些天底下最冷静、最热烈的话。在那一刻,他不再想罗盘和仪器的事,耳边也没有引擎的轰鸣和炸弹的喧嚣,只有那些话,自己对自己说的话,非说不可的话,让他觉得自己还踏踏实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近,我常想起故乡河道上的那些采冰人。我的一个亲戚也是做这一营生的。还在哈尔滨上中学时,我经常跑到松花江上去看他们采冰。亲戚干的是断冰这个活,脚下的冰被他一块块断开,活动空间越来越小,眼看着落脚点没了,非常危险。工友们提醒他小心,可每次他都哈哈一笑,说没事的,最后也总能找到退路。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家里人告诉我那个亲戚死了。他把脚下的冰采完后,自己没了容身之处,还浑然不知,最后跌落在冰窟窿里,活活冻死了。死前,他还叼着烟,与人说笑。尸体打捞上来的时候,还是那种表情,活生生的,一点也没走样。
现在,我忽然能理解他了。即使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跌入冰窟窿中,随时可能丧命,他还是这么做了。我今天的处境也是如此,没有未来可以预期,只有眼下,这架我所栖身的飞机,它是我可以支配的。我在那上面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有意义的,没有人可以告诉我那种意义是什么,唯有我自己可以赋予它。
你在云朵下面行走,而我在天上飞。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给你写信。是给你,而不是给别的姑娘。我总觉得你比别人更了解我们。只有你。毕竟,你在天上飞过,亲眼看过那个世界。当你在地面上行走的时候,也不会忘记那个世界。
四
后来,在四川江津县那个叫白沙的古镇上,林再次遇见荻。那是一个募捐会现场。那个年代,为了筹措抗日物资,在大后方,经常会举办各种献金活动。那天,除了白沙当地政商界人士,一位美国军官,还有特意赶来的冯玉祥将军。
主席台上,冯玉祥穿着军装,个子很高,军帽下的脸显得大,或许只是虚胖吧。那是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西北军阀。谁也不曾想到,仅仅是四年之后,这位著名人物就不明不白地死在异国的轮船上。
乐鼓声伴着口号声,几乎响彻云霄。现场被一种间歇性的声音所笼罩,好在是露天的场地,逐渐变得热烈的众人的情绪,还没有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很快,他们就泪眼汪汪,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自己身上的所有财物。那些富商和阔太太甚至当场摘下金表、金项链和金戒指,扔进那个大盘子里。
一开始,林并没有将她认出来。她和那些学生在一起,站在台下使劲地鼓掌。他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她的那种表情,那种专注而茫然的神情。她脸上的悲伤似乎不见了,暂时被某种东西治愈了。
各校派出学生代表抬着盛满法币和金银的大盘子依次登上主席台,冯玉祥接过盘子,一次次地鞠躬,向每个学生道谢。
几天之后,荻来找他。他们去了省立师范学校,她工作的地方。学校位于马项垭。马项垭是个隐蔽的坡地,位于两座山的夹角。战时因聚集了不少人和物资,商贸活动颇为兴旺。织布厂、打米厂、染坊、屠宰场、杂货店、裁缝店、饭馆,小吃店等工厂与店铺,应有尽有。
那是春天,她陪他吃了一碗红油抄手。白瓷碗上漂着好几层麻油,很香。他几乎不能吃辣,吃得泪眼汪汪,可心里实在高兴。她告诉他,抗战爆发后,她就辗转来到内地,经人介绍到现在这所学校当地理教员。因日机频繁轰炸,不久前学校从重庆迁到白沙镇。战时物资短缺,没有什么可吃的。她总是喊饿,半夜饥肠辘辘地醒来,到处找吃的。她喝房东家自酿的白酒,喝醉过好几次。她学会了吃辣,实在没有菜就以辣椒下饭,有一种线椒过了油后,特别香,吃着简直有肉味。
随着荻的讲述,林的不安和扭捏消失了。荻的模样变了许多,比之前更瘦了。他知道战时的伙食不好,大家都在忍饥挨饿,可她兴致勃勃的,好像并不以此为苦。他想,一个人从故乡出走后,自会渐渐地与以往不同。他沉默地聆听着,脑海里,那些场景被一点点放大、拼贴成连续的画面。但那只是她所有生活的一部分。他还想知道更多关于她的生活,那种地面上的生活,那种平凡的日复一日,她是怎么度过的。他因为自身远离了那种生活,而对此充满好奇。
有一刻,他甚至遗忘了战争,忘记自己身上背负的使命,忘记云朵之下的国土上,大屠杀正在进行。这短暂的遗忘让他品尝到了孤独的滋味,比在天上的时候还要孤独。特别是在夜里,当端坐在那些仪表盘前,听着发动机发出的轰鸣声,他感到自己与这个世界正在失去联系。
镇西驴子溪的水,清可见底。他们终于走到那溪边,彼此都有些尴尬,好像是无路可走了。两岸山体碧绿,如友人相对。自然永恒地静止着,人世的杀戮和破坏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
几天之后,他接到紧急任务,去轰炸敌方某处重要的军事设施。他立即跑去学校找她,非要见她最后一面不可,强烈的意念促使他冒险离开队伍。他丧失了最后一点理智,宛如一匹烈性马驹,在通往马项垭的土路上横冲直撞,扬起的尘灰使得眼前一片模糊。
那座临时搭建的校园,处处显示出因陋就简的模样。她授课的那间屋子就像是座破落的宫殿,除了顶棚勉强可遮雨,其余四处漏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她的工作场景。她站在讲台前,双手捧着课本,以一种中等偏慢的语速向学生们描述每条河流的走向。当谈及那些亘古不变的山川之时,她的语速较先前变得更为缓慢而延宕。而那些或极端或温和的气候,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她的讲述下充满了命运的必然性。而当描述天上那变幻莫测的云系时,她的神情又洋溢着孩童的天真。
那块小黑板上,两行秀丽的字迹映入林的眼帘:
水始冰,地始冻。
风有信,花不误;岁岁如此,永不相负。
他反复默念着那几句话,好像那不仅是对自然世界真相的描述,还另有所指。那一刻,他的不安完全消失了。荻或许觉察到了他的到来,但并没有终止授课。
当重新回到天上,回到那个逼仄的机舱里,面对着仪器和罗盘,他又恢复了那种持久的专注。
生命的最后一刻,林想起一支歌,那支不能唱出的歌,在故乡的黑土地上被禁多年。——那一刻,终于从他嘴里哼唱而出。旧曲成调,好似某种召唤。
眼前浮现出采冰人的身影,荻站在那座宫殿一样的房子里授课,很快,这些身影都消失了。飞机在猝不及防的坠落中,去与死亡的丛林接壤!
五
胜利的消息还要晚一年才传来。
那年秋天,荻接到林牺牲的噩耗。随遗嘱一块儿寄来的还有那些信,厚厚一大摞,有完整的书写地点和日期,但没有称呼和署名。荻知道是写给她的,她知道得太晚了。荻夜以继日地读信。白沙镇黑暗的夜晚,烛光下的荻走进那个纸页般脆弱而窸窣作响的世界。在此之前,她并不知道那个世界的存在,当知道的时候,它已经被炸得粉碎,成了尘埃中的碎片。
她从来都不知道,一个人的肉身可以毁灭到这个地步,彻彻底底地消失,不留一点痕迹。那些天上的画面在荻的脑海里毫无意义地定格,她并不相信他们是去了那个世界。事实上,是那个世界摧毁了他们的肉身。
那些日子,荻除了给学生上课,便躲在屋子里读信。她变得面黄肌瘦,青春的光彩一去不复返。她对自己的容颜越来越不在意,认为那是所有消亡事物中最无意义的。
荻重新回忆了与林的最后几次见面。因为那些信件的出现,她感到自己可能错过了太多,但随着回忆的深入,她又变得模棱两可,或许林压根儿就没有要向她表白的意思,他只是在信里袒露了一切。她开始对他的爱充满怀疑。于是,她夜以继日地读那些信,却一无所获。
她只想让他亲口告诉她;只要他开口,她不仅允许,还将报之以热烈的回应,她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林也不应该有,既然生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失去!
白沙镇的夜晚一片漆黑,荻想起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他们还在江南的时候,她,Y,还有林,一起去郊外爬山的情景。
那是一座无名荒山。早春时节,山上不见砍柴人,也没有农夫的影子。山林里有一股奇异的清香,或许是那些树叶、泥土、蕨类植物散发出来的。一开始,他们三个齐整地走在上山的路上,都有些莫名的兴奋。
后来,荻被兰花的清香所吸引,往背阴的地方走去。Y正好想要一根枯树枝,但没有柴刀,或许守林人的小屋里有,他要找到那个地方。只有林显得不知所措。
他说,那我就在原地等着你们吧。
那天,荻没有寻到兰花,她只是闻着那些清香,却怎么也找不到它们。Y大概找到了守林人的小屋,取到了柴刀,但没有找到枯树枝。后来,荻感到自己走远了,想要返回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原路了。他们各自度过了在山上的时间,回去的时候都有些隐秘的兴奋,但谁都不愿提及。
后来,荻常常想,如果没有战争,他们或许不会走到一起。在战争中,人们可以很快地爱上一个人,然后抛弃她,是命运让他们这么做,他们别无选择!
当胜利的消息传来,荻正处于高烧之中。整个白沙镇被喜庆的声音淹没,那些声音的涡流震得窗户纸嗡嗡作响。房东一家都跑到街上去了,连两岁的孩子也带出门去了。荻打开收音机,那里面也人声鼎沸,所有人都在唱歌或跳舞。
荻走出门,来到大街上。天黑了,广场上到处都是游行的人群,到处都是火把。有人认出了她,将她拖进他们的队伍中。那些将被子点成火把的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路上,不断有新的火把被点燃,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空。所有人都在大声说话或疾呼,但没有人听得见对方在说什么。
荻感到自己如在梦中,并明显地感到这个梦随时可能结束,而胜利的消息也极有可能是假的。她紧跟着狂欢的人群,随着他们嘶吼、歌唱、哭泣。他们使劲地摇晃着彼此的身体,或者干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又是啼哭又是狂叫。有人喝醉了,将脱下的衣服绑在木棍上点燃。瞬间,火苗从木头上绽放出来。身旁的人不顾一切地去捕捉那火焰,想把它永久地握在自己的掌心里。
没有人抬头看那天空;在狂欢的人群的头顶上,夜空就像一个巨大而虚无的伤口,沉默无声地打量着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荻被人群推搡,滚烫的身体像一截马上就要被点燃的木棍。她行走着,忍受着灼热与酸痛。她瘫倒在地上,那些泪水从眼角处滑落,几乎灼伤了她。她躺了很久,Y和林都没有出现。她忽然意识到眼下发生的一切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胜利的消息持续了太久,丝毫没有被打破的迹象。
——这一回,荻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并不在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