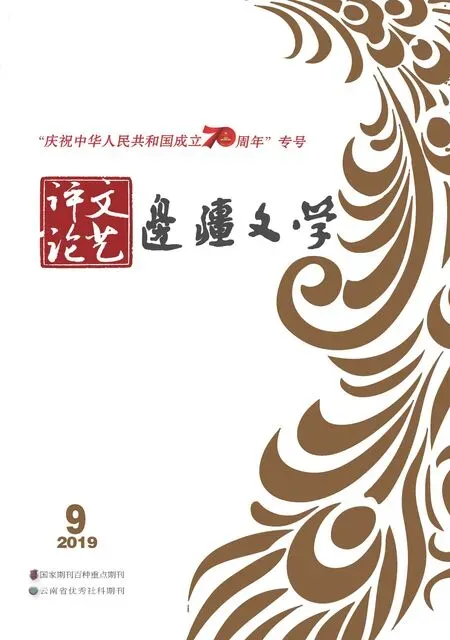穿越时光长河的丽江文脉
——丽江文学建国70年脉络梳理
·和晓梅
丽山水清淑,人士英敏,必将有握珠抱玉,崛起于雪山玉水之间者。
——管学宣《下车课士说》
云南多样化和立体化的地理结构导致文学和水土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山川、河流、土壤、植被、甚至空气,都是文学衍生的基础。基于此,云南文学在建国70年来,逐渐形成地域特征显著的文学版块,形成成绩卓著的作家群体,共同组建出云南文学绚丽多彩的画卷。在这些值得称道的版块中,丽江文学因为具备传统性和民族性备受关注。
在丽江,文学的存在,类似于一棵安静生长的树。
滇西北海拔超过2400米的高原地带,植物的生长通常都是安静而缓慢的,丽江文学,如果她是一棵树的话,在过去的时光里并不拥有最适合生长的生态条件,偏僻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经济态势、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就像干燥和低温对植物的制约一样,制约着文学的发展。但是,正因如此,植物会在环境的逼迫下生长出发达的根系,抓紧土地,在土壤更深处寻找水分和营养。文学亦如此,这种发源于母族、在文字的指引下实现内心表达的方式,在1000年前就成为丽江人笼罩在世俗烟火下的精神欲念,深深地根植于滇西北错落而贫瘠的泥土里,倔强地生长发育。
往上追溯,丽江有文字记载的纳西族作家文学出现在东汉明帝时(公元74年),《白兰歌》三章(又名《白狼王歌》);这之后很久,明代木氏土司进入极盛时期,在他们励精图治、效学中原的倡导下,木氏作家们诗文造诣日趋升华,和中原文人杨升庵、钱牧斋、杨慎等唱酬应和,作品也“得传中土,受到时人好评”;到了清代,木氏土司走向没落,丽江旁姓作家逐渐接力文学的传递,比如杨竹庐、杨昌、桑映斗、牛焘、木正源、妙明等崭露头角,他们突破木氏土司文学贵族化的阶级局限,开始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关注人民生活、展示人物命运。
此时,丽江文学已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根基,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与主流文学努力靠近,与时代风尚紧密相连。
今天,当我们梳理丽江文学建国70年来发展脉络的时候,就会发现丽江文学的发展来自于传统根基,是有根的文学,是在时光的变迁、历史的风雨反复洗礼中延续,并且依然保持着风骨的文学。
一
(1949~1966)在新中国的曙光里,丽江文学开启民族觉醒的征程。
20世纪40年代初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丽江,并没有避开战争和动荡的阴霾。在席卷全国的民主思潮影响下,在如火如荼的抗日烈焰激荡下,一批丽江青年作家迅速成长,他们在黑暗中蜗行摸索,以文字为武器,以思想为后盾,战斗在边地民族地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最前沿,用无比激越的情怀,率先迎接到新中国的曙光。这批青年作家的代表是:李寒谷、和柳、赵银棠、杨琦、周霖、范义田等。
这是一批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文学新人,他们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具备坚实的国学基础,也有个别出生贫困家庭但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良好的教育,他们勇敢地走出故乡,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影响下学习科学、探索真理。这时候,文学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
生活面的扩大、视野的改变带来思想的升华,他们创作的题材更为广泛:有取材于农村生活的乡土文学(如李寒谷的小说);取材于市民生活的城镇文学(如和柳的小说《菊生小姐的命运》);也有反映学校生活和异国风光非虚构作品(如杨超然的《海外通讯》《在印度》等);更多的是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诗篇。创作的体裁也转向更多的领域:小说、新诗、散文诗、评论、戏剧均有涉及。此外,各类与丽江文学有关的文艺刊物也为培养民族作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云南最早的白话报诞生于丽江, 1907年创办的《丽江白话报》,由此可以窥见丽江文学在上世纪初期储备着极为丰厚的力量,走在时代前沿。1932年,范义田、王应岐、宣伯超在昆明创办《南荒》,1937年李寒谷在昆明创办《文艺季刊》,其中刊登了许多丽江作家的作品。此外,一些综合性刊物,如在昆明创办的《丽江旅省学会会刊》,在丽江创办出版的《大众壁报》《丽江周报》等,更是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充分展示丽江文学在传承文化、弘扬五四精神、宣传实业救国中取得的成绩。
新中国的建立给这批经历民族民主革命大时代的丽江作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和期盼,他们满怀激情,带着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全部憧憬投入创作,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变迁、人民生活的佳作。李寒谷的小说《狮子山》《三仙沽之秋》《三月街》《劫》等,在深切同情受苦受难的农民,热情讴歌年轻一代农民反抗精神的同时,严厉抨击了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和柳的诗歌,保持着战斗的激情,小说则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尤其是反映市民家庭纳西女性生活和命运的作品,揭示了中国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桎梏。赵银棠新中国建国后发表的文章一是搜集整理后的东巴文学,另外一类是散文、诗歌和杂感,作为云南最早从事作家写作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她的作品《新时代给我的鼓舞》《亲切的墨迹,难忘的教诲》《感怀》以女性视角展现对新时代和新生活的感悟,语言带着浓郁的“民国腔调”,古雅而鲜活,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云南早期觉醒的女作家,在文辞和思想上、女性意识的强化上,都有着不输于内地女作家的实力。
杨琦是一个被云南文坛忽略的纳西族诗人,早在1935年就在《云南民国日报》副刊发表新诗,后接受地下党委任的文艺工作组组长职务,辗转到沈阳、重庆、南京等地从事文艺工作。在南京和丁力、刘力理等著名诗人共同创办《诗行列》,同时还为南京《中国日报》主编《文学新丛》,为重庆《国民公报》主编《文学新叶》,他个人的作品,更是因时代风云的映照和人格力量的呈现,频频在上海《大公报》、重庆《新蜀报》、武汉《新湖北日报》等刊物上亮相。新中国建国后调回北京中国音乐家协会,在从事音乐专业研究同时,创作大量新诗。
风云急涌的时代造就了迎风歌唱的作家诗人,在新中国的曙光里,无论是走出丽江来到广阔天地的文人,还是驻守故土辛勤耕耘的本土作家,都秉承丽江文学崇尚汉学兼顾民族情怀的传统,创作与时代脉搏交相辉映的作品。然而,随着“左倾”思想的出现、“文化大革命”爆发,社会动荡严重伤害了丽江作家的创作热情,一时间,除了民间文学尚能勉强维持发展以外,丽江文学沉寂在风雨飘摇中。
二
(1978~1990)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丽江文学跨过断裂地带,重续中断的脉络。
对于一个小地方文学而言,长时间的沉默有可能带来文化断裂的危险,然而,民间文学的存在,挽救了丽江文学,使之及时避开风险,沿着文脉固有的方向,逐渐苏醒、发展并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春天的气息刚刚吹拂过滇西北广袤的土地,丽江作家,立即开始倾泻他们蓄积太久的创作激情。
木丽春、牛相奎是新中国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纳西族本土作家,对民间文学有深入的了解,早在1956年就以长诗《玉龙第三国》步入文坛,此后,又以长诗《丛蕊刘偶和天上的公主》以及在《人民日报》《诗刊》《红岩》《边疆文艺》发表的诸多短诗、散文稳固了在云南文坛的地位。“文革”期间,他们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保护工作,这也使他们掌握有大量的素材,在后期创作中带上民间文学的烙印。当然,这也是云南甚至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流派众多,频繁更迭,影响巨大。那些衍生于民间文化和历史文化的作家写作,虽不能引起强烈反响,但是经久不衰。
牛相奎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发表长诗《云妹》,短诗《奴隶的女儿》《小独玛》等,其中短诗《小独玛》获云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此外,与李即善合作整理发表的长诗《牧象姑娘》、与赵敬修合作整理的纳西族著名长诗《鲁般鲁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木丽春则在继续民间文学工作的同时转向小说创作,相继在省级刊物发表《铁核桃》《雪山磐石》《没有开盖的合心酒》《山外的声音》《失落的山魂》等短篇小说和《最后一座水磨房》《骑龙的人》等中篇小说。其中《铁核桃》获云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戈阿干、杨世光是在昆工作的纳西族作家,虽然离开故土,但他们的创作依然深深根植在民族文化的沃土里。戈阿干还在中学读书时就开始翻译纳西族民歌,在《北京文艺》《边疆文艺》上发表,1978年以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根据东巴神话诗再创作的《格拉茨姆》《查热丽恩》两部长诗、情歌集《玉龙山情歌》、东巴文学集成卷《祭天古歌》、发表30多部中短篇小说,其中长诗《格拉茨姆》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短篇小说《化雪图》《七星锁》分获云南省第一、二届文学创作奖,《天女湖畔》获云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杨世光同样多次获得奖项,成为丽江走出的杰出作家代表。1978年以来的10余年光阴里,他先后在全国30余种报刊上发表散文150余篇,其中《玉龙春色》《夜石林》连获第一、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前身),《泸沽湖,晶莹的金杯》获云南省文学创作优秀奖,《虫草奇迹》《失落的色彩》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他和他的散文,作为当代一家,选入《中国散文百家谭》中。
丽江一批世居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也异常活跃:摩梭作家拉木·嘎土萨的散文《泸沽湖我的故乡》、散文集《母亲湖》,普米族作家何顺明的短诗《啊,泸沽湖》,殷海涛的诗作《女人》,彝族作家吉霍旺甲的小说《山里的女人》均获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此期,丽江出现了一个奇人作家王丕震。在经历了24年右派牢狱生活之后,积淀了半个世纪的创作热情如同火山般喷发,他用18年时间、平均每45天一部的速度完成142部历史小说创作,涉及自虞舜到近现代秋瑾、蔡锷等百余位重要历史人物。他和他的写作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传奇,是丽江作家在写作领域另辟蹊径的尝试。从这个意义出发,丽江文脉在王丕震披肝沥胆的写作中,无论是宽度还是纵深度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延展。
一个偏远且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文学能够形成自身的脉纹持续行进,除了作家个人的努力以外,还跟社会风尚密切关联。在80年代,大量文学社团和刊物的出现,为丽江营造出一派天雨流芳的崇文氛围。首先是公开刊物《玉龙山》创办,这本诞生于改革开放号角声中的杂志成为无数丽江作家扬帆起航的起点,除了上述提到的作家以外,白庚胜、杨福全、和国才、海男、李世明、沙蠡、马霁鸿、鲁若迪基、人狼格、蔡晓龄等一批在云南文坛可圈可点的学者诗人小说家均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并逐渐走出丽江,为云南文坛乃至中国文坛认知。
此外,活跃在各个领域的40多家民间文学社团一度点燃了人们创作的火焰,其中永胜县的“星巷诗社”“三川文学社”“东风文学社”,丽江地区师范学校的“象山人文学社”、地区财贸学校的“小草文学社”、教育学院的“突破文学社”、丽江古城的“玉泉诗社”最为有名,坚持时间也最为持久。有些由文学社筹资印刷的内部刊物,一直创办至今。比如《东风杂志》,曾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几欲停刊,但是一批坚韧的文学工作者为她保留了微弱的火星。今天,这份杂志有固定的办刊经费,固定的写作群和读者群,持续传递着大山深处绵延不绝的文学精神。
三
(1990~2010)繁花似锦的世纪之交,丽江文脉向着重塑文化方向及重塑人格本质方面持续向前。
通常情况下,1996年“2·3”大地震被认为是丽江的转折点,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震动打破了丽江长久以来的格局,经济、社会、思想方面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开放是这个时期最大的特性。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化方向的重塑和人格本质的重塑。丽江文脉的发展,一直没有离开过民族文化的滋养,这个支系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依然占据一定位置,但是,随着思想的进一步开放,更加接近主流文学和大众文学成为丽江作家努力的方向。许多民族作家用更多的时间思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挖掘上。
于是,一些适度脱离民族文化甚至彻底决裂的文学作品诞生。但无论是脱离还是决裂,就文脉的发展而言,都不是一个反方向的前进,而是一次传统文化根基上的提升和扩展。这是一个宝贵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丽江文学出现了一批佳作,也收获了许多奖项,呈现一种群体性发展的态势。
纳西族著名学者白庚胜出版的文艺论著先后11次在全国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评奖中获奖,被中国文联授予全国优秀青年文艺家称号。摩梭作家拉木·嘎土萨获1994年庄重文文学奖。纳西族小说家沙蠡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首届云南边防军事文学奖等奖项。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获第五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诗人提名奖,《人民文学》年度优秀诗歌奖等奖项。纳西族军旅作家和国才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纳西族随笔作家白郎作品获第六届北京图书节十大畅销书,第25届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彝族作家木祥获《大家》文学奖。普米族青年诗人曹翔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显然,这是一份并未统计齐全的获奖名录,是一支由纳西族、彝族和普米族等少数民族作家构建的获奖队伍。奖项的获得不是评判文学发展与繁荣的唯一标准,但一定是文学活跃程度的指向标,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丽江这块面积并不大人口也不多的土地上,拥有这样一支获奖队伍,可见文学占比是个可观的数值。
在获奖队伍中,最闪光的是从永胜县走出的女性先锋作家海男,她以执着坚持的先锋意识在中国文坛开辟出女性写作的广阔天地,那些抵达灵魂秘境的文字深受读者喜爱。作品先后获1996年刘丽安诗歌奖,中国新时期十大女诗人殊荣奖,《诗歌报》年度诗人奖,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等重大奖项。
在这之外,马霁鸿、陈洪金、严谅、胡继惠、胡延平、赵晓梅、杨宝琼等永胜籍作家;马海、刘芝英、何顺学、杨世祥等华坪籍作家;阿卓务林、李永天、李黑、黑羊、任尚荣、吉春、华秀明、周宗寿等宁蒗籍作家;人狼格、蔡晓龄、和克纯、周文英、和凤琼、祁萍等丽江籍纳西族作家,这些以更小范围区域文化为核心凝聚而成的文学创作群体,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丽江文学的界域。这当中,人狼格、陈洪金、马海是杰出的代表,他们的创作部分受到现代文学的影响,在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都有着比以往的创作更为成熟的思考,比如人狼格的诗,在逐渐被同化和消解的文明中汲取力量,使它们积淀成历史,演变成现实,融入当下。
紧接着,小凉山诗群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辨识度,得到云南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关注。鲁若迪基和阿卓务林是小凉山诗群的引领者,他们的诗犹如天地山川所孕育,在莽荒之中书写另类的人生体验,自然性与神性的结合带来一种别开生面甚至意料之外的表述,令人惊喜。鲁若迪基《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阿卓务林《耳朵里的天堂》是此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建立在与土地亲密的血缘关系上向内反思人格的诗作,这批作品把小凉山诗群的整体实力提升到一定高度。其他的诗人,如阿克·雾宁石根、曹翔、佳斯阳春、沙马永生,吉克木嘎,杨洪林等也以他们各具特色的诗作,丰富和扩大了小凉山诗群的影响力。
另外一个群体是丽江女性作家群体。过去,对此没有进行系统的关联和研究,但今天我们梳理云南女性作家的时候,会发现,丽江也许是云南最能产生女性作者的地方,这或许跟丽江女性在极早的时候,就通过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争取到相对平等的教育权有关。也或许仅仅是因为这片土地,适合女作家的生长和走出。
赵银棠是在妇女普遍不识字的社会状况下脱颖而出、最早从事作家写作和文学活动的少数民族女性,海男以其瑰丽的文字和尖锐的女性思考把女性文学推到高远的天空,蔡晓龄的创作驻守着学院派的清冷与平静,赵晓梅的诗着意于人间烟火爱恨交加……如今,就职于中山大学的冯娜、坚守在丽江的李凤,作品频频在国内一线刊物发表,成为丽江文学80后最强有力的支柱。
在这个世纪交替的时期,丽江文学呈现出多元格局,但其中最核心的主题就是文化重塑与人格重塑,丽江文学突破了文化界域的限制,朝着更有现代意义和更具备历史价值的方向缓缓发展。
四
(2010~)21世纪,丽江文脉的接力者和发扬者任重道远。
时光进入21世纪第10个年头。在这接近10年的时光里,丽江文学依然保持着锐意的实力:海男夺取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桂冠,冯娜获华文青年诗人奖、美国Pushcart Prize提名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奖项,鲁若迪基获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第十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二等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和晓梅获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九届湄公河文学奖,阿卓务林作品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之星”,陈洪金获陕西省散文学会首届散文奖。此外,在云南省文艺创作基金奖、云南省文化精品工程奖、云南作协年度优秀作品扶持奖中,丽江作家均有入选。
这个时期,海男《忧伤的黑麋鹿》,鲁若迪基《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一个普米人的心经》,人狼格《锋芒》,陈洪金《村庄记》,蔡晓玲《公民宣科》,阿卓务林《凉山雪》,木祥《红灯记外传》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同时,一批80后青年作家也渐渐进入人们视野:李凤、黄立康、尹晓燕、吉克木嘎、东巴夫、李志文、周杰、杨璇、戈戎纰措、今古阿嘎、杨彦川、和传妤、曹媛、和利莹、拉姆周雯等。这是一份足以带来希望的名单,从年龄、性别、民族构架来看,都趋于合理,丽江文脉有了新的接力者和发扬者。
然而,不容忽略的是就丽江文学而言,恰恰面临一个艰难的时期,新的挑战和难题日益凸显:文学,被铺天盖地的旅游业覆盖,逐渐被主流边缘化。
是的,从古到今,文学都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战斗,孤独而落寞。但是,过去,这场一个人的战斗是有可能打赢的,只要你有一定的天赋又足够努力。今天,没有群体性的氛围和良好的政策引导,文学会瞬间消失在无比庞大的、各种类型的关注点里。在丽江,这些关注点来得异常猛烈。
所以说,2010年以后,丽江青年作家,尤其是居住在丽江本土的这一部分青年作家,虽有成绩优异的佼佼者,但屈指可数,大部分青年作家只能在当地产生影响,无法进入更高层面。这里面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政策原因和个人原因。
丽江古城以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吸引大量游客来此放空,一个总是过多宣扬享乐主义和逃避主义的城市,有可能消解年轻人的工作动力,带来负面的懈怠和松漫;另外,在丽江普遍存在的重出版轻发表的导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也严重影响青年作家走出去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个人的文学追求和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像一条巨大的沟壑横亘在青年作家的面前。如今的丽江充满商机也充满诱惑,除去网络文学以外,传统文学带来的物质回报可谓微薄,何去何从,他们的坚守变得困难。
其实,新中国建国70年来,丽江文学的发展虽然脉纹清晰、延续稳健,却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机遇永远跟挑战并存,问题永远在奋斗中和解。当我们看到一棵树的年轮,某些斑驳的向四周漫溢的纹路,最终又向着核心的部分绕行聚拢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不仅仅是时光的力量,也不仅仅是阳光、雨露,而是一种精神向度使然。文学就是这种精神向度,任何时代都有人为之负重前行。这就是丽江文脉经历漫长岁月发展至今的原因。
正如乾隆元年(1736年)丽江第五任知府管学宣在《下车课士说》中所期待的那样,“丽山水清淑,人士英敏,必将有握珠抱玉,崛起于雪山玉水之间者。”我们期待丽江青年作者,在21世纪接力文脉的传承与发扬,无畏风雨,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