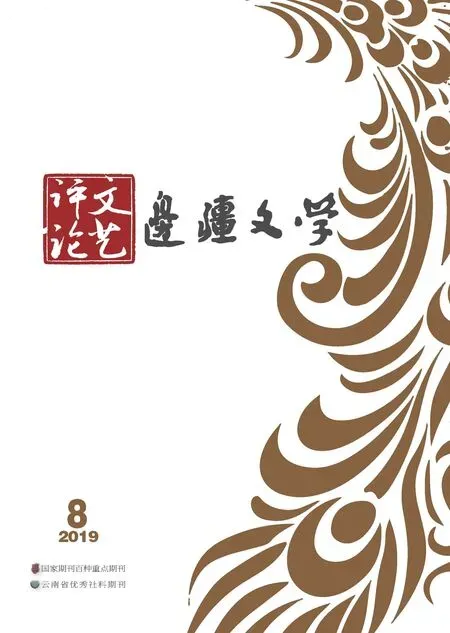影视剧中癌症的隐喻及其变迁
…………………………………………………………………·欧阳炽玉
(作者系北京大学在读硕士)
1
随着人们对癌症的印象的转变和对癌症认知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癌症种类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对癌症这个庞大家族的了解本来是整体的,现在变成了局部的细节的。这种变化带来的效果是,原本癌症整体的隐喻变得支离破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癌症家族成员拥有了各自的隐喻,他们区别于彼此又互相联系,就像一朵玫瑰的每一片花瓣,同苞相似却不尽相同。一些癌症发病率较低,或是在公众眼中没有显著性特征,则没有形成隐喻。其中,白血病是一种被广泛知晓,且具有强势的隐喻的成员。白血病隐喻的兴起和大众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在新媒介还未生成或是流行起来之前,其隐喻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在日本1976电视剧《血疑》中,女主角是个白血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与男主角相识,二者发生恋情。但是在当时,这样的设定并不多见。白血病元素真正流行起来,是在韩国电视剧之中。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连续出现多部包含白血病元素的韩国电视剧,1998年的《我怕恋爱》,2000年的《蓝色生死恋》,2001年的《美丽的日子》等。在这些作品中,白血病作为一种升华灵魂或是升华的情感的角色存在,也作为渲染悲剧色彩的道具。比如,《蓝色生死恋》中女主角恩熙通过患白血病,找到了人生的答案,放下了情感纠葛安心赴死,并且与多名角色的感情都有所增加。最终她的离去更是将故事的催泪程度升到最高点。
当一个人患上某种死亡率极高的病症时,她与病魔的抗争,自然会将她的人格升华,而她与周围人的互动,亲近之人对这场疾病的反应也能体现出他们之间的情感,让他们更加紧密。
那么这些编剧为何不约而同地选择白血病呢?首先,相比其他癌症,白血病更易袭击30岁以下的人群,而这些电视剧多为爱情偶像剧,主角最多不超过30岁,所以他们患上白血病似乎更加有说服力,更加实际。其次,白血病患病后最明显的表现是贫血,出血和发热,这些现象比较好表演,也容易演出美感,脸色苍白,吐血和发烧相比而其他癌症患病的现象,如腹部积水,呕吐等,后者不仅对化妆技术和演员的要求较高,且美感较低。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白血病患者被塑造出来的一种虚假的不切实际的美——一个美人,脸色苍白,虚弱得不行,并且时不时吐几口血,当然,这肯定不是白血病患者实际的样子,但是这种美态,无疑迎合了病态美的审美,也是新时代病态美的体现——瘦骨嶙峋的美丽女人。心脏病也有着类似的作用,不会吐血,但是却会捂着心脏喘息。
再次,白血病这种疾病的病因,已经确认的有这些:病毒,化学污染,放射污染和遗传,这些成因全部是外部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受害者做了什么,所以他才得了这样的疾病,而是因为他很倒霉,所以白血病患者是全然无辜的存在,这种完美受害者模型,更能被观众喜欢和认同。与之相对比的是肺癌和宫颈癌,大部分观众看到这两种一定会联想到吸烟与乱交,从而厌恶主角或是觉得剧本写得很容易让人出戏,总之无法对角色产生足够的同情。
最后,白血病是一种家喻户晓的高发癌症,在CA杂志发布的2018年各类癌症发病率中,白血病排名第十五位。在白血病的知名度的基础上构建隐喻,比从科普开始构建另一种疾病的隐喻要简单许多。因此,白血病就这样被各国影视所选择作为一种工具了。
比如改编于小说的电影《姐姐的守护者》,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小女孩为了给姐姐提供器官和血液被父母生出来,而这个孩子的姐姐就是一名白血病患者。在这部电影里,白血病的隐喻被扩张了,除了是升华,悲剧和斗争,它还代表着新生。这样的隐喻基于白血病的特殊治疗方式,骨髓移植。相对其他器官移植,骨髓移植更加容易。一方面,骨髓捐赠对捐赠者的伤害更小,因此捐赠者较多。另一方面,骨髓移植排异性相对较小,骨髓移植生存率较高,其成功率普遍认为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在骨髓移植五年之后,白血病未复发在临床医学上就可以算是痊愈了。正是因为有着骨髓移植这种特殊疗法的存在,所以白血病患者有着一个从死亡到新生的完整过程,将人与自身的抗争这一主题展现到极致。这种过程带来的美感是不可估量的,哪怕不是所有白血病患者都需要骨髓移植。《姐姐的守护者》这部电影中姐姐靠着妹妹的血液和骨髓延续着生命,获得了新生。
但是这部电影的结局是姐姐出现了排异反应肾衰竭,最后又移植了妹妹的肾脏,代价是妹妹的死亡。因此,原本的自我斗争在这一刻变成了“我”对“他人”的剥夺,一命换一命。妹妹的死去和姐姐的活着,没有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快乐与幸福,也没能让姐姐获得新生,甚至让姐姐的精神一直活在痛苦之中。这种幻灭感,便是白血病的另一种隐喻。骨髓移植原本应该带来新生,可是因无法确定的原因,仅是概率性地失败了,所以一切都幻灭了。除此之外,因移植失败带来的器官衰竭也是造成幻灭感的原因,首先,主要器官来源艰难,很难活着等到,并且就算等到,除了骨髓移植以外的移植,几乎都是以一换一,哪怕不危害捐赠者的生命,也会对捐赠者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这种伤害,意味着捐赠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移植变为对他人的掠夺。所以,白血病的治疗中,带来的这种新生和幻灭感交织的隐喻的强烈程度,是其他癌症无法比拟的,巨大的成功率对应的是失败后的绝望。
其他的癌症,也有着类似的隐喻。那些存活率极低的癌症,比如患癌五年存活率仅有百分之10的肝癌和百分之12的胰腺癌,意味着从始至终的绝望。那些有一定治愈率,却需要切除什么的癌症,比如乳腺癌和睾丸癌,意味着失去和破碎。那些需要剥夺别人的才能活下去的疾病,不单单只是癌症,则意味着融合,并存,再生,如果失败了则意味着幻灭,分隔和距离。
白血病的另一种隐喻是关于同情。正如之前所说,很多影视作品将白血病作为一种引起人同情的工具,这种同情很复杂,有的是因白血病高发而产生的一种共感,有的是对美丽的角色凋零的遗憾,是一种天妒红颜或英才的恨意,最后还有一种,非常特殊,与急性白血病的高发人群有关——百分之三十五是15岁以下的孩童。人类对于幼童的特殊的天然的爱意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打开轻松筹,就可以看到许多白血病患儿在募捐。这三种同情交织在一起,赋予了白血病新的隐喻,无辜,可怜,需要关爱与金钱。在美国电视剧《绝望主妇》里,女主角斯加沃太太,通过将自己的儿子伪装成白血病患儿,以获得各种礼遇和优先权。正是由于同情被发挥到极致,白血病在这里变成一种获得特权和优先权的方式。正如电视剧中的情节,这种同情经常会被利用,正如近几年频发的诈捐事件,其中引起巨大争议的“罗一笑事件”就是父亲以无力支持医疗费为由为身患白血病的女儿募集大量捐款,最后被发现其实女儿的医疗费几乎可以报销,并且家境优渥那些少得可怜的自费部分根本不存在无力支付。由此可见这种隐喻的强大。
2
癌症的整体性隐喻随着癌症被认知得越来越细致,而变得不清晰。可是仍然具有整体性隐喻,比如是勇气。这个隐喻在那些存活率极低的癌症里体现得更明显。
科幻小说《湮灭》中的探索小队队长文崔斯博士正是由于身患癌症,才能在明知必死的情况下进入恐怖未知区域,为人类冒险寻求真相。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中身患癌症的康斯坦斯为了实现自己废除死刑的理想,自杀然后伪装为谋杀案使他人被判死刑,以来揭示死刑的不人道。如果电影里有什么人做出了常人无法理解的不符合逻辑的大胆行为,只要把他设定为癌症患者,那么一切都变得合理了。无望治愈的癌症,使患者得到勇气——与未知抗争的勇气,与世界抗争的勇气。一无所有的人总是比拥有太多的人勇敢。而癌症群体,则是失去了太多的,几乎一无所有的人,连生命也是转瞬即逝的,他们还拥有什么呢?所以他们拥有去打破那些其他人因为害怕失去而不敢打破的东西的勇气。
这种隐喻变得明晰,而使身患绝症的角色很容易做出一些超越常规的事情,也易于通过自我牺牲来达成一个远大目标,这种自我牺牲的情况下,他们肉体覆灭,可是精神却变成丰碑,被永远刻印在结尾。自我牺牲,是从勇气衍生出的新隐喻。在纪录片《人间世》的第九集《爱》中,体现了这一形式。癌症母亲牺牲了原本应该争分夺秒的检查和治疗时间来生下自己的孩子,最终没有奇迹发生,癌症母亲依旧去世了,可是她的自我牺牲却感动着每一个知道她故事的人。
由晚期癌症而引入了一些新的名词,止痛药,自杀和抢救。癌症晚期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痛苦和止痛药耐受。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常常让人真的选择去死。不过很多癌症病人甚至没有自杀的能力,只能被动等待死亡的到来,有的人希望多活一秒也好,有的人则希望快一秒死去,但是他们都会被一视同仁地接受抢救。痛苦与道德伦理交织,形成一张巨网,将癌症患者紧紧缠住,甚至让他们呼吸都困难。这种情况,展现了癌症的另一层含义,选择。上面讲述的是最可怕的情况,就是因为痛苦而需要选择放弃或是不放弃生命。但是即使还有得救,癌症也意味着需要放弃很多东西,从患上癌症的那一刻起,患者的生命中就充满着左生右死二选一的选择题。例如金钱方面,是否要放弃金钱,而选择烧钱拖命(主要针对没有有效治疗方式或复发率高的癌症)。例如切割,是否要放弃身体的一部分来换取一线生机,并且要做好以后还需要放弃更多部分的准备。再例如时间,是否要舍弃短时间高质量的生活,来换取长时间低质量的生活,可以舒舒服服短暂得活几个月,然后虚弱下来迅速死去,还是在呕吐,脱发的痛苦治疗中度过几年。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也许后悔了,也许死而无憾,但是只要一提起癌症,那么所有人下意识就会开始做这些选择题,癌症意味着选择。
但是,现今的癌症,也有着负面的隐喻。这个隐喻与其遗传性有关。癌症的传染性早被证实是不存在的,并且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其隐喻性质改变的一部分原因。
但是癌症的遗传性,则让传染这个话题重回到它身上。遗传被证实是许多癌症的病因,这给癌症画了个圈,让他在这个圈里传播,圈外的人似乎是绝对安全的,哪怕有其他患上癌症的原因,但是避免了这个原因,就给人一种似乎可以逃过一劫的错觉。既然有一个圈的存在,那么圈外人会自然规避进入圈内。这表现在有癌症家族史的人在亲密关系上的挫败。一种比普通人概率更高发生的恐惧,笼罩着他们和他们的伴侣。是否会如他的亲属一般患上癌症,影响着他们和伴侣的生活质量,共同财产和后代。在这里,癌症不再被惧怕传染给某个人了,被害怕的是癌症患病后带来的效果,这是一种生活中埋着隐藏的炸弹的可怕。这种复杂的情绪和癌症的其他隐喻是并行的,人们对陌生癌症患者依然友好而同情,但是对于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癌症患者却增添了恐惧。
除了圈形感染以外,癌症还有一种一种传染方式——地域性传染。在地域性的传染中,被污染的那块土地具有传染性,会传染每一个踏上它的人。比如众多癌症村,发生过核泄漏的福岛和切尔诺贝利,被投放过原子弹的广岛和长崎,谁在这些土地上,谁就会面临失去。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疾病里,被人畏惧的是其他人身上所携带的病毒。在这种情况里,被畏惧的则是那片土地上的脏污。传染源从活物变成了死物,由死物传染给活物。但是这样定向传染的方式,则反而能让人安心,产生一种不在那片土地上就不会有事的错觉。但是,传染源蔓延的恐惧却还是存在的。《湮灭》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将小说中那个“透明气泡的区域”视为会让人身患绝症的被污染的土地,那么那个一直在蔓延的气泡边界就是土地被污染的边界。正如电影里的气泡区域在不断扩大,现代工业发展以来,被污染的地域也在不断增加。由癌症引出的环保话题,也给癌症带来了新的隐喻。许多疾病都可以引申出环保这个话题,与之不同的是,癌症是其中较为神秘的一种,大部分的这些被污染的土地,为什么会让人患上癌症,都只能找寻到间接原因而非直接原因,例如河南省沈丘县黄孟营村,癌症高发的原因是因为水污染,至于究竟水里的什么东西使人患癌,说不清。这种神秘性所达成的效果是——整体性。如果找不到具体原因,那就只有解决全部的问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污染物使人患癌,那就只有提倡去解决所有的污染物了。
3
癌症,这一除了代指一类疾病的集合以外还有着复杂的代表意义的名词,其隐喻在今日依旧被广泛运用,只是相比上一世纪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要从癌症的治疗和病因开始说起。正如曾经的结核病,癌症原本被认为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绝症,这种病症不但患病原因不明,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式抑或是治疗后没有有效的抑制复发的方式,并且具有延展性,会从身体的一个地方延展到另一个地方,使人体发生恶心的变异。因此,癌症具有极强的神秘感,激发了人们关于癌症的恐惧与不公正的幻想。可是在这一世纪,癌症的病因,被广泛科普,比如持续感染HPV会导致宫颈癌,乳腺癌的遗传因素等等,随着这些发现被广而告之,其预防方法也被广泛运用,如注射HPV疫苗,或是切除乳腺等。这些发现与预防手段虽未完全将癌症的神秘面纱拂去,可是也将这种被过度修饰了的疾病变得没有那么神秘。当一种神秘的,带有天罚性质的疾病,被从神坛上扯下来之时,人们对其看法也就理智得多,因为一种具有确定性的疾病,不再能够承担上帝之锤或是灭世之音的角色,人们对其看法乐观起来,逐渐开始相信,癌症正如以往被人类医学征服的狂犬病,结核病和梅毒等绝症一样,总有一日也会被治愈。“未来××年,癌症将被治愈”被一些不严谨的媒体杂志作为一种吸引人目光的手段,做为一些关于癌症研究新发现报道的题目。虽然这种预言不一定能成真,但是这样的态度无疑象征着人们对癌症的接受度的提升。
由于癌症是一种变异与增生的疾病,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长出一个本不存在的丑陋的东西,因此大部分人对于癌症治疗的了解停留在两个词上“放化疗”与“切除”。
首先是放化疗一词,大多数人对于放疗和化疗的具体操作和原理并不熟悉,对其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其副作用,即脱发与疲惫的肌身。所以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癌症病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早期病人或是放弃治疗的病人,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是会着重表现他们心态与常人之不同,渲染悲情气氛。另一种是接受治疗的病人,多是躺在病床上或是瘫坐在轮椅上,带着帽子,帽子下没有头发,穿着病号服,看起来毫无尊严并且没有辨识度,看到这身装扮人们几乎已经不在乎这个角色的其他特质,而仅仅记得他是癌症群体中的一人。这样的场景,能够引起观众的同情,恰恰也说明了人们对于癌症的态度不再是羞于启齿,而是同情与怜悯。但是,虽然人们对其看法有所改变,但是还是将癌症病人符号化和群体化了。癌症病人就是这样的群体——光着头,绝望虚弱的,即将死亡的。虽然癌症的隐喻有所变化,但是癌症群体被孤立被另眼看待的情况并未结束。
人们对于癌症的另一种治疗方式“切除”,是持着乐观态度的。癌症被认为是一种侵略性的,外来的,变异的疾病。其中变异是最令人恐惧的,正如人们对于会让人变得像狗的狂犬病的畏惧。即使在狂犬病有了疫苗的今日,这个名词依旧令人闻风丧胆,比如恐怖电影《惊变28天》,里面的丧尸的形态与狂犬病患者十分类似,他们行动迅速,野蛮,渴望撕咬,他们被感染的疾病被认为是狂犬病的升级版本。人们对于变异的恐惧,正是因为对于人类身份的认同,和对异类的排斥。变异的人类,就不再是群体中的一员了,这个观点隐藏在人群内心深处。身患癌症的人,身体变异了,与常人形态不同,因此癌症曾经作为一种会引起变异的疾病,让人恐惧和不敢提及。但是癌症如果全身转移的状态,变异的只有一两部分,那么把变异的地方切除,这个人不就是普通人了吗?因此切除了那个丑陋的部位的人,作为一种曾经变异的生物变回人类的可怜虫,被人们同情和接纳着。许多丧尸影视作品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的手或者腿被丧尸咬到后,他的同伴及时砍掉了他的腿或者手,于是他得以保存人类的身份继续好好地活着,比如美剧《行尸走肉》和美国电影《僵尸世界大战》。丧尸是一种变异的人类,是被病毒感染的人类,因此也是病患,但是这样的桥段明显带着对丧尸人类身份的不认同。正如曾经人们对于狂犬病和紫质症患者的不认同,认为他们是异种,狼人和吸血鬼。由于癌症患者的发病的样子没有这样恐怖和特异,因此没有被异化到这样的程度,没有被排除到人类之外,但是却被排除到了“普通人”之外。人们对于切除的狂热,也不仅仅表现在癌症的治疗上,例如现代美容技术,激光祛斑和激光褪毛,毁灭体表上一切“不正常”之物,以让自己在“普通人”的行列。“长了斑的人”“身上有体毛的女人”被与普通女人对立起来。这样的极端的对于变异的恐惧如今正在我们的生活中蔓延并且越来越严重。但是好在,由于癌症的治疗有所发展,所以他导致的变异是可以挽回的,因此人们对于这个群体的消极看法正在逐渐消失。甚至对这个群体的看法不仅再是同情与怜悯,还有敬佩。
这样的变化有两个前提。一是,曾经,人们认为癌症是羞于启齿的,这是因为癌症“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但是随着认知的进步,发现癌症也会攻击身体的一些神圣的部位,比如脑部。二是,对癌症人群认知的变化。曾经人们认为患肺癌的人爱抽烟,患宫颈癌的人性生活糜烂,癌症群体有愧对于道德和生活的地方,所以才会患上癌症。可是现在人们则认为部分癌症与遗传有关。癌症那种神秘的伪传染性变为了确定性的家族传染性。这样的变化使癌症人群从有污点的人变为了无辜的、被上天遗弃的可怜人。
除了这两个关于人们认知变化的前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癌症至今仍然被与情绪联系在一起,并且由于其遗传因素被强调,而从一种入侵的,外化的,单一疾病,变为一种自发的,内部的疾病。因此,癌症患者与癌症的对抗,被认为是一种自我对抗,与异化抗争的过程。这有两种体现,一是隐瞒患者其身患癌症,早在20世纪就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当做一桩丑事。”,但是现在原因则略有不同,瞒着患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需要患者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以免糟糕的心情影响病情。心态会影响病情,这几乎变成了一个常识,中国人口报上曾刊登《改变心态远离癌症苦厄》和《保持乐观心态有助于癌症治疗》等科普性文章,这一类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更加常见。那么心态是否真的对癌症有影响呢,现在仍未有特别有力的证据证明二者有关。但是甚至连医生,都不否认二者的关联性,他们甚至把人的心情看做癌症治疗的一环。只要避免病人内心的争斗,这场战争似乎就有大几率可以获胜。二是,癌症病人在接受询问或主动描述自己经历时,总是强调自己心情的变化,这点从许多关于癌症的采访和纪录片可以看出来,“我目前非常平静”是这些病人常常说出的一句话,好像说出了这句话自己的疾病治愈率就会增加。日本厨师神尾哲男在发现了前列腺晚期之后,仍然活了十四年,并出版了自己关于癌症食疗的书《癌症以后这样吃我活了十四年》,姑且不论这本食谱是否科学,书中除了饮食之外也非常强调对待癌症的态度,作者这样描述自己对抗癌症十四年的心得“和癌症对抗是行不通的,因为对抗的敌人也是自己一部分……我们要一起活下去。”这段话无疑是一个自我对抗的过程。自我斗争,是一个带有美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的过程,与对抗外敌不一样,既符合现代性又有崇高性。因此那些对抗癌症却成功的人变得像英雄一般,而那些未成功的,也被当做壮烈牺牲被人们记忆。比如,宋美龄患乳腺癌曾两次手术,但是一直活到百岁。成功是涅槃的凤凰,失败了是昙花。总之,都是正面形象。
由于类似的原因,其他疾病的隐喻也在当今时代发生着剧烈变化。与癌症相同,艾滋病也被认为是绝症,其隐喻也包含着绝症皆有的勇气。可是二者却相差甚远。癌症病人的勇气,多是正面意义的勇气,比如帮助人类走出绝境,引起人们对某社会问题的关注等问题。但是艾滋病人的勇气则多是报复社会和恶意传播,因为“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的社会性死亡”。这是人们的恐惧向艾滋病转移的一个表现。这些令人恐惧的疾病通过把病人转化成他者(另一个种族),来将自身隐喻化,这一点从始至终都未变过。但是被转化的他者,却有着高下好坏之分。这些疾病有的高雅有的低俗,甚至于同样是绝症,待遇却不尽相同。病人跟病人之间也有阶层的划分,癌症病人是令人同情和钦佩的,艾滋病人是值得恐惧的。但是这种偏好,这种恐惧,却会随着对疾病的认识所转移,转移到一种新的,认知不够的疾病里。曾经的梅毒,癌症,现在的艾滋病,未来的另一种传染性极强,发病原因与自身有关,存在变异因素的疾病——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疾病,让人们倾泻自己对于生命尽头的恐惧和厌恶。也许某一日,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未知的疾病已经不存在,唯一的绝症是衰老之时,生命就变成了最后的唯一的时代疾病隐喻。
【注释】
[1] 《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麦田出版,程巍译,p23
[2] 《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麦田出版,程巍译,p11
[3] 《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麦田出版社,程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