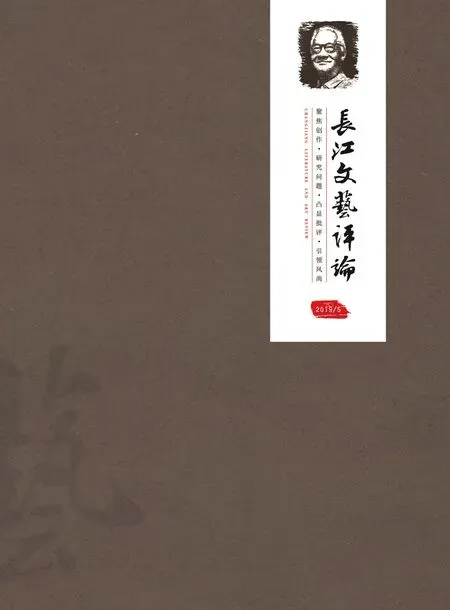以真性情为巴土文化立传
——谈周立荣的歌词创作
◆刘 波
一
从写小说到写歌词,周立荣的文学之路似乎经历过很大的反转,他以激情的方式一次次地实现自己的艺术抱负。也许周立荣就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否则,他也不会在自己的创作上如此冒险。18岁开始创作,20来岁写的八万字中篇小说《山骚》发表于《莽原》杂志,后出单行本,随即引起很大反响,了解周立荣的读者,都以为他会顺着这条叙事之道做一个小说家,周立荣自己当初可能也是这么打算的。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样一条顺利的文学之路,是多少年轻写作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可奇怪的是,周立荣后来逐渐放弃了小说创作,不少熟悉他的朋友,都有些惋惜,不知当年的周立荣自己作何感想。
之所以从周立荣的文学创作道路来引入对他的认识,还是在于他的创作正契合了某种国家改革的策略——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求经验“再造”之道。从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回到现实,从激情的青春走到成熟的中年,从微观叙事到宏观抒情,周立荣看似走了一条与很多作家相反的路,其实他有着自己对文学独特的理解。别人是用诗将激情挥洒在了青春时代,然后逐渐转向理性的叙事;可周立荣最开始小说和诗歌齐头并进,将青春以叙事的方式定格在了理想的年代,尔后,他返回到抒情的人间,再以歌词的方式重塑他对巴土风情的回望,这里面是否暗示了一种必要的身份认同?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如何以更文学的方式来重新命名自我,这在于一种敞开的胸襟,一种决定作家文学境界的义理和格局。
当年,周立荣在小说中叙述自己的故乡,那片清江山水画,皆在一转一折之间,无论内部暗含着多少戏剧性,离乡和返乡的矛盾冲突,都只是一个过去时代的烙印。后来,他以一种更雄壮开阔的歌词形式,再次抒写了那方生养他的土地,皆在那一吟一唱之间,离开了故乡,山水还是那片山水,只是更多了乡愁的意绪。可能很多作家都无法回避这样一条路径:年轻时竭力排斥故乡,皆因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向往,而人到中年,又开始怀念故乡,这种怀念里隐藏着在外游子难以言说的孤独。当我们迫不得已把他乡作故乡时,更难消除的,还是那种漂泊流浪的无根之感。其实,我在周立荣早期的一些歌词中,洞察到了这种隐隐的忧伤。即便他在书写清江的山水风俗与人伦情爱时,仍然带着乐观主义的格调,可是,大山的苦难深深地扎根于他的人生里,并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关键词。这就是命运赋予他的虔诚,他最终只能以抒情的方式,再次领受故乡给予他的爱和馈赠。
周立荣的文学选择,也许无法用“不走寻常路”来形容,他自然地闯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那条通道。不管他曾经做过多少种工作,经历过多少命运挣扎,他还是摸索着回到了文学,这是他内心的精神家园,这一点不用别人规劝他,利诱他,不管他在外追梦多少年,还是会回来,回到他牵挂的词语中,回到他梦萦的艺术旋律里。他可能做了很多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但他一直在以文学的方式行事,这已经内化成了他身上的某种气质。无论他走多远,也只有在语言和音乐的交融滋养下,一个钟爱文艺的灵魂才会安放下来,才会在历史感的溢出中获得一方宁静。
二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周立荣,是否是一种冒犯?当然,这种推测即使是在冒险之中,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含着某种文学的隐喻意味。周立荣集中在某个时段书写一种文体,也可能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但无论有着怎样的原因,他终究是由着自己的心性,在美学的意义上对文字进行审视。从小说到散文,再由散文到歌词,虽然文体越来越短,也越发具有抒情性,然而,他正是在这种文体转换的过程中,构筑起了自己越发雅致的文学王国。
1990年,周立荣27岁,那时他或许还沉浸在小说与散文创作的喜悦中。3月8日那天,他写了一首《爹是山里男子汉》,这首歌词貌似赶了1990年代初信天游的风潮,但是周立荣将这种形式移植到了带有巴楚风味的土家大山书写中,也别具一番生动和情趣。这种不同地域的风格移植,在歌词创作界是很普遍的,它恰恰构成了周立荣早期歌词创作的一个关键节点。抒情并非文学的敌人,就看怎样抒情,如何抒情。与那些泛滥抒情可能趋于空洞的歌词不同,周立荣这首歌词是有所指的,他由平凡普通的爹出发,抒写了大山里的亲情,这是最好的切入口,直接,干脆,且在一些描述性的细节中来呈现山里人的质朴、纯真和原始力量。
歌词在音乐中的作用,功能不一,就看我们如何去理解与把握了。有人听歌可能只注重旋律和节奏,而极少关注歌词本身,但歌词的力量在于语言和情感内在的呼应,那种情绪流和音乐一起,会注入我们的内心,作用于感官,成为一道润泽心灵的清新剂。对此,周立荣抓住了歌词的力量,因为押韵不是问题,而如何应和一种内在的节奏,才是关键。所以,他后来不断地琢磨起歌词的韵味和美感,应是一种深入创作的体现。当他将笔触和情感直接对准自己最熟悉的土家风情和巴楚山水,这两方面的题材构成了他歌词创作的源泉。尽管后来也受邀写过一些“应景”之作,但他只要一下笔,总会不自觉地回到故乡的山水风物,这是他的精神根据地,他的写作,就是要为那片土地在文学和艺术上立传。周立荣的歌词创作立足于土家和清江,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过分局限于地方性了,然而,正是这种地方性成就了他。他将自己的个性与风格,恰如其分地对接了地方性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地貌,这样就自然生成了他的峡江歌词美学。所有的生命、爱恋与情怀,都在他的歌词中得以被记录、演绎和流传,这不仅是一种功德,我想,对于周立荣来说,它还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始。他起步于地方,由此出发,再将这片土地赋予更丰富的内涵与文化力量。
三
周立荣新世纪以来的歌词创作,多集中于大江大河,从意象上来看,视野开阔了,而从主题上而言,则开始转向民族文化和自然山水。这种转型对于周立荣来说,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于家国情怀的某种回归。如果说之前他是专注于个体的自我言说,那么,新世纪以来,他更多地在向时代和世界敞开自己的胸怀,这里有不少可以自由拓展的空间,同时他也在创作中出示了自己的美学标准和艺术体系。
曾经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的《巴土恋歌》,即是周立荣新世纪创作转型的体现。从歌词本身来说,周立荣可能并非要契合什么民族风,他由过去关注故乡的个体与细节,上升到了对整个巴土地域文化的历史追溯和当下定位,尤其是经过方石谱曲之后,更是获得了一种文化的立体感。面对大山,面对清江,这位土家词人用他积累的血性、真情,书写出了民族的魂魄,也道出了个体记忆在遭遇公共经验时的价值选择。
周立荣新世纪创作转型后的抒情,在建基于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同时,并没有以丧失文学性作为代价,他甚至更在意歌词的诗性特征。那种大开大阖的气势背后,所流露出来的,仍然是他现代性与古典感交融下的中国风,这种中国风的书写,不能完全依靠天马行空的想象,它的放达与神秘,其实也是作者人文修养和历史风度在文字中的体现。像以三峡、土家和清江为主题的《巴楚天堂》《巴土风情》《清江画廊》《三峡神女》《三峡恋歌》等歌词,都是巴土峡江文化的生动再现,它们虽然同属于一个文化体系,但又都有着各自的格调与品味。那对于周立荣来说,既是一种诗性气质,也是一重精神境界。尤其是《喊山歌》,以山歌文化切入命题,真正写出了土家人喊山歌的那种豪迈与野性,微妙的文化暗示和身体书写里,更有着话语修辞的灿烂与精彩。《昭君还乡》则以历史书写的方式,还原了一个经典形象,在歌词中,昭君已经自然化和经典化了,所有的传说和演绎,都化作了一份念想,一种关于爱的回溯。
没有抒情不成歌,周立荣不仅书写过往和记忆,也创造当下的人生,他还清楚,自我的生命里也有诗和远方。在他二度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江河恋》里,“周氏词风”再次唤起了我们的信任。在我的理解里,周立荣激活了江河在他内心的某种情愫,将一种大气磅礴的精神寄托在了浪花一般的想象搭配和词语组合上,而我们的自然与文明也在这种书写里获得了永久的回响。这是周立荣文学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变得越发自由、率性,以真心书写他钟情的山水、自然与风物,这些主题成就了他;而他也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了现代歌词在理想主义精神上的启蒙之真和对古典趣味的传承之意。
周立荣以歌词为巴土的山水与文化立传,这是他的信念,他的梦想,也是他的一份责任。以上也许只是阶段性的总结,此后,周立荣在歌词创作上仍会踏上新的征程,那将是他又一个“抒情时代”的开始,未来的那道文学之光,依然会真切地划过巴楚风情的历史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