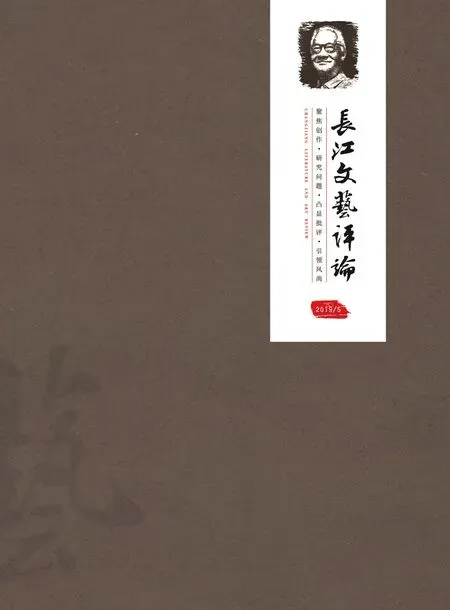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美学的丰富形态
◆陈旭光
2018年的中国电影,曾经遭遇了行业“遇冷”的“寒冬期”。在连续高速发展十余年之后,因为税收政策的改革所导致的行业震动,也因为多年来粗放型的扩张,以及人口红利、影院银幕数红利、票补红利等的终结,影视产业的高速发展遭遇“瓶颈期”。但是,随互联网+加时代影视企业发展愈发迅猛,网络影评、评分网站使得“口碑”日益重要,创意、内容、质量成为真正的制胜之道,从这些方面看,2018年度的电影创作颇可称道,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仍然值得期待。
一
在本年度“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复杂态势中,现实主义美学潮流的涌动及多样化美学形态,喜剧电影的多样化风格、新力量导演的崛起、青年媒介美学新类型的涌现等现象令人欣喜。
《中国电影年度蓝皮书2019》,以助推中国电影艺术与产业的健康、高速、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影响力、创意力、运营力、工业美学、新美学等为关键词或标准,秉持互联网+时代电影的“多元评价标准”,兼顾电影的商业/艺术,票房/口碑的“二元对立”,综合考虑类型、题材的代表性与多样化,文化的多元化与丰富性等原则,经北京大学与浙江大学的青年学生的初选和推荐,再经过五十余位国内重要影视专家的最后投票,我们又一次迎来2019年度“蓝皮书”。2018年度十大影响力电影,按得票排序如下:
《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无名之辈》《邪不压正》《影》《江湖儿女》《狗十三》《无双》《无问西东》《地球最后的夜晚》。
后十部则依次是:《找到你》《阿拉姜色》《暴裂无声》《唐人街探案2》《西虹市首富》《一出好戏》《你好,之华》《后来的我们》《动物世界》《超时空同居》)。
《我不是药神》《江湖儿女》《无问西东》都不乏现实主义精神与直面现实、历史的勇气。实际上,2018年度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表现形态更为丰富。颇具现实主义力度和女性自省精神的《找到你》,以精神朝圣为主题但又凝聚了更多现实生活、民族生存思考的《阿拉姜色》,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假定性寓言体《一出好戏》,具有游戏架构的《动物世界》,小成本科幻电影《超时空同居》等未能入选,其实还是有不少遗憾的。
毫无疑问,这十大“影响力电影”的布局及其背后隐现着的中国电影生态,活画出了2018年度中国电影艺术、文化与产业的地形图。
现实主义回归是2018年最为重要的电影文化和美学景观之一。许多电影触及当代中国现实、社会与民生的问题,书写了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之中试图自主或无法自主的悲剧命运,从而生成一股深沉、悲怆厚重(不排除黑色幽默化的喜剧)的现实主义的电影文化潮流。多年浸淫于轻喜剧、玄幻、魔幻的观众对这个现实主义潮流的回归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这些电影不仅形成了与以视觉效果取胜的进口大片相抗衡之势,在网络上也形成了有关这些电影的巨大舆论场。
从十部比较重要的现实题材电影的票房看,票房总共达到了67.81亿,其中《我不是药神》达30.97亿、《后来的我们》达13.52亿、《无名之辈》达7.94亿、《无问西东》达7.54亿、《悲伤逆流成河》达3.55亿、《找到你》达2.85亿。还有的现实主义风格或题材的电影,虽票房不尽如人意但艺术上获评颇高,如《大象席地而坐》《狗十三》《阿拉姜色》《宝贝儿》等也从各个角度或层面,积极介入现实。
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层出不穷地衍生着诸多来自社会阶层的分野、来自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来自城乡差距的加大所导致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新闻、社会现象每日里层出不穷、热点频仍,但是,大多数电影依旧是在娱乐的层面、讲述或猎奇、或虚假、或某一阶层的小时代的故事,而没有深入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去,文艺作品没有能够和人们的当下生活产生共鸣——类型化、却离人民生活较远、以奇观化、娱乐性来吸引观众早是产业中的某种主流”。无疑,本年度崛起的以当下现实为观照对象的现实主义电影,进一步满足了观众的现实需求,发挥了电影作为“窗户”或“镜子”的功能,是国人认识社会,完成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
二
现实主义不是标签而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直面现实、面对社会问题的勇气和态度,其道路更应该是宽广的。我们不妨把2018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电影区分为“问题现实主义”“青春现实主义”“女性现实主义”和“荒诞现实主义”四种美学风格形态。
其一,“问题现实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戏剧有“问题剧”或“社会问题剧”之说。问题现实主义电影就是直面现实问题,反映社会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电影,态度是积极向上的。《我不是药神》就是如此。
在《我不是药神》中,人物所处的环境与位置整体而言都是压抑、灰暗和令人沮丧的,但是整体风格却并没有落入异常沉重压抑的状态中,而是轻松自如,日常生活化,甚至带着些许诙谐。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但对之进行了更加典型化的加工。比之于原型,主人公更具有丰富多样的小人物性格特征,最后塑造的是一个属于当下中国的“平民英雄”——一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陌生人”。《我不是药神》中群像式的人物塑造更让我们产生了共鸣。
程勇这个“平民英雄”是一步步“长大”的,一个有家暴倾向,历经婚姻失败,儿子离散,经济窘困但敬老爱幼的“小人物”,经过一系列情感与生死的磨砺,最终成长为一个为了他人牺牲自我,铤而走险的“药神”。据说现实生活中的原型程勇本人就是白血病患者。他曾经评价说,如果电影中的程勇本人就是病人,其所作所为会更具真实性也更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但电影中这一平民英雄的塑造,有着颇为符合好莱坞戏剧化电影情节的逻辑和节奏,因为与现实生活、空间场景融为一体的影像叙事,使得整个故事的发生,人物形象的建构都显得比较实在,人物行动逻辑与性格、形象基本可信,成为一个发生在当下的平民故事、“中国故事”。
《我不是药神》触及了中国当代社会中的社会、阶层矛盾,而且以城市的边缘空间作为主体景观,不再聚焦于代表着城市化和现代性的高楼大厦和豪华空间。另外,《我不是药神》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某些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内在冲突,但是电影却给了一个光明的结局——程勇三年刑满出狱,慢粒白血病的药被国家纳入医保体系——这就给了已经被感动的观众以希望和信心。因此,正如笔者所言,“《我不是药神》非以情节、戏剧性取胜,亦非以徐峥所擅长且品牌化了的喜剧性为噱头,而是以悲悯的人道情怀,小人物的人道勇气,接地气的现实批判精神感人心怀。洋溢着温情,不那么悲催无望的结尾虽然降解了现实批判的力度,但符合体制的要求和普通百姓的中国梦,终于引发全民热议和观影热潮,并被寄予了推动现实变革的民众理想”。
其二,“青春现实主义”。《悲伤逆流成河》《后来的我们》《狗十三》等电影,大体属于青春片。通过青少年与社会、父权、资本发生的碰撞与矛盾,来完成对社会的审视和自己的长大成人。
《狗十三》以一个十三岁初中女生的视角,通过她养狗、丢狗、找狗以及再次失去狗的成长经历,来表述她在成长过程中与成人社会的冲突、归化或妥协的历程。影片不是简单下价值判断,不是简单地批评谁,更重要的是它带给我们超越生活表象的深度理性思考。与之相似,《后来的我们》通过一对青年北漂恋人的恋爱史和奋斗史,来表现北京这个大都市内部的社会落差、阶层差别以及种种价值观与生活观的冲突。
《无问西东》讲述四代清华人的青春故事,却几乎串起了一部中国现代史。影片虽属历史题材,但跨度极大,既包括对“文革”的反思,还有当下现实的人生选择。虽然也有“文革”中残酷批斗、人人自危的阴影笼罩,但影片呈现的整体调子是明朗光明、热情洋溢的。《无问西东》实为近年比较难得的有历史意识、艺术品格和思想深度的青春片。
《无问西东》的结构是颇富有创意力的,甚至带有互联时代“数据化思维”的特点:四个年代,四个故事,每个故事自成一体,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连结,环环相扣。20年代的吴岭澜,30年代的沈光耀,50年代的陈鹏,新世纪的张果果,不同时代的人,既有属于个体的忧伤,又有属于时代的焦虑,更共同有着青春的理想、激情和追求。每个故事似乎都以光明为结尾:吴岭澜成为一代大师,沈光耀战死沙场成为民族英烈,陈鹏成为科学家,张果果最后决定帮助四胞胎及其家人。当然,这些人物的成长都经历了巨大的“创伤”,几乎都面临过人生节点的重要选择。他们也许都具有某种“悲剧性”,某种悲怆的调子,但他们都是在可抗或不可抗的历史洪流和社会波澜中力争自主选择的个体的人、“大写的人”:富商华侨独子沈光耀,义无反顾投笔从戎,投身抗战,在蓝天上保家卫国;李想,救下张果果父母却牺牲了自己;张果果毅然决定帮助他人。毋庸置疑,电影直面现实的所有人生选择、反思批判,最终都指向人性之善,家国使命的重要性和个体选择的意义,并最终凸显了清华大学的校训即影片主旨——“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其三,“女性现实主义”。与往年大量“小妞电影”所呈现的女性物质欲望、安全心理需求等的隐秘表达主题不一样,本年度的《找到你》与《宝贝儿》等电影,堪称女性题材的悲情现实主义表达,可以称为一种“女性现实主义”电影。这些电影关注当今中国不同阶层的女性问题,婚姻、职业、生育、母爱、爱情等。
《找到你》具有清醒的女性自省意识和丰富的社会意识形态内涵。影片把三种分属不同阶层(相应的职业、收入、生活境遇等)的女性放在一个因为丢失儿童而引发的情节链中,使得原来可能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同阶层女性面对面近距离发生关系。她们都在有关孩子的冲突中面临艰难的抉择和巨大的创痛。三个女性分别代表城市白领职业女性、普通家庭妇女和底层劳动妇女。职业女性事业成功,恪守所谓的“法理”;家庭妇女相信“孩子是我的全部”,不能判得孩子就觉得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底层劳动妇女则带着对这两个阶层的嘲讽,以“偷孩子”的犯罪行为“挑战”社会上层,同时带给观众关于女性位置、女性身份、女性情感的深刻反思。
底层女性孙芳带着对他人、对社会、对自己的绝望(但心地善良,母性永恒)而跳海,将中国底层女性的悲剧人生裸呈在我们面前。虽然孙芳最后被救起,作为律师的职业女性也通过对另两个女性的设身处地、推人及己而完成了自己的反省。影片展示的女性心理深度是发人深省的,揭示的社会问题是非常严峻的。
《江湖儿女》继承了贾樟柯一贯的现实主义传统,将人物“抛入”时代巨变中。“剧变的小城市里,他们建立江湖,他们毁灭江湖,他们离开江湖,他们回到江湖。‘江湖’在这里不是一个特指,而成为一个泛指,也即其所引用的那句《笑傲江湖》的话,‘有人的地方即有江湖’。所以贾樟柯书写的个体往往是具有某种寓言性质的个体。《江湖儿女》最终走向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高潮:巧巧在辽阔的新疆的戈壁上,看到了璀璨的、布满星空的、象征着终极理想的UFO。”当然,这只是一种贾樟柯开出的虚幻化解决的药方。
这部电影是贾樟柯电影中不多的主要以女性视角叙述故事,审视男性的电影,巧巧在出狱之后依然以某种女性的博爱给斌哥以落脚的地方,常常维护斌哥孱弱可怜的虚荣心,既代表了女性的某种自立与自强,作为男性导演,也表征了某种男性的自我反思意识。
其四,“荒诞现实主义”。2018年,是寓言性电影或寓言体电影的丰收年。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它原指一种旨在进行道德劝谕、扬善惩恶的文体,而且它与神话、史诗等文体一样,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国先秦诸子散文中的“诸子寓言”。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2019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指出,2018年的中国电影创作,出现了一个“寓言体”现象。《邪不压正》《一出好戏》《动物世界》《无名之辈》《江湖儿女》《西虹市首富》《李茶的姑妈》《影》等都集中体现了鲜明的“寓言创作”倾向。
但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一种建基于不无荒诞性的假定性情节结构之上的寓言。上面所述的部分电影,在电影语言层面是基本写实的,它还是要追求一种可信性。但如《一出好戏》《动物世界》《幕后玩家》都设置了一个假定性很强、有一定的封闭性、颇为荒诞的涉及总体情境的叙事结构,都以封闭空间和“逃生”作为核心叙事,这种假定性构成一种寓言性或象征性。
《一出好戏》通过荒岛情境的设置,推到荒岛上人们原先的社会地位和阶层属性,通过各色人等在一个原始天地的行为反应,为了食物而尔虞我诈、争风吃醋、重新分配权力,实际表达的是对人类文明、人性善恶、社会权力关系等的思考。
《动物世界》设定一个远离社会、漂浮在公海上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的生死赌博的邮轮,游戏方式虽简单但却直接与命运生死、金钱、人性相关联。它以寓言的方式指涉了爱情与友情、信任与背叛、规则与契约等人性难题,直抵灵魂深处。
不同于《一出好戏》《动物世界》《幕后玩家》这样的荒诞性假定性结构的电影,《无名之辈》是一种整体风格、情调上的荒诞性和寓言化。它的叙事形态很独特,是非线性的、多线并置式的,但它是接地气的,它所满怀理解和深情聚焦的是在城市中挣扎生存着的小人物——他们身上所固有的,是作为人的尊严,是大时代中的某种自我选择。《无名之辈》通过悲喜之间的戏剧化冲突、多线性叙事和快节奏剪辑的视听风格,书写了荒诞社会和人生。
2018年这股现实主义潮流的崛起源于中国当下现实的需求。它们讲述基于当下的“中国故事”,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关注民生社稷,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和力量,也源自于今日中国崛起的文化自信。“这些电影揭示了当下中国人面临生存或经济困境。这个困境不光裹挟了《药神》中的病人、《找到你》的保姆、《无问西东》中被扶贫的一家、《后来的我们》里的北漂、《无名之辈》中的马先勇,还裹挟着那一批看似经济条件尚可的中产阶层,如《找到你》的女律师、《狗十三》的父亲、《江湖儿女》的斌哥、《无名之辈》里的高总——这批人,不再是小时代里光鲜亮丽、用情感左右命运的人们;而是在现实的压抑中生存着的人们,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理论,都是作为‘此在’的‘在者’”。
除上述作品之外,部分现实主义作品还涉及到了校园暴力(《悲伤逆流成河》)、少数民族的家庭与信仰(《阿拉姜色》)、老年人赡养问题(《大象席地而坐》)等。这些现实主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地指涉了现实问题,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创作趋向,表明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注释:
[1]陈旭光、范志忠主编:《中国电影蓝皮书20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陈旭光、赵立诺:《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与艺术年度报告》,《文艺论坛》,2019年第1期。
[3]陈旭光:《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上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4][5][7]陈旭光、赵立诺:《2018:中国电影文化地形图》,《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2期。
[6]【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