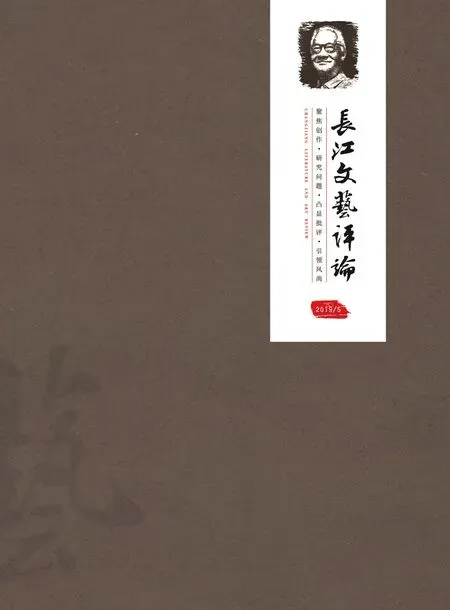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的镶合
——兼论《暗算》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增量意义
◆陈培浩
从2002年出版曾被退稿十七次的《解密》,到2008年摘得中国最有分量的文学奖,麦家迈向文学巅峰的时间如此之短,这是因为麦家在题材和写法上都走了一条不可复制的道路。李敬泽称麦家为文坛“偷袭者”,某种意义上,麦家携带着在新世纪日益强大的类型文学象征资本,逼使日益陷入窘境的纯文学打破自身的边界。《解密》《暗算》《风声》大热之后,诸多重要文学批评家纷纷从麦家独特的题材和想象力中阐发“麦家的意义”,这意味着,主流文学界正努力通过接纳麦家,将麦家经典化来弥合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之间的缝隙,并维系严肃文学写作的新平衡。这或许便是麦家获奖背后的文化意味。
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等被称为“特情”(或新智力)小说,使用了类型小说的题材和叙事,却延续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小说”中常见的命运主题,在人物谱系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了一系列“悲剧天才”(也称为“弱的天才”)形象,这事实上是将八十年代以来的个人性话语融入社会主义文学的英雄叙事,将人学话语铆合于国家话语的结果。麦家的人物塑造还促使我们去思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被麦家转化为“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之后,对经典现实主义产生了怎样的爆破和新创?并不抵达“一般”的“特殊”,在麦家这里将打开什么样的“可能性”?
一、《暗算》:版本重构的文化政治
用麦家的说法,《暗算》“写得很容易”,写起来有削铁如泥的感觉,只用了七个月,“甚至没有《解密》耗在邮路上的时间长”。2003年,出版《暗算》时,麦家尚未得到市场和主流文坛的认可。电视剧《暗算》的走红无疑助推了麦家的名声和小说的畅销,但电视剧《暗算》仅使用了小说《暗算》的前二章。初版本的《暗算》共分三部五章。第一部《听风者》含第一章《瞎子阿炳》;第二部《看风者》含第二章《有问题的天使》和第三章《陈二湖的影子》;第三部《捕风者》含第四章《韦夫的灵魂说》和第五章《刀尖上的步履》。应该说,《暗算》的结构倾注了麦家的一腔心血和深沉寓意,但后来这部小说的结构却遭遇质疑:“火力最猛的是关于小说‘各章独立’的结构上,有人甚至因此认为它不过是几个中短篇的巧妙组合。对此,我深有‘委屈’之苦。”为此,麦家不得不为《暗算》的结构一辩:
我对《暗算》的结构是蛮得意的。《暗算》是一种“档案柜”或“抽屉柜”的结构,即分开看,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可以单独成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
对结构的满意并不意味着麦家对作品满意。上述辩言写于2006年,在此之前,麦家在改编电视剧《暗算》时,已经深深意识到初版本第二章《有问题的天使》“似乎只有人物,情节缺乏张力,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个破译家,主人公黄依依只有对密码的认知,缺少破译的过程。用个别评论家的话说,这个人物只有‘心跳声’,没有‘脚步声’”。麦家遂萌发了修改之念,借着电视剧改编之机,搜集了大量素材重写,遂有了后来所谓的“作者唯一认定版”。
修改完毕之后,麦家心心念念的是在《暗算》再版时将内容替换,也曾与后来的版权授权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协商。出版社没意见,但希望将已印作品售完再换新版。有趣的是,2008年《暗算》连续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和代表中国文学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然不愿改变茅奖作品的原貌。后来经麦家本人亲自参与协商,《暗算》版权改授作家出版社,采用修订版内容。
然而,《暗算》的版本故事并未结束。2012年,英国企鹅出版公司买走了《解密》和《暗算》两书的英语版权,并将其列入“企鹅经典文库”。这是麦家小说迈向国际化非常重要的一步,麦家遂成为继鲁迅和张爱玲之后列入“企鹅经典文库”的第三位中国作家,也是唯一列入该文库的在世中国作家。不过,该书的编辑却提出删掉最后一章《刀尖上的步履》的建议,原因在于:
前面四章,从题材类型上说是一致的,都是一群天赋异禀的奇人异事,做的也都是事关国家安危的谍报工作,却独独最后一章,岔开去,讲一个国家的内部斗争,两党之争,扭着的,不协调。
麦家接受了这一意见,他感慨《暗算》“出现第三个版本,这是它的命”。2013年,麦家写下《〈暗算〉版本说明》:“到目前为止,除英语外,《暗算》还卖出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多个外文版本,在以后的以后,它们都将一一成书出版。我不知道,该书奇特的命会不会还安排哪个编辑来制造新的版本?”2014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暗算》采用的是与英文版本统一的内容,即删去《刀尖上的步履》一章,说明麦家对英文版本的认可并非出于海外传播时必要的妥协。
《暗算》三个版本的变化,主要落在情节和结构两个元素。第二版在情节上对《有问题的天使》进行改写和扩容,使黄依依作为破译家既有“心跳声”,也有“脚步声”;第三版通过内容的删节对结构的属性进行变更,所谓从ABB的开放型结构变成ABA的古典闭合型结构。然而在我看来,第三版的修改其实可以有另一番解读。
麦家在《暗算》的结构上“深思熟虑”,简单将《暗算》结构视为几个中短篇的“巧妙”集合(言其“巧妙”,实责其“讨巧”),并不符合事实。要注意《暗算》非常严格的限制叙事,以及通过身为作家的叙事人将不同章节串联起来的良苦用心,其严谨性不是一般由几个关联松散的系列中短篇连缀而成的长篇可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且不论《暗算》在艺术上的完美性,我们必须看到其初版本中便已经显示出来的某种“整体性”或“有机性”,其意义已经超越麦家自己强调的“抽屉结构”。《暗算》中,阿炳、黄依依和陈二湖都是破译家,阿炳和黄依依都属于“弱的天才”,是天才和白痴的结合体,是悲剧化的英雄,他们之间构成“同位关系”;陈二湖和阿炳、黄依依同为破译家,都为701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不是“弱的天才”,却也遭遇了和他们二位程度不同的悲剧,所谓异人同命,殊途同归,陈二湖与阿炳、黄依依构成了“对位关系”,诠释了破译家的另一种悲剧方式。从第三部开始,《暗算》就突破了“破译家”框架,《韦夫的灵魂说》写的是701执行局老吕“导演”的一出故事,这并不属于“电台密码破译”而属于“谍报”。《韦夫的灵魂说》可能得之博尔赫斯《分岔小径的花园》的启示,描写一种以死人作为传递情报媒介的谍报方式。从叙事学角度看,《韦夫的灵魂说》在主体故事采用死者越南人韦夫的灵魂视角,这对严格限制叙事来说是一种瑕疵。因为在其他部分,整部小说的叙事人——第一人称“我”,一个与701有接触的作家——所有故事材料都是通过听乡党或朋友讲述得知,这是符合现实情理逻辑的。独独《韦夫的灵魂说》一章在此不能成立,换言之,当作家不能完全严格地遵守限制叙事时,他不能不借助于“视角越界”来弥补材料之不足。不过,《韦夫的灵魂说》显然扩大了《暗算》中701的工作格局,701作为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特殊部门,不止有“破译处”,还有其他同样不得不身处“暗算”和“被暗算”逻辑的执行部门。而韦夫这个在战争中蒙受不幸的越南小伙,意外地卷入这场“暗算”中,跟整部《暗算》人不能决定自身命运的主题有着密切关联。因此,第四章使《暗算》的内在张力进一步扩大。
到了第五章《刀尖上的步履》,小说的取景框进一步扩大,它在空间上超越了701,在时间上已经来到1940年代,写国共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谍战,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特工人员之命悬一线、忠心不渝以及莫测的命运。显然,这一章是最近于国家的英雄主义话语的。或许,写作《暗算》时,麦家便在小心翼翼地维系着种种话语的平衡。前面的部分,书写天才英雄的悲剧,更容易获得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学个人话语的共鸣;但这些天才的悲剧如何在国家主义话语的内部获得意义,第五章给出了解释——701英雄们的悲剧,在第五章显豁的国家安全视域中得到了整体确认和提升。就此而言,第五章对于《暗算》并非可有可无。很可能,对于茅奖而言,第五章也是主题上画龙点睛之笔。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企鹅经典文库”不同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如果仅是为了保持小说那种关于“破译家”的奇人异事的相同属性,那么《韦夫的灵魂说》也在可删之列,但何以这个故事被保留,很可能是因为这依然是一个基于个人话语立场来书写战争的作品。小说奇特的故事背后隐含的依然是个体无常的命运。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越南小伙韦夫因为身体原因而被安排在一个很窝囊的管仓库的岗位;没能上战场的他因此获得了一个完整的身体,这导致他的尸体被老吕看上,死后被用来顶替一个叫胡海洋的中国人,他的尸体替中国向美军发出了假情报。这是一个游走于个人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的故事。某种意义上,麦家作品正是以对个人化文学话语和国家主义话语的成功镶合为特征的,他并不放弃其中的任何一面。
然而,“企鹅经典文库”看中的是《暗算》中在谍战叙事中书写“天才的悲剧”或“人的悲剧”的这一重属性,却完全不在乎《暗算》想维持的“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平衡。其结构上的变更,与其说是让小说从开放型现代结构回复为封闭型古典结构,不如说是剔除了小说的国家话语,使其更符合西方读者的文化期待。这番改动,于是也显出了某种文化政治的意味。
二、谁在“暗算”:《暗算》的命运主题
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常常被作为题材和写法都相近的“特情小说”系列来看待,事实上这些小说每部都各有新创,但彼此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面貌也很突出,甚至于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实上,“解密”和“暗算”构成了这些小说的两个关键词。所谓“解密”,就是破译,既是容金珍、阿炳、黄依依、陈二湖等天才从事的工作,是天才与天才之间的较量,用书中的话说“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是“想方设法聆听死人的心跳声”;“破译密码不是单打独斗的游戏,它需要替死鬼!只有别人跌入了陷阱,你才会轻而易举地避开陷阱”。这里已经非常清晰地说出了“解密”和“暗算”之一体两面了。解密是一个天才通过密码与另一个天才的长期残酷的较量;解密是一个天才绕过另一个天才设下的阴损陷阱,却又陷入似乎永难走出的泥潭深坑;所以,解密之残酷就在于,破译家要充满警惕性地避开暗算,又要让同伴成为“替死鬼”,这构成了另一种“暗算”;同时解密还是对自身的“暗算”,破译家把自己逼上绝境,去踩踏科学与疯傻之间那条危险的临界线,解密事业充满了被“烧坏的钨丝”——那些被密码“暗算”的疯子。不过,在麦家小说中,最大的“暗算”或许并不来自于密码本身,而是来自于命运,来自由于自身才华被解密事业盯上时就已经无法拒绝的命运的“暗算”。
《暗算》中,陈二湖和疯子江南属于被密码“暗算”的人,尤以江南为甚。江南是《暗算》中极不起眼、一晃而过的人物,但其作用却是明显的。安在天听说黄依依又到后山去私会王主任,找到后山却遇见了因密码而疯癫的破译员江南在后山喃喃自语,仍沉浸在破译的情景中。江南的存在意在指出,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在阿炳、黄依依这些成功的破译家之外,还有大批被密码所击败的破译者存在。相比之下,陈二湖在破译成绩上比疯子江南好,虽没有取得阿炳、黄依依那样的成就,但一辈子呆在701,破译了好几部高级别的密码。但陈二湖同样是精神上被密码深深扭曲的人,表现在他离开“密码”就已经无法生活。长期从事破译这种极致的高级智力活动已经使他从一个完整性的人变成一个单向度的人。退休之后,他需要源源不断的“智力游戏”来填充。他从一个初学的棋手迅速击败各种级别的对手,最后变得一“敌”难求,精神生活又陷入极度的虚无中。这一不无荒诞的情节设计,意在说明陈二湖这批被密码选择的人,终生都难以脱离密码的精神“暗算”。
相比江南,阿炳和黄依依是密码战争中的胜利者,却都是偶然性导致的悲剧命运的认领者。换言之,在密码的暗算之外,另有一种更复杂的“暗算”令这些天才无法避开。阿炳摸电源插头自杀,因为他发现了妻子林小芳生下的不是自己的儿子。作为破译天才,阿炳没有性能力,且天真地以为只要夫妻睡在一起就会有孩子,因此以为没有孩子的责任在林小芳,为此甚至几次说要休掉林小芳重新找女人。无奈之下,林小芳找了药房的山东人“借种”怀孕。“白痴”的阿炳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孩子的出生,但他“天才”的听力却使他仅从声音上就辨认出孩子与山东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于是只有去死。这里当然有文学夸张的因素,但却通过文学虚构使阿炳之死成为令人唏嘘的偶然性的产物。因为天才的听力,阿炳成为组织重点保护的宝贝,甚至不惜让林小芳自我牺牲成为阿炳的妻子。问题在于阿炳乃是天才与白痴合体的存在,他白痴到不能明白男女之事及传宗接代之基本原理,却天才到不需任何外在手段就可以判别血缘关系。这个情节设计离奇到荒诞,但其荒诞却又因同构于解密工作之疯狂而具有合理性。
黄依依之死同样充满偶然性。几经婚恋挫折的黄依依内心强烈地渴望着爱情,甚至把任何愿意和她在一起的男人都当成了爱情对象。在破译成功成为701大英雄之后,她忍不住又跟有妇之夫张国庆暗通款曲,并且珠胎暗结。这使她理直气壮又简单粗暴地要求组织上安排张国庆离婚并跟她结婚。作为为国家安全作出重大贡献,未来依然存在巨大价值的重点保护人才,黄依依的要求得到了组织上的支持。获得幸福的黄依依却在流产手术之后在医院厕所意外邂逅张国庆的妻子,并因为后者隐秘的报复行为(让厕所弹簧门反弹打在黄依依身上)而意外丧生。黄依依死于偶然,但悲剧的必然性却隐藏在其肆意任性、无拘无束的性格中。问题于是又回到那个疯狂与科学的悖论中:假如她性格循规蹈矩,一切都在中庸和伦理的限度,没有肆意妄为的部分,她如何可能破译那些几乎不可能破译的密码?可是,她性格如此张扬,情商和智商如此不匹配,即使组织上重重保护,她又如何能逃过无所不在的偶然性?她遭遇的乃是命运的“暗算”。
在破译家之外,很多人也处在某种不可摆脱的悲剧中。比如701副院长安在天,他被组织上安排到苏联以留学生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又因组织上工作需要而被安排回国参加701的破译工作。留学期间,他并不知道他的妻子小雨同样是同一战线的地下人员,归国时他也不知道妻子小雨“惨遭车祸”身亡乃是组织上遮人耳目的障眼法。后来,当主管领导铁院长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后,他怀揣着秘密等待着妻子某一天以某种方式“复活”,为此不惜一再伤害对他痴心苦恋的黄依依。某种意义上,安在天对于黄依依后来的悲剧负有一定的责任;荒唐的是,安在天对黄依依的冷漠辜负和对妻子的忠诚守望换来的却是多年后妻子真的死于车祸的消息。一个假骨灰盒换来一个真的骨灰盒,可是多少真实的青春和日子,多少辜负和血泪已经彻底归零。这是命运对人的另一种“暗算”——你别无选择。
麦家对特情人员悲剧命运的书写,已然触及了某种生命荒诞主题。不同在于,麦家希望从这些命运不可选择的人身上不断提炼某种命运的不可知性,更提炼出一种个体为集体献身的道德情感。恰恰是这种悲剧性与英雄性同在的表现方式,使麦家巧妙地铆合了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经验”和“80年代文学经验”。这二种文学经验无疑都纷纭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涉及的概念也歧异纷争。不惜挂一漏万并冒“二元论”危险的话,我们或许可以简单说,“社会主义文学”更看重集体性,而“80年代文学”更看重个人性;“社会主义文学”更重视塑造并激活英雄的阶级主体召唤性,而“80年代文学”更重视打开卑微者的日常经验;“社会主义文学”更相信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化论,而“80年代文学”虽不都秉持历史虚无论,但由于对个人价值的坚持,因此对大历史演进过程中无数个体被轻易归零的生命经验常有悲剧化的感慨;“社会主义文学”主要以国家话语为主导,而“80年代文学”受启蒙和人性话语影响至深。由此而产生了两个时代文学不同的资源导向和价值分野,以至于人们常不自觉地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文学经验像两条背向而行的河流,在麦家这里找到了合流的契机,也便促成了“当代文学”一个新的增量。
三、从“高大全”到“有问题的天使”:英雄叙事的悲剧化
必须指出,麦家小说虽然充满了荒诞命运主题的回响,但是荒诞在他那里不是走向虚无,而是跟一种新创的英雄叙事迎面相遇,化合成一种悲剧化的英雄叙事,这也是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贡献。麦家是个酷爱读书和思考的作家,很多作家自称不读活着作家的作品,而他读,因而对自身写作占位及中国当代的文学趋势都有相当独到的把握。麦家称,《解密》之前发布的中篇小说《陈华南的笔记本》,“以前写了那么多小说,没有什么反应,为什么这个小说反应那么好?我就像尝到甜头一样。”这个“甜头”指的是特情小说独特题材带来的关注度。他开始意识到“写作应该是要有策略的,你东打一拳,西打一拳,评论家没法关注你。那么我现在写这个地下题材,某种意义上,就像我在创我的一个品牌,但是,如果我老是抱住这个品牌不走,人家也会说你江郎才尽,而我自己也会没有新鲜感了。”关于当代文学中的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他有这样的思考:
从前(50—70年代)我们的写照始终缺乏个人化的内容,都是围绕宏大叙事,问国家在说什么,问这个时代在说什么,结果是塑造了一大批假大空、高大全的英雄……现在我们这条路就是:写我自己。这种完全个人化的写作,二十年前是不允许的。这种写作对反抗宏大叙事来说有非常革命性的意义,但是这种革命性现在某种程度上被消解了。中国文学也好,中国影视也好,总有一窝蜂的毛病,反对宏大叙事时,大家全都这样做,这就错了。回头来看这将近二十年的作品,大家都在写个人,写黑暗,写绝望,写人生的阴暗面,写私欲的无限膨胀。换言之,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在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英雄叙事与平民叙事两端,麦家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从人物塑造角度,麦家确乎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象,即所谓“弱的天才”。不论是容金珍、阿炳还是黄依依,他们一方面具有常人所不具的破译天才,另一方面在生活的某方面又近乎弱智。这是一种有缺陷的英雄、“有问题的天使”。这种书写截然不同于1950—1970年代那种“高大全”的文学人物,既延续英雄叙事又能与80年代以来的人学话语相衔接。
“高大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力倡导的人物塑造原则,跟“三突出”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否塑造“中间人物”,特别是有缺点的英雄人物,曾经是长期困扰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对于文艺的反思一个很重要的点便是解除人物塑造的清规戒律。1979年洪子诚先生在一篇对话体文章《不要忘记他是人》中以一个对话人口吻指出,“在英雄人物塑造上的一些错误的理论、框框,也不是这十几年才有的”;“其中有些理论,实际上是在提倡把英雄人物写出‘神’,这种理论还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将文学人物从过度理想化、阶级化的僵化原则中解救出来,这构成了80年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当属刘再复提出的“性格组合论”。
然而,70年代末期开始的对“高大全”理想化英雄的反思,导致的不是有弱点英雄的流行,而是人学话语对英雄主义叙事的取代。80年代的英雄叙事被视为从属于“人民文学”谱系,进而被“人的文学”话语消解了。进入90年代,在文学市场化的背景下,以个人化之名而行私人化、欲望化叙事之实的潮流成了文学时尚,怀疑英雄一度成为一种普遍的大众文化心理。
麦家对特情英雄的表现,跟他个人独特的军旅经历有关:“我知道有这样的部门,虽然没有太具体地干过这样的工作,但我多多少少有些别人没有的了解。”对于他有所接触的这些特殊领域的英雄,麦家事实上怀着复杂的情感。作为一个有过军旅生活的人,他对这些因着个人天才而不得不牺牲献祭于国家安全的英雄们,当然有着崇高的敬意;但作为一个受过80年代文学熏陶的作家,他的视点并不囿于集体主义话语内部的英雄颂歌立场,带着人学立场去观看,他深刻地感知到这些英雄身上的悲剧色彩,他们所面临的内在精神深渊并由此挖掘出驳杂的人性景观。因此,麦家的特情小说,表现出国家话语和人学话语相铆合的驳杂。也正是这种铆合,使得麦家小说成了在集体与个人、革命与人性、英雄与悲剧之间相沟通的桥梁。“当代文学”在经过“社会主义文学”“启蒙文学”和“市场化类型文学”三个阶段之后,麦家是罕见地能将三者兼容的作家。因此,不妨说麦家特情小说以不同的侧面回应着“当代文学”不同阶段的诉求。
余论: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到“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
《暗算》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冲击还在于,这是一种以写实逻辑来结构的小说,却又明显超越了现实主义的成规。比如,在古典现实主义中,对人物形象的要求在于形象性和丰富性;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则要求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50—70年代文学中,对人物的要求则是“三突出”和“高大全”。要求人物性格的形象、丰富,这是要求人物必须建立一种基于细节真实的艺术可信性;要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则是要求文学通过人物去建立跟时代的关系,要求文学处理好特殊和一般的关系,通过个别对象提炼时代的普遍性;至于“三突出”和“高大全”,则是要求文学通过理想人物的塑造为读者提供一种具有社会动员和精神召唤功能的想象性符号。不难发现,《暗算》人物塑造服膺的原则已经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变成了“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该如何在理论上解释现实主义“当代化”过程中这种新变化,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
如果说典型是要在特殊和一般之间建立联系的话,《暗算》里这些有缺陷的英雄却并不具有典型性,因此无法构成普遍性的启示。无论阿炳、黄依依还是陈二湖,他们都是难得一遇的天才,他们的遭际和命运也是不可复制的。那么,这种以绝对的特殊性为基础的人物的文学意义何在?这是麦家抛给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值得从不同角度去回答。假如抛砖引玉的话,我以为麦家创造的这类新的文学人物并不像很多人理解那样更多从属于消费性。奇人异事在中国传奇和话本中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麦家笔下的“弱的天才”的特殊性中却隐含了某种通过极限而打开可能性的潜能。换言之,虽然很多无法通往“一般”的“特殊”常被视为欠缺意义,但麦家笔下人物的“特殊”却是一种极致的“特殊”,因而是一种在消费性之外另有意义的“特殊”。阿炳和黄依依们以某方面极致的天才而被某种特殊生活所选择,从而使某种极致的人性景观获得了呈现的可能。这也是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书写当代化过程中打开的新路径,其文学经验的理论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提炼和总结。
注释:
[1]李敬泽:《偏执、正果、写作——麦家印象》,《山花》,2003年第5期。
[2][5][6][7]麦家:《〈暗算〉版本说明》,《暗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页,297页,299页,300页。
[3][4]麦家:《形式也是内容》,《暗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285页。
[8][9]麦家:《暗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96页。
[10][11][12][14]麦家:《人生中途》,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 204页,205页,258页,204页。
[13]洪子诚:《不要忘记他是人》,《花城文艺丛刊》,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