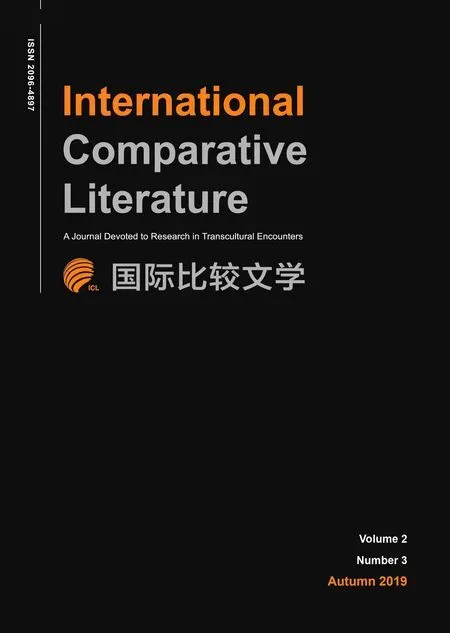尹 锡南:《 印度诗学导论》
王冬青
随着20世纪各种西方理论资源在中国的广泛借用、移植和吸收,中国学术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西方话语审视东方,东方文化与文学必将失真。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学术界还存在另一种倾向,即不理性的民族本位情结,它虽然对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有所倡导和裨益,但此情结若过于浓烈,以致盲目“攘外”,则会将文学研究导向貌似合理的“片面的深刻”。面对“西方中心”和“民族本位”的双重困境,部分学人意识到如果长期囿于中西诗学比较,势必影响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也会制约对其他东方诗学的译介和研究,导致相关领域的研究生态严重失衡。为了促进中国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他们努力挣脱以中西比较为中心的范式,将视野移向中西诗学以外的其他东方诗学。例如,金克木、黄宝生、曹顺庆、王向远和穆宏燕等学者先后在打破“西方中心”或“中西中心”范式方面做出了表率。爱德华·萨义德认为:“考虑东方就无法回避印度”。金克木和黄宝生等学者深谙此理,他们先后译介和研究印度诗学的代表即梵语诗学,其不凡的造诣为中国比较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注入了新的活力。
印度诗学在中国的现代译介和研究肇始于金克木。他曾先后出版了《梵语文学史》(1964年)和《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1980年)。1993年,黄宝生出版了《印度古典诗学》。该书全面介绍了梵语戏剧学和诗学,是中国第一部梵语诗学研究著作。随后,黄宝生出版了《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两卷本,2008年)。该书汇集了《舞论》等十部梵语诗学经典,“皇皇83万字,是印度诗学汉译史上的里程碑”,为梵语诗学研究在中国的垦拓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在著名梵学家季羡林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曹顺庆主编的一部“全面反映东方文论概貌”的《东方文论选》于1996年出版,书中收录了金克木和黄宝生等翻译的八种梵语诗学论著。有论者将该书与王国维《人间词话》引介西方文艺理论的历史功绩相比较,认为它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样,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东方文论选》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文论从‘两点一线’的第二阶段发展到‘三点成面’的第三阶段”,不仅为研究东方文论提供了起跳板,还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除此之外,唐仁虎、刘安武、赵康、白开元、郁龙余、侯传文、邱紫华等学者分别对梵语诗学理论、印地语文论、孟加拉语文论等进行过翻译或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垦拓,中国学界在印度诗学领域已收获甚丰。但较之于学界对中、西诗学的关注,印度诗学研究成果显然过于单薄。在此背景下,尹锡南在印度诗学研究方面的垦拓不可忽视。其最新研究成果《印度诗学导论》(下简称《导论》)不仅对印度诗学的历史源流、发展历程、重要范畴和经典命题做了历时梳理,还以比较视野对印度、中国和西方诗学进行比较,同时还涉及印度诗学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
《导论》的突出特点首先体现在全书结构的体大虑周和内容的条分缕析。该书由七部分构成,主要探讨了以“情论”为代表的十四种重要诗学范畴,以“优秀文学作品使人获得快乐”为代表的十种诗学命题,以“戏剧论”为代表的九种文体论,以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为代表的现当代诗学名家及其理论,印度诗学在中国、东南亚、西方以及南亚各国的传播,以及印度诗学的民族特色等。从内容上看,该书不仅保存了作者所著《印度文论史》的精华,同时以重要范畴和经典命题为核心,对印度诗学进行历史梳理。全书涵盖印度古典梵语诗学和现当代诗学理论,兼具印度诗学的内部文本研究和外部影响研究,是作者周全思虑和宏阔视野的集中体现。在论述具体命题时,作者又条分缕析地呈现了各命题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各诗学家的主要观点。譬如,在探讨 “味论”时,作者首先发掘了“味”这一概念的缘起,并通过探讨“情”与“味”的关系,指出“味”在印度诗学中的突出地位与重要价值。随后,作者从婆摩诃、檀丁和优婆吒等人的味论观出发,重点探讨了楼陀罗吒、新护、波阇及世主的味论观,对“味论”理念的传承和流变做了深入的分析。作者指出,商古迦对洛罗吒的味论持批评态度,而商古迦的观点又受到了新护的老师跋吒·道多的批评。道多所倡导的“感情普遍化”原理又在那耶迦和新护那里得到了充分地发挥。然后,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新护等各诗学理论家有关“味的数量”、“类味”和“主味”等重要观点。接着,作者辟专节重点探讨了梵语诗学中独具特色的“虔诚味论”。通过分析般努达多、鲁波·高斯瓦明以及格维·格尔纳布罗等的虔诚味论观,作者认为虔诚味论对梵语诗学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壮大了味论诗学的生命力,但同时又使晚期味论彻底走向神秘化,使印度古典诗学沾染了神秘的宗教意蕴。同样,在论述梵语诗学的另一重要流派庄严论时,作者首先对广义和狭义的“庄严”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从萌芽期、早期发展和中后期发展三个阶段探讨了庄严论的历史流变,并对不同时期各个诗学家的庄严论进行详细梳理。最后,作者不仅对庄严的外延和内涵做了深入挖掘,还指出“庄严论不仅具有比较诗学研究价值,也具有文学批评的工具价值”。这种系统而深入的梳理,可让读者充分把握各诗学范畴与重要命题的发展流变。毋庸置疑,《导论》的结构布局和细致梳理,为促进印度诗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导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中西中心”研究范式的突破和超越。这与作者所倡导的“三维世界”跨文化研究理念一脉相承。作者在论及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时曾指出,“就今后很长时期内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而言,应该设立一个跨文化研究的崭新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三维世界’的理想建构”。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西独大”的痼疾,作者认为“中西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文学关系研究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中’和‘西’两点一线式的研究,如果再加上西方和印度、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甚至加上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印度和日本等相互之间文学关系的清理,我们就会有无数个文学关系方面的‘三维世界’,这就将乐黛云先生的‘跨文化’体现得更加名副其实”。毫无疑问,《导论》是对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文本回应,也是推动中国比较诗学“从中西两极转向整体关注”的实践。具体来说,作者在《导论》中以印度诗学的基本话语体系为主,对印度、中国、西方诗学的基本原理展开了异同比较。在论及“戏剧再现三界的一切情况”的模仿说时,作者将婆罗多的《舞论》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行比较,认为二者的模仿说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殊途同归的美学效果”。就二者的内涵而言,作者认为婆罗多独特的诗学命题比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因为“婆罗多不仅主张模仿现象世界的大宇宙,还主张模仿内心世界的小宇宙”。通过对比,作者进一步指出“亚氏的模仿论重点在于主张作品中艺术的再现和客观的叙事,中国的‘物感说’强调情志的表现和感情的抒发,婆罗多的模仿论则重在戏剧表演中情味的唤起和超越世界的构筑”。同样,在探讨“戏剧情节”时,作者通过比较《诗学》和《舞论》,指出“对戏剧情节重要性的强调,是东、西方戏剧理论的共同特点,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思维差异”。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论与悲剧密不可分,“情节是悲剧的目的,情节第一”;婆罗多认为“情节是戏剧的身体,味乃戏剧的灵魂,味重于情节”;李渔和孔尚任等则强调戏剧情节的传奇特性。客观地看,《导论》一书有机地借鉴和参考了作者所著《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并将其重要元素有机地融入自身。《导论》有意识地加入了中国诗学的第三元素。通过三方比较,《导论》从实质上建构了印度、西方和中国诗学比较的“三维世界”。这种以中国、印度和西方诗学为主展开的三维比较在目前尚不多见。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主要以印度诗学为主,涉猎西方诗学和中国诗学的内容并不多,但这种比较视野对于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而言,是突破和超越“中西中心”研究范式的有益尝试。第三元素的加入,不仅能展开东西方多元诗学间的深层对话,让晦涩艰深的诗学命题更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还有益于推动中国比较诗学走向整体诗学研究。同时,该书不拘泥于印度、西方和中国诗学的三方比较,还引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模式,探讨了印度诗学在中国、东南亚、西方及南亚各国的传播。在论及印度古典诗学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时,作者不仅梳理了其在中国汉民族文化中的译介、研究和批评运用,还对梵语诗学经典《诗镜》与中国藏族、蒙古族文论的历史关联进行了考察。这也体现了作者突破“中西中心”范式,走向多元关注的文化视野。总之,《导论》的出版无疑将促进中国的印度诗学和比较诗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导论》是作者浸淫印度诗学研究多年的成果,体现了作者在印度诗学研究领域的锐意创新。客观地看,较之于国内已有的印度诗学研究著作,该书在结构布局、内容选择和论述视角等很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首先,该书借鉴了黄宝生等前辈学者对印度古典诗学的研究成果,并将研究视野延伸到印度现当代诗学领域。在《印度古典诗学》中,黄宝生先生以梵语诗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认为“所谓印度文学理论,也主要是指梵语文学理论”。他还认同印度学者S.达耶古德的观点,认为“梵语诗学代表未受到外来理论影响的、真正的印度艺术观,而现代印度各种语言文学理论主要是对梵语诗学或西方文艺理论的改造”。很明显,《导论》没有囿于梵语诗学研究,而是将印度现当代文艺理论纳入研究范畴,并辟专章介绍包括泰戈尔在内的众多现当代诗学家及其理论。从作者的论述中,读者不仅能体察印度古典诗学的现代流变,也能领悟西方现代诗学对印度诗学的影响。在探讨印度古典诗学时,作者不限于对“味论”“庄严论”及“曲语论”等传统话语进行阐释,而是进一步提炼出“诗的灵魂是风格”等经典命题和“图案诗论”等重要文体并逐一论述。这种以命题探讨模式为主的研究方法,不仅有益于深入发掘诗学经典的意义与内涵,还能促进印度诗学研究的纵深发展。作者还辟专节论述了研究印度诗学的基本方法。
作为一部“导论”性质的论著,《导论》亦存在可以完善的空间。例如,《印度古典诗学》一书为了便于读者把握原意,为主要术语的译名附录梵语原文,而《导论》在这方面未能尽如人意,这给读者理解和把握术语的原意提出了挑战。
综上所述,《导论》的出版对于促进中国比较诗学和印度诗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在印度诗学研究领域的垦拓意识和锐意创新,值得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