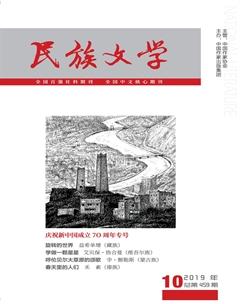如椽之笔写彩云
李传锋
我对云南兄弟民族生活的了解始于电影《边寨烽火》和《芦笙恋歌》,还有一部是《山间铃响马帮来》,那时候,我不懂写作,只对奇丽的风光和新鲜的故事感兴趣,对作者不怎么注意。大学毕业之后,在《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我才读到彭荆风先生的文学作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作家协会创刊《民族文学》,在首次聘任的编委名单中有一名汉族编委,就是彭荆风。关心和支持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汉族作家成千上万,彭先生竟能成为大刊编委中的唯一,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彭荆风先生祖籍江西萍乡,出生于鄱阳湖畔,因为家贫,少时书读得不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有幸参军入伍,随后进入云南边疆,从此扎根彩云之南,亲身参与了云南少数民族翻天覆地变化的全过程,长期关注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艺术创作,写出了大量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学作品。
听说彭荆风先生曾被错划右派,“十年动乱”中还坐过牢,“文革”后复出,他写的第一篇作品却是《驿路梨花》。故事发生在哀牢山哈尼族山寨附近,在那山最高处,在那云雾深处,哈尼族人建成海市蜃楼般令人神往的山寨。瑰丽的大山,月亮,梨树,小茅屋,还有纯朴善良乐于奉献的小梨花……《驿路梨花》是作者在新的时期对亲历生活的重构,是对哈尼族人深情的怀念。这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好作品,文笔流淌着浓浓的爱意。当年《光明日报》全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快就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我从1981年进北京文学讲习所读书开始,也热心投身新时期民族文学事业的复兴,将自己的业余创作专注于民族生活,坚持将自己的好作品给《民族文学》发表。中国作协和《民族文学》多次组织我们到祖国各地特别是边疆地区采风和参加笔会,我也就有机会多次见到心仪已久的彭荆风先生。我到过云南很多地方,都是坐着车,或是坐飞机去的,而彭荆风先生当年是靠两条腿走去的,我很难想见和体会到那种困苦和艰辛,也就越发对老一辈革命作家产生出崇敬与钦佩。我有幸遇到两位我国军事文学的领军人物,一个是王愿坚先生,他是我在文讲所时的写作导师,所以,后来见了彭荆风先生,自然就产生一种亲近感。彭先生一身戎装,那宽厚和善的面容,儒雅而刚毅的神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身上没有那种社会上常见的文人的自由散漫和不修边幅,浑身透出一种军人的严肃和认真。当他和你交谈时,又是那样的热情奔放,平易近人。
那几年,是彭荆风先生复出之后的创作喷发期,一年有多部作品由全国各地报刊和出版社推出。1987年,他的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获全国大奖。我那时正主编着大型通俗文学期刊《今古传奇》,这本刊物深受大众欢迎,期发行量曾经突破270万册,但我们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有个“大人物”竟然在报章上说“通俗文学即是庸俗文学”,有的文学大伽也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态度。我把这些委屈说给他听,荆风先生认真听了,他认为,“通俗”未毕不严肃,只要是人民群众喜欢的刊物,我们就有责任把它办得更好。荆风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让我更坚定了办好通俗文学期刊的决心。
1994年6月,今古传奇杂志社和人民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长江三峡文学笔会”,荆风先生应邀。大队人马从武汉坐汽车到荆州,到宜昌,坐船去小三峡,进入有些河段,得分几拨坐弯豆角船往上游拖,我至今保留有一张照片,在小三峡那美丽的河滩上,我陪荆风先生在卵石上漫步。彭先生说,这里的山水风光和云南很不一样,我们自然而然就谈到了美丽的云南。
彭先生深情地说:“我1950年春天随同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在红土高原上生活,至今近50年了。几十年来,我多数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和战斗。在红河、怒江、澜沧江流域,那里地势险峻,人们性格淳朴,风俗特异,在那一时期,一般人难以经历的战斗生活和民族工作,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作为一个作家,我有责任,把边地人民永远告别旧时代,热情拥抱新生活的过程,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荆风先生的许多作品,如《边寨亲人》《卡瓦部落的火把》《驿路梨花》,长篇小说《鹿衔草》以及与人合作的几个电影文学剧本,都真实的表达了作者对云南边地的美好感情。
一谈到云南边疆,荆风先生满脸豪情,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云南的作家当中,我是第一个进入滇东北的乌蒙山系彝族人地区,第一个进入澜沧江以南拉祜族人地区,第一个进入还处于原始部落末期的佤族人地区。” 我静静地听着,彭先生当时是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参加民族工作组的作家,这几个“第一”真是人生难得的经历啊。当年,那可是深入不毛之地,每天行走在无尽深山里,山高路险,经常走几十里路难见人烟,而且野兽时常在附近山林间出没,还有土匪和敌对势力,他们不仅要背上背包,背上枪支,夜里经常找不到村寨,不得不露宿于山林间,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我从内心里说,是时代创造了独特的生活,是生活创造了伟大作品,是苦难造就了伟大作家,是云南边地成就了军旅作家彭荆风。三峡笔会不久,彭老给我寄来了他的长篇小说新作《绿月亮》签名本作为纪念。这部小说,以“文革”动乱为背景,写的是几个社会渣滓——色狼、小偷、杀人犯。视角独特,情节复杂,耐人寻味。
2005年秋,“十一”过后,彭先生在女儿彭鸽子的陪伴下来到武汉我的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参加“第二届全国文学教育高峰论坛”,我闻讯去看望他们父女,在他的房间谈了很久很久。彭老是这次论坛的主角,研讨的就是彭老那篇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短篇小说《驿路梨花》。这个论坛实行“一课三讲”,彭先生面对几千名中学语文教师和一部分学生讲《驿路梨花》的写作和思考,讲他跋涉过的那些高山大川,讲他入住过的那些简陋的村寨,讲他结交过的少数民族朋友,讲他难以忘怀的许多旧事,讲他如何将真实生活进行重构,将情感如何赋予形象。教师代表就讲他们如何给学生上好这堂课的体会,学生代表就讲他们读了这篇课文的感受。这次论坛别开生面,各方反映都很好。
1999年春天,云南昆明成功举办了20世纪末全球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园艺博览会,我们此时在昆明举办活动,就去参观世博园。我跟着荆风先生在花海中漫步,我们又谈到了文学。我知道他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监狱待了七年,打倒“四人帮”后,本来有许多痛苦的遭遇可以写,我就问他:“怎么没见你写伤痕文学?这东西很走红的。”他想了想,说:“我要书写我最关注的事。”先生为什么不急于写那一段自己的伤痕呢?什么才是他“最关注的事”?我事后才明白,先生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建,他已经跳出了个人的恩怨得失,所以他把他的全部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描绘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了。他给我说,他正在酝酿几部长篇纪实文学,也就是此后推出的《解放大西南》《滇缅铁路祭》《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他女儿彭鸽子伴陪着老人跋山涉水,故地采风,重蹈古战场,到处搜集资料。这几部作品的成功面世,弥补了中国军队战争历史的一处空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彭先生在云南十分关心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我的很多云南朋友时常说到他。每当春节,我们都互有问候。2011年夏天,我收到了彭先生新出的短篇小说集《驿路梨花》,他把我这个忘年交小弟称之为“老友”。我又认真欣赏了他的这本小说集。彭先生是中国文坛一棵常青树,耄耋之年,他仍然新作不断。当全国读者和报章正热议着他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时,多雨的 7月,彭鸽子给我发来讣告,90高龄的彭老溘然仙逝。彭先生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活积累,肯定还有很多珍贵素材没来得及写出,精彩描绘少数民族生活的《太阳升起》就成了彭先生留给读者最后的奉献。
彭荆风先生是文坛骁将,是自学成才的将军作家,他的一生深爱着祖国和人民,深爱着生活和文学,在彩云之南的民族地區挥动着如椽之笔,给我们留下了近千万字的著作,他的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纪实文学、电影剧本、话剧剧本、文学评论都写得很好,其中很多部作品奇丽而壮美,实至名归获得了全国大奖。
在我的心目中,一个汉族作家,扎根边地,将自己化作多民族中的一员,同呼吸,共命运,将自己的全部青春和才华,责任和担当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奉献给了少数民族地区,而且不离不弃,无怨无悔,终其一生,其人格,其形象,在我心中是无比高大,无比尊崇的。
彭荆风先生是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实践者和支持者,也是西南边地民族文学和军事文学的开拓者和见证人。他是我可亲、可敬的汉族老大哥、作家朋友和老师。
在荆风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谨以此文怀念他。
责任编辑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