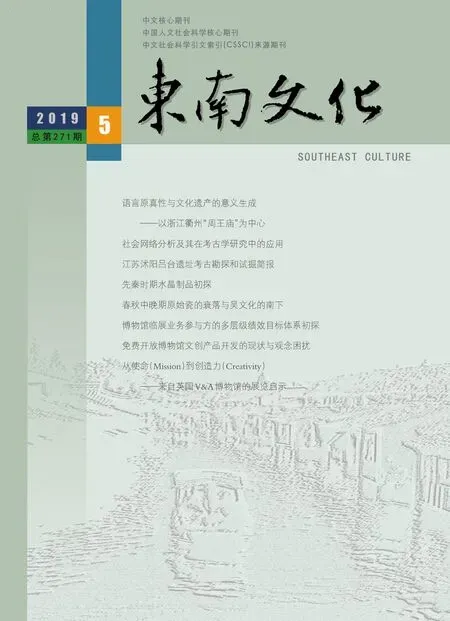春秋中晚期原始瓷的衰落与吴文化的南下
郑建明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春秋中晚期的原始瓷器类单一、器形简单,以日用的盅式碗占绝大多数,少量盘与罐类器物,少见或基本不见礼器类器物,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衰退现象。这一现象与吴文化南下扩张进入太湖流域原越文化传统分布区,从而造成越文化往南退缩有直接的关系。
先秦时期原始瓷滥觞于夏、成熟于商、发展于西周、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从整体发展来看,基本呈螺旋形上升,有高潮,也有低谷,直到战国早期达到鼎盛。原始瓷的发展,基本有三个高峰: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战国早中期。西周中期与春秋中晚期是相对衰落时期;后两个高峰之间的春秋中晚期,器类单一、器形简单,与前后两个高峰相比反差更加明显。这一现象与吴文化的南下扩张进入原来太湖流域的越文化分布区,从而造成越文化往南退缩有直接的关系。
一、西周末期以来先秦时期原始瓷发展概况
西周末期以来,特别是春秋至战国早期原始瓷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从产品的类型来看,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与战国早中期是原始瓷发展的两大高峰,而这两大高峰之间的春秋中晚期,则明显衰落;二是从窑址的分布来看,春秋中晚期,在原始瓷烧造的核心分布区浙江德清龙山地区,窑址从原来相对交通便利、更接近于平原地区的丘陵向更深、更高的山区转移,并且首次从钱塘江北岸的东苕溪流域扩张到了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地区。
(一)产品类型所反映的东周时期原始瓷发展脉络
1.窑址材料
西周末期至战国早期原始瓷产品的基本类型与面貌,集中体现在浙江德清火烧山与亭子桥两处窑址中,这两处窑址均于2007年经过大规模地发掘,是这一时期非常典型的窑址。
火烧山窑址始烧于西周末期,延及春秋晚期,共分成三个区。每个区在烧造时代、器物种类与质量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别[1]。
Ⅰ区时代最早,从西周末期延续至春秋早中期,以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最为兴盛:产品种类丰富、器形复杂、装饰繁缛、胎釉质量较好,仿青铜礼器产品及繁缛的纹饰主要出现于此区。器形以宽沿浅弧腹的碗为主,不仅包括盂、碟、罐、盘、钵等日用器物,亦包括鼎(图一︰1)、簋(图一︰2)、卣等礼器类器物。后者不仅器形较大、装饰复杂、胎釉质量明显更佳,而且通常每种器物有多种不同的器形。卣不仅有筒型卣(图一︰3)与垂腹卣(图一︰4)两大类,每种卣又器形大小、腹部鼓凸不一:筒型卣腹部有直筒型和微鼓腹筒型等;垂腹卣有最大腹径近中部偏下的,也有最大腹径接近于器底的。仿青铜礼器的器物腹部往往装饰有繁缛的纹饰,纹样复杂多变,主要有勾连云纹、细乱云纹、双勾线S形、云雷纹、对称弧形纹等。纹饰个体较大、风格粗放、排列杂乱,且常见重叠拍印的现象。这一时期的釉色普遍较深,呈酱褐色或青褐色,流釉、凝釉明显,但釉层较厚、玻璃质感强,基本通体施釉。
Ⅱ区自春秋早期后段开始,一直延续自春秋晚期中段。产品单一,以直腹的盅式碗占绝对的主流:春秋中期主要是方唇、浅直腹、小平底的盅式碗(图一︰5);春秋晚期则碗的腹部加深并呈子母口状,带盖,小平底(图一︰6)。少量的盘、罐类器物。仿青铜礼器产品仅见少量的卣,呈微鼓腹的直筒型(图一︰8)。纹饰种类大幅度下降,仅见对称弧形纹一种,并且纹饰个体小而细密,排列整齐规则而拘谨,早期杂乱、豪放的风格完全不见。釉色青黄、釉层薄、施釉均匀、玻璃质感较强。
Ⅲ区仅有春秋晚期后段一期,器类更为单一,仅有尖圆唇盅式碗一种(图一︰7)。胎、釉质量与春秋中期的盅式碗基本一致。
亭子桥窑址位于火烧山窑址以东约2公里处,是一处战国早期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址。出土大量的原始瓷产品,可分成日用器、仿青铜礼器与乐器三大类[2]。
日用器以碗为主,其他还有杯、盅、钵、碟、盘、盂、盒等。虽然种类不多,但造型比较丰富,每种器物通常有多种不同的造型,如碗有直口或敞口浅弧腹碗、弧敛口深腹碗、直口盅式碗等,且大小不一。
仿青铜礼器数量较多,器形有盆形鼎、盂形鼎(图二︰1)、豆、平底盆、三足盆、平底盘、圈足盘、三足盘、提梁壶(图二︰2)、提梁盉、镂孔长颈瓶、尊(图二︰3)、簋、罍、罐(图二︰4)、壶、鉴(图二︰5)、匜(图二︰6)、镇等。此类器物一般器形较大、造型规整、工艺精巧,且胎釉质量较佳,通常装饰有各种纹饰,如堆贴常见于青铜器上的各种模印铺首(图二︰7)、戳印各种云雷纹(图二︰8)、修刮粗细深浅不一的瓦楞纹等。
乐器数量较少,有甬钟、錞于、句鑃、三足缶和器座(图二︰9)。器形上以模仿同类实用青铜器为主,并且器物均装饰精细的云雷纹等纹饰。制作精良、胎釉质量极佳。
以上窑址材料清晰地勾勒出西周末期至战国早期原始瓷的发展脉络,其中春秋中晚期是一个明显的发展低谷:产品种类少、造型简单、器形较小、装饰极少,并且基本为日用器而少见礼器类产品。
2.墓葬材料
太湖南岸地区西周末至春秋早期的大型墓葬中,随葬的原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以各种类型的礼器为主;而春秋中晚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数量则明显减少,种类单一,以碗占绝大多数,基本不见礼器类产品。
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德清地区典型的墓葬有新市皇坟堆与三合塔山。
皇坟堆是一个直径近50、高约4米的大土墩,墓葬已被毁,结构、大小不清,但采集回来的原始瓷是目前已知同一时期墓葬中数量最多、规格最高的。有筒型卣11、垂腹卣1、尊7、鼎3、盂1、碗4件。这批器物胎釉质量高超,除碗外,多数器物装饰有各种纹饰,作为礼器的卣与尊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多样(封三︰1)[3]。
塔山墓葬位于塔山之巅,墓(不含原封土)总长10.2、宽5.3、高0.98米。墓室净长8.5、宽1.8、高0.98米。整个墓用二十余块大石砌筑,仅南端开口,并用小石块封闭。在墓北端外壁两侧,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堆筑护坡,墓的上部并未加条石封盖。共收缴出土器物34件,均为原始青瓷器,有鼎7、尊2、卣1、筒型卣1、罐4、盂8、羊角形把杯3、碗7、盘1件[4]。
春秋中晚期的墓葬以德清小紫山D1为代表。小紫山是先秦时期大型的土墩墓群,其中D1位于小紫山主峰之巅,墓葬坐东朝西,用大块石块砌筑墓室,外侧用大小不一的石块堆筑护坡,墓上用大块石块封盖(封三︰3)。墓葬西端后壁被破坏,墓室残长16、宽1.6、高2.3米,整个封土墩残长17.4、宽12.8、高3.1米。但仅出土了10件原始瓷,包括碗7、碟2、盂1件,均为小型的日用器,不见纹饰(封三︰2)。时代为春秋中期早段[5]。
小紫山D1的规模远大于塔山墓葬,用大块的石块封盖,且位于整个墓地的主峰,非常显眼,因此等级上明显较塔山墓葬为高,但出土的随葬品却完全没法与之相比,较之皇坟堆则相差更远。这反映了原始瓷生产的迅速衰落过程。
到了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葬中普遍随葬大量的原始瓷,而且等级越高,数量越多、档次越高。如江苏无锡邱承墩越国贵族墓,共随葬原始瓷581件,主要为礼器和乐器[6]。
因此无论是从窑址还是墓葬出土的原始瓷材料来看,西周末期到战国早中期之间,原始瓷发展在春秋中晚期有一个明显的衰落过程。
(二)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分布的变化
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的原始瓷窑址,目前主要分布于今德清洛(舍)武(康)线的沿线,包括龙山村委、后山、火烧山、下南山、青龙山、南塘头等一众窑址[7],这一线的北边是东西向的莫干山余脉龙山山脉,往西逐渐进入莫干山,而往东、往南则逐渐进入了河网地区。依山傍水,水上交通相当便利,许多窑址附近至今仍有河道,是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的核心分布区。
进入春秋中晚期,窑址数量有所增加,但多数窑址向西、北方向的更高、更深的山区转移,这在整个先秦时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部分窑址几乎接近于非常不利于烧窑的近山顶处,如跳板山窑址,即几乎接近于跳板山的山顶(封三︰4);同时,白洋坞、响堂坞、泉源坞、玉树岭、夏家坞等一众窑址均远离窑址群的核心分布区[8]。
同时,这一时期,钱塘江南岸、邻近越国政治中心绍兴的浦阳江下游地区开始形成新的窑址群,包括茅湾里窑址群、泥桥头窑址群等[9]。
而进入战国时期,窑业的生产中心又重新向原来的核心分布区火烧山、亭子桥一带聚集。
因此,在春秋中晚期原始瓷生产地点有因某种外来的压力向传统核心区之外转移的现象。
二、考古所见西周中期以来吴文化的南下
从西周末期以来整个东周时期的原始瓷发展脉络来看,春秋中晚期原始瓷的衰落是相当明显的,不仅器物种类少,器形小而单一,装饰亦极少见,制作工艺简单。这种衰落可能与吴、越文化(或吴、越两国)西周早期以来的相争及吴文化(或吴国)的南下密切相关。
吴文化的南迁,首先表现在其政治中心的逐步南迁上。
1.吴文化的早期中心——宁镇地区
吴越两国地域相近,文化相通,然而在政治上则势同水火,“夫差将欲听与之成。子胥谏曰:‘不可!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必无及已。’”[10]“(子胥)乃进谏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辞伪诈而贪齐,破齐譬由磐石之田,无立其苗也。愿王释齐而前越,不然悔之无及。’”“今齐陵迟千里之外,更历楚赵之界,齐为疾其疥耳;越之为病,乃心腹也。不发则伤,动则有死。愿大王定越而后图齐。”[11]
当然,这描述的是春秋吴越争霸时的情形,此时二者更是有你无我。实际上吴越两国的冲突,远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之际即已开始,这与吴文化扩张并进而南下深入传统越文化区直接相关。
吴文化或吴国的早期政治中心,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可能在长江沿岸的宁镇地区(包括皖东南地区)一带。在考古学上,最主要的证据是这一地区大量高等级墓葬的发现。
宁镇地区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属低山丘陵地区,区内东部的茅山山脉是长江流域与太湖流域的分水岭,山脉西侧水系大部分经秦淮河注入长江,坡麓地带多为岗阜地形,分布着大量的土墩墓,而东侧土墩墓则较少。茅山山脉不仅是长江与太湖流域的地理分水岭,同时也是吴越两文化的分界线:以西以北地区是吴文化分布区,以东以南地区是越文化分布区。吴、越文化的差别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葬俗上,吴文化虽然也以土墩墓为葬俗,但出现时间比较晚,与越文化地区从夏商时期出现土墩墓相比,吴文化地区土墩墓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显然是受越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葬俗,此外,吴文化因与中原地区较为接近,它同时接受了中原葬俗上的一些因素,如挖坑埋葬等,这种挖坑土墩墓在越文化地区较为少见,后者更多的是平地掩埋。其次,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越文化土墩墓中至今未见青铜器出土,而大量使用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少量为夹砂陶与泥质软陶,原始瓷的使用相当普遍且比例极高,许多墓葬中仅见原始瓷而不见其他器物,因此使用原始瓷与印纹硬陶而不使用青铜器随葬是越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吴文化则与之不同,墓葬中除使用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外,亦见有青铜器随葬,尤其是大型墓葬中,青铜器不仅数量多,且质量亦极高,而吴文化使用原始瓷的普遍性远不及越文化,墓葬中原始瓷比例低、器物种类与数量均相对较少。第三,使用器物上,两者的器物群亦差别比较大,尤其显著的是炊器的差别上,吴文化大量使用鬲,而越文化则基本不见鬲而主要使用鼎。
宁镇地区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不仅与太湖地区迥然有别,且集中分布着大量的土墩墓、遗址等。据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遥感调查数据,仅镇江地区就分布着1400多座土墩墓[12]。在江苏镇江丹徒的大港—谏壁的长江沿岸集中分布着一大批高等级的墓葬,主要有烟墩山、母子墩、四脚墩、磨盘墩、粮山、北家山、青龙山、北山顶、双墩等[13],这些墓葬一般修建在山顶,一山一墩,一墩一墓,有高大的封土,随葬品丰富,包含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显然非一般墓葬可比。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带是吴国的王陵区[14]。
长江之滨的丘陵坡地,地势普遍较低,青龙山、乔木山、烟墩山等,高度一般不超过四十米。除大型墓葬外,这一带还分布着很多大规模的台形遗址。同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遥感调查数据,镇江地区大型台形遗址共有70多处,并且沿长江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如高资河所在的河谷地区,东西仅宽1~2、南北长8公里的范围内,就有遗址6处,在镇江丹徒以东的丹徒镇至大港、丁岗一带,平均每3.5公里就有一处台形遗址,其密度几乎接近于现代村庄[15]。因此镇江一带是宁镇地区台形遗址的中心分布区。
台形遗址一般有上万平方米,大的如丹徒丁岗断山墩遗址[16],达两万平方米以上,除发现印纹硬陶、原始瓷外,有的遗址中还发现青铜器冶铸遗迹[17],此类大型的、能冶铸青铜器的聚落,在当时绝非普通民众的村落,而应该具有中心聚落的地位。
再来看吴国青铜器的分布,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吴文化地区共出土青铜器2000多件,其中大件容器600多件,主要集中在宁镇地区;苏锡地区仅发现130多件,其中容器仅19件[18]。从时代上看,宁镇地区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西周至春秋早期,而苏锡地区发现的130多件青铜器多是春秋中晚期器物[19]。
因此从遗址、土墩墓的分布及青铜器出土情况来看,镇江尤其是丹徒沿长江的大港、丁岗一带,显然是一个政治中心,应该就是吴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地。但具体的都城位置仍待日后考古发现。
2.吴文化南下的桥头堡——葛城与淹城
葛城遗址位于江苏镇江丹阳珥陵镇一土岗上。古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向。南北长约200、东西宽约180米,现残存城墙最宽处24米,最高处距地面约7米。城内四面城墙均有城门,城门宽约6米左右。四面城墙均存在早中晚三期,各期城墙相互之间有叠压或沿用关系。早、中、晚各期城墙均有对应的两道护城濠沟,河道宽10~20、深2~3米。葛城始建于西周中晚期,废弃于春秋末期,曾连续使用数百年,是现在已发现的吴国城址中最早的[20]。
淹城遗址位于江苏常州武进区,现存城址由外、中、内三城组成。外城为一不规则圆形;中城呈方形,处于外城东北部;内城在中城中部偏北,呈不规则的方形,周长不足500米。三城墙外均有宽阔的护城河。
从淹城一带出土的遗物主要是原始瓷与印纹硬陶来看,其时代主要是春秋早期为主,延续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的遗物则几乎不见[21]。
葛城与淹城两城址具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城的规模均非常小,葛城仅三万多平方米,而淹城更小,两城规模根本无法承担宫城等职能,因此不太可能是一处大型政治中心;二是防卫相当严密,葛城城墙外有三重护城河,从目前的考古学证据来看,其中至少两重与城墙相关联,而淹城有三重城墙,且每重城墙外均有护城河,河面较为开阔,城墙至今高耸;三是时代均为西周中期以后,其中靠近宁镇地区的葛城略早,更南边的淹城略晚。
从两城的规模及其严密的防守来看,它们很可能是吴文化南下的前沿和军事中心。两城这种严密防守的筑城法当与其时该地区不稳定的形势密切相关。大概从西周中期开始,吴文化开始自宁镇地区南下开疆拓土,与环太湖地区的越文化形成冲突,从而爆发激烈的战争,作为深入越文化腹地的外来者,早期显然需要多重城墙与濠沟进行自我保护。葛城城墙经过多次损毁与重筑,显然是这种激烈冲突的反映。吴文化在西周中期的首次南下即遭遇越文化的激烈抵抗并在此进行了多次拉锯,葛城多次易手,直至春秋早期稳定下来。
稳定下来的吴文化则继续南下,来到现在的淹城地区并构筑新的前沿堡垒。这一地区处于越文化的北部边缘而未深入到太湖腹地,因此淹城的功能应该与葛城基本一致,主要是巩固葛城的成果,并进一步形成更大而纵深的对越文化前沿,因此其安全形势仍比较严峻,需要三城三池的防守。但可能较初次南下的葛城时期略缓和,因为淹城虽然仍防卫严密,但不见葛城几毁几建的情况,应该是这一时期局面已经稳定,摆脱了前一时期在此地直接接触与拉锯的短兵相接态势,淹城很可能已经是吴文化南下的军事指挥中心了。
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春秋中期。
3.吴文化占据太湖流域——阖闾城与吴大城
在淹城以南,太湖以北的地区,有两座城址值得重视,它们可能是吴文化进一步南下的重要证据,这就是常州与无锡之间的锡常古城,传统上称之为阖闾城。还有一处在苏州西郊,近几年来新发现的一处新城址,称为木渎古城。
锡常古城位于江苏常州市雪堰桥镇与无锡市胡埭镇之间,东临太湖,北靠仆射山、胥山、虾笼山等。古城有外城和内城。外城即大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100、南北宽约1400米,面积约2.94平方公里,外有保存完好的城壕。内城分为东、西两小城,两城东西长约1300、南北宽约500米,面积约0.65平方公里。考古钻探结果表明古城的年代上限晚于春秋中期,下限早于汉代,大致为春秋晚期。周边龙山山脉的山顶和山脊上分布着蜿蜒起伏的石城,年代亦为春秋晚期。古城遗址的范围应包括龙山石城。发掘者认为此城的规模庞大,与春秋时期列国的都城相似,应该是吴国的都城,而时代在春秋晚期[22]。
木渎古城位于苏州西部以木渎为中心的山间平地上,包括大城、小城、郭城及城址内外房屋台基等遗迹。大城分布于由灵岩山、大焦山、五峰山、砚台山、穹窿山、香山、胥山、尧峰山、七子山、姑苏山等山脉所围成的区间内,东西向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两道城墙之间的距离为6728米。
大城内有小城,外有郭城,在郭城、大城及小城内,遍布大小不等的方形或长方形台地。围绕郭城,发现两座小城址——千年寺古城址和长头古城址,面积较小,地处险要之地,对郭城起一定的护卫作用。古城墙解剖出土的几何形印纹硬陶片及残石器,都具有春秋晚期风格,古城址的营造年代应在春秋晚期[23]。
城外还发现包括土墩墓、遗址等在内的大量遗迹存在。周边上方山、七子山、观音山、五峰山、天平山、真山、胥山、横山等山峰、山脊上,存在大量春秋时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许多墓葬等级极高,如真山、树山、阳宝山、鸡笼山等地大墓等。木渎古城如此宏大的规模、大小城及外郭的结构、城周边大量的高等级墓葬和玉器窖藏的存在,表明这是一个规格极高的政治中心,是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24]。
从后世文献资料来看,吴国都城的变迁历史大致如下。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太伯、仲雍“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亦,吴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
《史记·吴太伯世家》司马贞《索隐》引《系本》(即《世本》):“吴孰哉居蕃离,孰姑徙句吴。”宋忠注:“孰哉,仲雍字……孰姑,寿梦也。”
《史记·吴太伯世家》裴骃《集解》引《世本》,张守节《正义》:“太伯居梅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吴国的都城有两次变迁,先后分布于三个地区。第一个地区是商末至西周早期太伯与仲雍时的梅里也即蕃离或番丽;第一次变迁大约发生在寿梦或诸樊时期,形成吴国都城的第二个地区,即吴或句吴;第二次变迁在春秋末期的吴王阖闾时期,也即伍子胥筑的阖闾城,也称吴大城,即第三个地区。
关于蕃离的地望,历来争议比较大,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在镇江的丹徒一带[25]。撇开“太伯奔吴”的传说性成份,这种观点是经得起几十年来考古材料的检验的。
寿梦或诸樊所迁的吴或句吴的地望,文献上同样无解。先看地望比较明确的阖闾城。
阖闾城又称为吴越城或吴大城,文献主要见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然而无论是《越绝书》还是《吴越春秋》,均没有明确指出吴大城的具体方位。将吴大城与苏州城相关联,是在唐以后,且其过程与梅里在无锡的观点一样,也是一个层累叠造的过程。
新发现的木渎古城,使阖闾城与现代苏州城不在同一地的观点在考古学上得到印证[26];之后的正式考古工作,更是直接提出该城址的性质“为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27],基本肯定其就是春秋晚期吴国都城阖闾城了。
阖闾城的位置确定后,再来讨论寿梦或诸樊所迁的都城。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寿梦城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从吴国自宁镇地区逐步向太湖地区南下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位置上寿梦城应该介于淹城与木渎古城之间,并且已进入到太湖地区;其次,这是吴国的一次迁都行为,该城具有都城性质,同时按史料记载,吴国自寿梦时始大,此时吴国国力相对强大,因此该城应该具有春秋列国时期都城的规模,而与淹城等纯军事性质的城堡具有根本性的差别;再次,时代上,寿梦在位时间进入了春秋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时期。
位于常州与无锡之间的锡常古城几乎完全满足以上诸条件。因此这个所谓的“阖闾城”,其实应当是春秋中晚期的寿梦所筑之城。这是吴国自宁镇地区首次南迁进入到太湖地区,也标志着吴国正式开始占有太湖北岸地区。
这样,通过对苏南一系列城址的分布及其性质的分析,吴国南下的路线基本清晰可见。
西周早期,吴国的政治中心在镇江的丹徒一带,其中葛城是其防御越国的前沿阵地。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吴国开始向南边的太湖流域扩展,在武进淹城建立了桥头堡,作为南下的前沿军事指挥中心。由于已经进入越国的势力范围,吴、越面对面短兵相接,激烈相争。危急的形势使淹城出现了三墙三濠的结构用以拱卫其安全。这一时期吴国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还达不到对太湖地区的真正经营,因此其政治中心应该仍在镇江地区。
经过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多年战争,春秋中晚期,形势已朝着对吴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整个太湖北岸逐渐为吴国掌控,越国退居到太湖以南地区。紧张的安全形势解决后,经营并巩固这一地区成为吴国下一步的任务。同时,由于吴楚在淮河流域的纷争,相比新占领的太湖地区,宁镇地区的局势反而比较紧张,于是在寿梦时期吴国进行了迁都,政治中心从宁镇地区迁移到了太湖的北岸。虽然吴在与楚、越的战争中频频获胜,但其紧张的局势并未完全解决。寿梦城防御设施极其严密,太湖及其周边的山脉等天险亦是城市防御重要构成,因此这一时期城址选在了太湖边上。阖闾城与春秋列国都城相比,几乎同具规模而略小,也是符合吴国初兴历史的。
进入到春秋末期,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吴终于攻入楚都郢,楚国的威胁暂时解除,整个淮河流域落入吴国之手;而南边越国尚无力与之争锋,“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28]。越国也仅能在吴国伐楚,后防空虚之时作小规模攻击而已,因此此时吴国安全形势空前大好,俨然成为一个东方大国和春秋晚期霸主。而此时都城寿梦城已嫌狭小,同时这一时期的太湖南岸部分地区也已纳入吴国的版图,疆域进一步扩大,因此建造规模更大、位置更南的新都城,成了吴国一项新的任务。木渎古城——即真正的阖闾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该城的规模、布局、位置等都符合春秋晚期吴国的霸主地位。其防卫设施也不如寿梦城严密,更不用说与淹城与葛城相比了,说明其建城之初安全形势较寿梦时期要好很多。在这里,吴国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三、春秋中晚期原始瓷衰落的原因
越国或越文化最大的特色,是使用原始瓷而非青铜器作为礼器,因此原始瓷的地位类似于本地区早期良渚文化的玉器与北方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是身份与地位的重要象征,是一种显赫物品。这些物品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和特别的精细技艺,因此只有贵族才能支撑生产这些东西所需的专职匠人和生产设施,控制了这些匠人和设施也就等于控制了政治权威。这样,通过不断提高显赫物品的生产技艺,贵族的政治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与合法化。因此,原始瓷的出现与使用,是社会分化与权力集中的象征。
在这种条件下,影响原始瓷生产及其发展的,不是单纯的技术因素,也不是经济因素,而是越国或者越文化政权的实力。实力强大,则生产的原始瓷数量多而种类丰富,器形与装饰复杂;实力衰弱,原始瓷的制造也跟着衰落。整个先秦时期原始瓷的发展起伏,大致反映的是越文化这种实力的兴衰。
春秋中晚期原始瓷发展上的这种衰落,跟吴文化南下及越文化南迁直接相关。
伴随着吴文化的南下,特别是春秋中晚期整个政治中心南迁到太湖北岸,太湖南岸原始瓷传统生产基地亦成了两国对峙与拉锯的前沿,不仅越国对这一地区完全失去控制,实力大为削弱,同时原始瓷制造亦受到严重影响。从窑址分布上看,这一时期本地区的窑址明显有向更深的山里迁徙的现象,同时还开始扩展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等浦阳江下游地区。而钱塘江南岸原始瓷的生产,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几乎仅限于这一时期及稍后一段时间,一旦越灭吴后,其生产中心又马上回迁到钱塘江以北的德清地区。显然这一时期原始瓷窑址的这种地域上的波动是与吴国政治中心的南下相契合的,不仅是生产区域的大变动。由于越国实力在衰落,暂时无力支撑原始瓷这种庞大而复杂的礼器生产,产品中仅剩简单的盅式碗类日用品也就顺理成章了。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火烧山》,文物出版社2008年。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亭子桥》,文物出版社2011年。
[3]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瓷器》,《文物》1982年第4期。
[4]朱建明:《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
[5]郑建明:《浙江德清小紫山土墩墓群》,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10》,中国文物报社,2011年。
[6]南京博物院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7]瓷之源课题组2007—2014年考古调查材料。
[8]同[7]。
[9]王士伦:《浙江萧山进化区古代窑址的发现》,《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10]《国语·越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33页。[11]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2、80页。
[12]刘树人等:《镇江地区吴文化台形遗址及土墩墓分布规律遥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遥感考古研究专辑)》,1982年。
[13]肖梦龙:《吴国王陵区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14]同[13]。
[15]同[12]。
[16]邹厚本等:《丹徒断山墩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17]肖梦龙:《吴国台形聚落遗址》,王玉国等编《镇江吴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18]商志醰:《吴国都城的变迁及阖闾建都苏州的缘由》,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编《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19]同[18]。
[20]a.南京博物院等:《江苏丹阳葛城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0年第5期;b.镇江博物馆考古队:《江苏丹阳葛城遗址勘探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c.南京博物院等:《江苏丹阳神河头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0年第5期。
[21]南京博物院等:《淹城——1958至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22]a.张敏:《阖闾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及其保护设想》,《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b.张敏:《吴国都城新探》,《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
[23]张照根:《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9卷第4期。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考古》2011年第7期。
[25]同[18]。
[26]同[23]。
[27]同[24]。
[28]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吴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