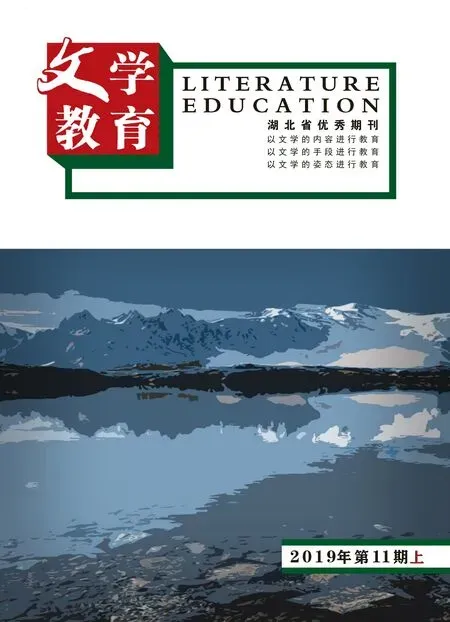看客
华 清
1.枯叶
必须要看到这枚叶子,它壮观的内部
即使是一片再普通也不过的叶子——
原野的广袤,和沟壑的纵横
被浓缩了的火焰与汁水
脉系发达,有日落日出,有月光普照
甚至田野的房屋幢幢,炊烟依依
叶脉中有河流的轰鸣,瀑布的喧响
有日午时分田畴的祥和与安谧
有依稀的虫鸣,秋蝉爬行的痕迹
有星空的图谱,宇宙永不停歇的轮转交替
有一个王朝的塌陷。犹如抗拒者的下坠
连同它的枯干,死去,还有关于这一切的记忆……
2.春梦
最好的某兄弟告诉我
——原谅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他早熟的因由源自这样一个经历
十四岁,家里来了一位漂亮的阿姨
远道而来,走亲戚。天色晚了
她只好留宿,与发育不良的他同处一室
夜色平静,他疯了一天
早疲倦地睡去。而朦胧中那阿姨
也和衣而卧,大家相安无事
然而天亮醒来,他发觉事情微妙
被窝里多了一具滚烫而柔软的裸体
他想喊,嘴唇却被什么堵住
一切像梦,他记得在梦里有过
类似的经历。而关键是,此刻
事情还在起变化,他身下的什么东西
已悄然变硬。并随着一只温柔之手的指引
缓缓地伸进了一个不明的去处
朋友们,故事到这儿我只能打住
因为这看起来确像个谎言,或是酒酣后的
吹牛。因为太不可信,一如他
酒醒后对我的讲述
3.麦地的三月——致海子
一群鸟儿倏然飞起
在昌平的孤独,孤独的麦地
并没有人。想象的坟地,周遭一片静寂

悬在空气中的麦子早已落地
墓中的人已熟睡,所惦记的人
也已老去。四姐妹,如今已是广场大妈
在神州各地扭秧歌,或跳健身舞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死的人是认真的,活着的人却各奔东西
这些年那落满灰尘的房间早已易主
人的记忆也已稀薄如空气
没有人召唤。当他
出现在三月的麦地,一群悲伤的小鸟
正在低空盘旋。它们叽喳不停,跌宕起伏
无视这老迈的闯入者,仿佛在专心致志
高声诵读,那些悲伤的诗句
4.记忆
在那些斜阳稀疏
和黯淡的秋日,光线洒落在我们的
背上。我们静静卧着,并不说话
窗外是白杨叶子的唦唦声
我在捋着你浓密的头发,或抚着你
温软的乳房,而你,在傻傻地想着什么
褐黄色的眸子里
泛着散淡而兴奋的光
那种熟悉的气息,被一只古老的坛子
封存到了这个春日的
阳光灿烂的早上
5.看客
木乃伊是这世界最适宜的看客
无助的人病了,面黄肌瘦,一无所有
他只有坐在路边看世界
他看着,你们华美的车队
你们蔽日的森林仪仗
你们傲然的圣像,你们哗然驶过的
碾压一切的马蹄
你们横扫六合,所向披靡
让一切对手发抖的胜利
他眼睛空洞,形容如死神般安静
盯着你们,沉默但不曾
错过一切,看着这马群上飞驰而过的洪流
最终化为一堆冲天蔽日的尘土
是的,尘土。他想起先知的句子——
野马也,尘埃也。他仍旧摇晃着
那一柄破旧的羽扇,静静地坐在驿道上
由木乃伊,最后化为了一块磐石
6.春光
无边春光中有一根旗杆高竖
卖豆腐的,收旧报纸的,摇着
车铃和喇叭声穿梭而入,窗外
是活泼起来的市声,街景如疯长的柳条
野草,麦苗,有节节拔高且无边蔓延的恐惧
一面镜子映着这一切,照着一张旧报纸
在故乡老宅黑漆漆的墙壁上
几欲掉落,如一只陈年的蝉蜕
光线强烈起来,光柱中有万千尘埃在飞舞
仿佛法老唤醒的逝水
零乱,缥缈,无从安置的春意
让你近旁的清晨重新睡去,除了那旗杆
还在无厘头地竖着,仿佛一个遥远的回忆
提醒你,在无边春光与你的存在之间
只有一层薄薄的窗帘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