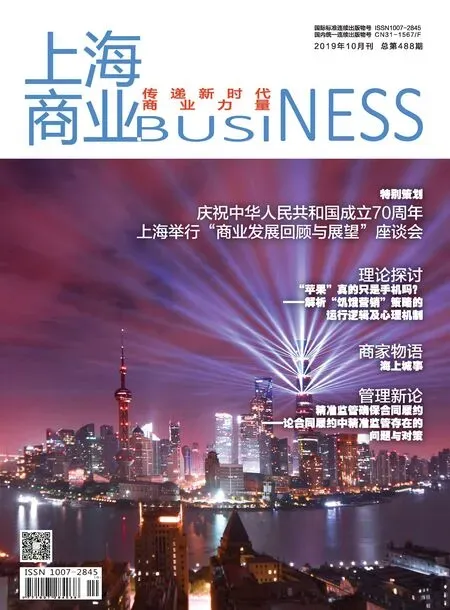亲情
文 /三 三
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湛江工作的徒儿打电话来,邀我晚上去宝山聚餐。并说,她到上海来公干,明天一早就要乘飞机回湛江,今晚抽空聚一聚。要我务必出席,哪怕再晚也会等候。
当我匆匆忙忙赶到位于宝山渔人码头的餐厅时,已经是7点半了,与徒儿约定的就餐时间,整整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徒儿心很诚,一直等到我入座,才开席。聚会者都是徒儿的铁哥们,除了徒儿我一个也不认识。好在有徒儿在中间斡旋,调剂氛围,大家很快熟悉、热络起来。
坐在我斜对面的那个女子身材修长,皮肤白的像鸡蛋里的二层皮,柳眉瑶鼻,樱桃嘴,很文静,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带着一点港台口音。当我们六目(六目乃是在座的阳子独创, 我是戴眼镜的四目,对方是不戴眼镜的两目)相对时,彼此一见如故,有种特别亲切,早就认识的感觉。
她姓刘,是一家外资公司空气净化方面的工程师。攀谈之下,果不其然,我们是同乡。她是台湾苗栗人,我是新竹的。她的老家紧挨着我的老家。熟知台湾历史的人都知道,苗栗和新竹原本属于一个县,后来县治调整才分属两县。不同的是,她父亲是从山东去台湾的国军老兵;我父亲则是从台湾到大陆,后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血总是浓于水,那横亘在中间的藩篱早已被亲情跨越。于是,两个原本在战场上处于不同阵营、兵戎相见的老兵后代,如今像一对多年没见面的好友一般,围坐在一起把酒言欢,无拘无束地交谈着。其情融融、其乐陶陶。徒儿见了,笑着说,原本就是一家人,为何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一
许是应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老话。第一次见面的我与她,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她说,她的父亲是1949年初,从山东老家乘军舰到台湾的。
那一年,她父亲才20岁,稀里糊涂被拉了壮丁。兵败如山倒,她父亲随着溃退的人群,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摸黑上了一艘开往海岛的军舰。站在船舷旁,满耳都是轻轻地抽泣声,一个个垂头丧气,脸上愁云密布。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舍不得背井离乡的愁绪弥漫在空间,盘旋在心中。带队的长官知道,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返。为了安抚士气,他板着脸,言辞凿凿地大声叫唤,只是暂时撤退,用不了两个月就能回来。长官心里也明白,这是睁着眼说瞎话,但是不这样说不行,他怕引起骚乱。
这一去,两个月自然是没能回来。两年过去了,仍然没能回来。整整盼望了20年,两鬓染上白霜,眼睛有点昏花,脸上爬满皱纹,还是没有能回来。此时,已退出军旅生涯的他,回家的信念却愈加强烈。孤苦一人在海岛的他,渴望回家,渴望回到父母的身边,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
他长得一表人才,在这20年里,前来为他说媒的袍泽和邻居众多,但都被他一口拒绝。他的心里有个梗,希冀回到家乡,由父母来操办自己的婚姻大事。
20多年过去了,回家的路遥遥无期。“回不去了。”同去的山东老乡悄悄地告诉他,肯定回不去了。他心寒了,绝望了。难道我真的要终老在异乡?
40岁那年,在一位好友的撮合下,心灰意冷的他与一位苗栗的客家姑娘,也就是刘女士的母亲成了亲。
苗栗是台湾有名的“客家大县”,县内的18个乡镇市中,13个都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他们的祖先都是17世纪时期从广东、福建一带迁来苗栗定居、开垦,在此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的。刘女士母亲的祖先是其中的一位。
婚礼上,他坚持按照山东老家的习俗来操办。那位比他整整小了20岁的苗栗姑娘,对他是百依百顺。刘女士说,母亲不贪图父亲什么。确实,作为一位落魄的荣军,两手空空,房无一间,地无一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母亲之所以愿意嫁给父亲,一是可怜父亲举目无亲,二是希冀有朝一日能由父亲陪同到广东老家去寻根。
刘女士母亲的祖辈离开广东老家时日已久,但是寻根溯源,到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去祭拜的念想,从来没有中断过。在两岸能够往来的昔日,刘女士母亲曾经随父母到广东去寻过根。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寻根之旅自然不可能有结果的。
刘女士的爷爷在临去世时说,根在广东,他的骨灰要洒在故乡的山水之间。人回不去了,魂魄要回去,叶落归根,他不愿做无家可归的荒山野鬼。
二
听到刘女士的祖先是从广东梅县过海的,一个想法在我心里萌发,会不会跟我的祖先是一个族里的叔伯兄弟,或者是乘同一条船的老乡。这想法我没有说出来,也没有去向刘女士求证。因为无法求证,也无需求证。
我那出生在台湾的侄子德辉,曾经为修家谱特地来找过我。他说,在台湾的那一脉,是沈家十四祖从梅县渡海到台湾,落脚在新竹,先是开染坊做些小生意,慢慢的有了些积蓄,从红毛乡(现改为新丰乡)徐姓大地主手里购得15公顷田地,开始务农,繁衍子孙,直到如今。
随着岁月的流失,一代代人的逝去,在德辉这代人的脑回路里,祖籍老家的印象已经有点模糊,但是对家乡的思念和寻根归祖的念头却愈发强烈。这些年来,这些唐山人的后代,纷纷组织寻根团,到祖籍地去追寻祖先的足迹。
德辉曾经跟着一个台湾寻根团,到大陆来寻找祖先的旧址。他们那个团有50多人,祖籍都是在广东、福建一带的,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德辉说,年纪上去了,甚是想念祖籍,盼望着能到祖先生活过得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点上三支清香,寄托自己的哀思。
他们从台湾到广州后,按照不同的祖籍地(省、县、市),分成若干个小组,开始寻根之旅。每每听到有人寻找到祖籍所在地的消息时,大家就不约而同为他喝彩祝贺。
由于年代相隔得实在太久远了,仅仅凭借着祖辈口口相传的记忆,寻根之路很艰难。德辉说,他按照十四祖在家谱中的记载,到广东后,开始不厌其烦地一点一点寻找线索。有一次,在梅县,他吃好晚饭在街头散步,在与一位修鞋的师傅聊天中,感到师傅所说的地方,似乎是家谱记载的祖先老家,于是,就央求师傅能否在收工后带他去看看。那位师傅也热情,得知他是从台湾来寻根的,当即放下活,带他前往。
到了目的地,德辉对照家谱记载,不像。询问之下,该地从古至今没有姓沈的家族,更没有渡海去台湾的人家。得知这结果,德辉心里有点失落。师傅却安慰他,只要大致方向对头,慢慢寻找,总能找到。师傅很真诚地说,只要有恒心,“铁棒磨成针”。
德辉参加的那个民间寻根团,在大陆整整寻找了三个月。有找到的,有没有找到的。找到的心花怒放,满脸笑容对没有找到的说,下次会陪着一起来;没有找到的,为找到的举杯祝贺,表示将继续努力。
得知他们是来寻根的,足迹所到之处,人们都热情有加。由于,都是退休老人,收入微薄,非常节省。三个月的寻根之旅,花费甚少。比如,打电话,他们不舍得使用手机的港台漫游,也不舍得使用旅馆里收费的固定长途电话,而与大陆或台湾亲人的联系又不能中断,怎么办?他们就腆着脸向前台服务员借手机。电话甫接通,告诉亲友所居住旅馆的电话就立马挂断。然后,等待亲友打过来。
德辉曾经幽幽地对我说,自己年纪大了,来去不方便。希望我能接过他的接力棒,继续寻根之旅。我点点头,说,一定尽力而为。
三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1989年,两岸开禁。刘女士的父亲在第一时间就带着她们姐弟四人,乘机从台湾到香港,再转机到济南。一出机场,就有一位年轻男子举着接机的牌子迎接着他们。刘女士说,这是大伯的儿子,彼此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亲情使他们迅速消除了陌生。她欢笑着、跳跃着,奔向这位素未谋面的堂哥。
她说,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也来了。看见40多年没有见面又日思夜想的母亲,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扑向母亲,抱着母亲嚎啕大哭。嘴里喊着,“妈妈,不孝儿子回来了。”所有的思念,在这一刻爆发;所有的眼泪,在这一刻迸发。
20岁离去,60岁回来,40年的思念哀愁,一言难尽。老母亲抚摸着他的头,高兴地说,孩子,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相比刘女士一家父母双全、亲人相聚的场面,我父亲的探亲之旅,就显得冷清心酸。同样是20岁离开家乡,同样是从香港转机。1989年的夏天,父亲从香港转机到台北机场后,居住在台北的梅表姐驾车陪同他回到了40多年没有亲近过的新丰乡老家。
祖屋还在,景色依旧,但是父母都已去世。望着挂在墙上的双亲遗像,父亲泪如潮涌。父亲是家里的老么,上面有哥哥姐姐10人,此刻不仅双亲不在了,兄姐中,除了老三、老八,其余的也都驾鹤西去了。
祖母在家里格外疼爱这最小的儿子。梅表姐说,祖母临去世时,嘴里一直念叨着父亲的名字,至死,眼睛也没有闭上。
在祖父母的墓前,父亲很虔诚地按照广东老家的上坟习俗,磕头点香。在袅袅的烟雾中,父亲想起了在两岸没有解冻前,在台湾肥料公司当工程师的老三,经过一番侧转托人从美国寄来的一封家书。老三在信中说,父亲已经去世了,病重的母亲心心念念想着你老么,盼望着能见上最后一面。
“我也想家,想念母亲,期盼着能回家尽上一份孝心。” 然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鸣天下白。要实现心中的愿景,那时比上青天还难。郁闷的父亲在墓前喃喃自语。
还居住在老家的德辉说,家族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连他的独子也离去了。他是一只孤独的留守狗,独自一人守候着这宽大又冷清的老屋。孤寂的时候,他最乐意做的事情是,用二胡拉一首广东的《步步高》乐曲,以此来排解心中的郁闷。
盼了40多年,好不容易回到了梦魂牵绕的故乡。然而,“子欲养,亲不待。”带着满腔的哀愁,父亲在归程的飞机上,不停地问,老天为何如此不公?为何不让他见双亲的最后一面。
四
刘女士说,她大学毕业后,沿着父亲从山东到台湾的路线,走了一遍,最后落户上海。在上海结婚生子,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她留在大陆,既有替父亲弥补对家乡父老的愧疚,希冀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为家乡的繁荣繁华,尽绵薄之力。同时,她觉得大陆的人文环境、营商环境,都很适合自己的发展。
她说,她的两个孩子如今也在大陆上学和工作。孩子比她更眷恋大陆,认为这里才是他们的根系所在。他们为能生活在强大的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感到自豪。他们经常由衷地高兴说,妈妈,你真英明,带我们回到了爷爷的故乡。
我对刘女士说,亲情是什么也不能阻隔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这些居住在上海的台湾省籍青年组团去厦门,在离金门岛最近的海滩,遥望着台湾岛,齐声朗诵着:你是一艘迟归的航船,这些年来,在海滩上迎接你的人越聚越多,千万双热切地眼光,在迎候着你……
五
我们就餐的包房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一艘船在海面上航行。徒儿随手拍下这幅画,发在微信上,语带双关地说,这艘迟归的航船,一定会回来。是的。这一刻,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不约而同想起了海涅的那句诗,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两岸分隔得已经太久太久,呼唤回归的喊声,越来越强烈;迎接归来的人群愈聚愈多。回来吧,回来吧。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