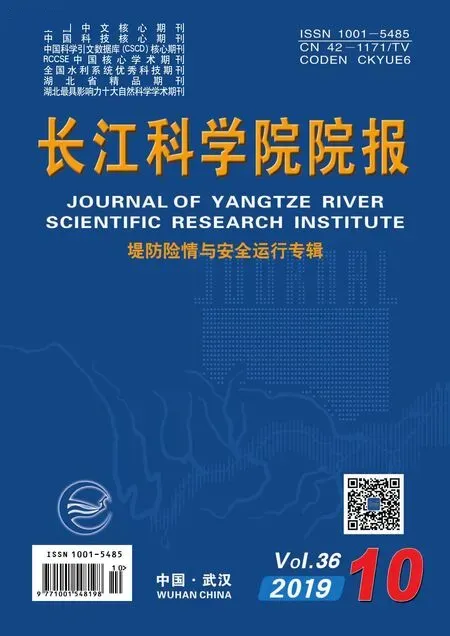论堤防管涌的危急性及其分类的意义
吴庆华 王金龙
(1.长江科学院 水利部岩土力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10;2.长江科学院 国家大坝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10)
中国幅员辽阔,江河众多,气候多样且多变,年年都有防汛抢险,管涌一词频繁见诸媒体,似已妇孺皆知。然而,管涌在渗流专业上只是渗透变形的4种型式(流土、管涌、接触流土和接触冲刷)之一[1]。在防汛抢险实践中,难以像在实验室中那样通过各种手段去观察和分析渗透变形的型式,管涌一词几乎被广泛地用于指称所有的渗透变形。可以将广义的堤防管涌简单归纳为:在堤防两侧水头差作用下,土体发生的浑水集中涌出现象。这样理解的广义管涌一词,既反映了防汛抢险的实际情况,包括防汛抢险部门的险情分类统计方式,也尽可能兼顾到了渗透变形的实质。本文中的管涌是指广义的管涌。
管涌是堤防工程常见险情之一。据统计[2],1998年长江发生的流域性大洪水期间,中下游堤防发生险情总数73 825处,管涌占35.2%;其中较大险情1 702处,管涌占51.2%;长江干流堤防较大险情698处,管涌占52.4%。通过1998年后加固的长江干堤,与三峡等枢纽控制工程和分蓄洪区一起组成的防洪体系,整体上已经达到可以防御1954年型洪水的能力,但由于堤防自身的工程特点及其运行环境的复杂性,不能完全排除干堤在高洪水位下出现险情的可能。长江中下游支流堤防的建设水平还远不及干流堤防,这是2016年区域性洪水期间发生大量险情和一些溃堤事件的重要原因。笔者2016年汛期参加长江防汛抢险指挥部的险情分析,汛后参加对长江干堤共50处一般险情逐一核查,对核查结果进行的统计分析[3]表明,50处险情中管涌险情占60%。
正因为管涌险情常见,且对堤防安全危害性大,管涌的发生和扩展规律一直是水工渗流及相关专业的重点研究对象,本文将对已有的研究工作进行梳理。总体上讲,规律性认识是在不断地深入。专业内已经认识到管涌险情未必一定会导致溃堤,有些管涌为“无害管涌”,对管涌危害性的判别方法及抢险范围也已经有一些讨论[2,4-5],但距离指导防汛抢险实践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目前的管涌抢险,不区分轻重缓急,“把苍蝇当老虎打”成为常态,打错对象的实例也不断发生;错误诊断险情,延误有利处置时机,或者处置不当,导致溃堤的实例也时有发生。这些都严重影响到管涌抢险的效率。
结合防汛抢险实践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提出管涌危急性和致溃型管涌的概念,从管涌险情实例和一系列管涌扩展规律研究成果得到启示,对管涌的危急性影响因素和危急性分类,以及致溃型管涌的识别展开讨论,力求为后续研究理清思路和明确方向。
1 荆江大堤管涌实例的启示
荆江大堤是江汉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不仅承担着极为重要的防洪使命,同时也是长江最为突出的险要堤段。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断整治加固荆江大堤。尤其是1980年代实施荆江大堤加固工程,使荆江大堤先于其他堤防工程达到规划的防洪能力。本节介绍不同年份荆江大堤的管涌实例,以便开启后续的分析讨论。
1.1 1962年管涌实例
1962年湖北省水利厅,长江科学院会同荆州修防处派员对当年发生的荆江大堤管涌险情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6]指出,由于堤外无滩,溃口形成的近堤渊塘,以及近堤取土坑对弱透水覆盖层的破坏,高水位时堤内脚常常出现管涌险情。随着堤身加高加固,汛期作用水头提高,此问题日益突出。多年来在改善堤基条件方面做了不少填塘固基工程,同时在个别堤段试用了减压井和导渗沟工程,使得几年来在同一水位下险情有所减少,但1962年汛期,在1954年以来较高洪水(沙市洪峰水位44.35 m)的考验下,此类险情还有发生。其中观音寺与廖子河堤段的险情规模很大。
1.1.1 观音寺堤段
观音寺闸下游渠道中距离堤脚290 m处,在7月中旬洪峰后发现管涌5个,其中一个管涌直径较大,约5 m,深10 m,其周围有3个小管涌。观音寺闸下游约30 m处的另一管涌直径约1 m,用反滤材料填压后沉降60~70 cm,继续填压,8月29日渠道水深约50 cm,涉水探知仍有细砂带出。
渠道中发现险情后,在观音寺街后塘中距堤70~90 m处探得3个管涌。其中一个管涌口呈椭圆形,长轴5 m,短轴约3 m,深9 m。
据当地群众反映,渠道及水塘为古张浦穴,昔日打渔即发现有“泉眼”,其位置常移动。
1.1.2 廖子河堤段
沙市水位达40.0 m时,堤脚发现管涌,深约1.6 m。经填压后堤脚附近继续发生管涌。7月10日沙市水位44.13 m时发现2个管涌(编号为12#及13#),直径1.8 m,深1.2 m。用石子填压后, 11日3时从12#孔向堤内脚移动3 m处出现新管涌,直径2 m,深约2 m;11日晚在13#孔附近又出现新管涌,至12日发展到直径2 m,深约3 m后,进行大面积填压。13日井口填料下沉1~2 m,随沉随加料,历时约一周后,沙市水位降至43 m以下,险情开始趋于稳定。
1.2 1964年管涌实例
1964年8月5—30日,长江科学院和湖北省水利厅联合对荆江大堤几个主要险工段和已经加固的堤段进行了险情调查[7]。其间沙市最高水位是42.92 m,低于前文提到的1962年沙市洪峰水位44.35 m。在1963年发生了管涌险情的观音寺堤段渠道和渊塘,经1963年5月至1964年5月共计实施了32口减压井后,调查期间没有任何险情。调查报告重点反映了蒋家脑堤段的险情。
蒋家脑堤段600+950—602+000桩号范围是历史性的严重管涌险段。1953年、1956年、1957年先后实施了填筑平台、压浸台和堤身外帮等措施加固,1962年在江水位32 m时即出现41个管涌,最大者直径20 cm。江水位33 m以上后险情不断扩大。多年汛期总共发现102个管涌,其中严重的有20个。1963年岁修时,在桩号601+572—601+972的400 m范围内,采取导渗与压渗相结合的措施,包括导渗沟、排渗竖管,以及将50 m宽压浸台加宽至80~90 m。
1964年6月29日,江水位33.4 m时,在桩号601+670、601+690、601+700、601+745多处发现管涌,其中一处在长10 m范围内发现管涌4个,6月30日增加至7个,7月1日邻近4个小管涌并成1个。1个管涌砂丘直径达80 cm,涌水高度2 cm。
6月30日,江水位33.54 m时,在601+660,601+730,601+775等桩号处发生管涌。桩号601+660处在处理过程中又陆续发生新管涌,管涌数由1个增至14个。
7月1日,江水位33.78 m时,在601+648,601+675,601+678,601+800,601+865等桩号处发生6个管涌。
7月2日,江水位34.18 m时,在601+615,601+625,601+732,601+735等桩号处发生管涌。
7月3日,江水位34.5 m时,在601+580,601+614等桩号处发生2个管涌。
7月4日,江水位34.58 m时,在601+580桩号处发生管涌。
这次洪峰期间,共发生20处69个管涌,一般发生在平台脚下10 m左右,管涌直径一般2~3 cm,最大的为20 cm,全部都带黑砂。
1.3 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险情统计分析
李思慎等[8]分析长江中下游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1982年6月汇编的解放以来荆江大堤险情资料,发现40处出险堤段中,堤基为34处,堤身为10处(其中4处堤身堤基都出险),堤基险情占绝大部分;并根据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勘察设计室1984年的资料,列出了荆江大堤管涌险情统计表(整理后见表1),可见管涌个别可远至离堤1 km,但绝大部分均在距堤脚200 m范围内;距堤脚100 m内,管涌险情数量多,但规模不大,距堤脚越远,规模反而有变大的趋势,其深度亦大,多系深层渗压力作用的结果。

表1 荆江大堤管涌险情统计(根据1984年资料)
1.4 2019年管涌实例
2019年7月3日荆江大堤江陵黄林垱段发现的管涌险情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熊河镇荆干村6组一处水塘内,对应堤防桩号716+650,距堤防背水坡堤脚约700 m。
当时,江水位约37.5 m,荆州港观音寺港区江陵石化码头及储运工程施工单位正在实施抽干水塘回填场地作业,已将塘内水位降低约3 m,造成长江与水塘之间约8 m的水位差。管涌口直径约20 cm,砂盘直径约3 m,出水量约10 L/min,带黑砂,手感水温较低。
3日晚施工单位向江陵县长江防汛指挥部报告险情。4日下午在距此管涌50 m范围内又发现另外4个较小管涌。4日夜采取抛投石块消杀水势,铺设三级反滤堆,5日5时引水入塘蓄水反压。至5日10时,水塘内水位已回升2 m。5日18时许,在大管涌50 m范围内再次发现4个小管涌。5日晚对新发现的小管涌进行应急处置,险情基本得到控制。
1.5 启 示
(1)1962年和1964年荆江大堤的险情调查资料非常珍贵,很可惜这样的险情调查工作没有在后续年代里得以继续,或者没能留下更多的文献资料;也没有报告介绍险情几何要素测量方法,管涌直径容易测量,而深度的测量方法值得研究,并可与依据砂的性质推测源自的地层及其埋深相互映证。故有必要继承1960年代初的传统,研究建立汛期堤防险情调查、记录的制度和统一技术要求,以便积累珍贵的技术资料。
(2)1962年荆江大堤管涌有的规模很大,直径可达3~5 m,远超后来的文献及防汛抢险实践中常见的险情,这是因为当时堤防工程基础条件差,渗流安全状况恶劣,同时也是因为后来的防汛抢险工作要求更高,管涌一经发现就采用倒滤堆等措施及时处置,难以再观察描述管涌口的几何形态。1962年荆江大堤管涌调查中描述的管涌尺寸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不采取抢险措施的话,管涌演变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可能达到的规模,也对类似条件下管涌模型模拟研究时设定合理的模型规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3)当堤基发生管涌险情后,地层土性发生了改变,形成了集中渗流带或渗流通道。采用常规的导滤堆或盖重措施处理后,在以后年份的高洪水位作用下,沿着往年形成的集中渗流带或渗流通道的渗透水流,遇到的渗流阻力更小,使得老的管涌口复活,或者在盖重区外找到新的薄弱部位作为突破口,形成新的管涌,这可以概括为管涌的复活特性和转移特性。
(4)具体在何处首先发生管涌,有一定的偶然性,影响因素有:地层结构和渗透性的空间变化,沟、渠、坑、塘对地层的切割及切割深度的变化,封堵不严的钻孔,无合理滤层或滤层失效的水井,动植物孔洞,古墓、古建筑造成的架空现象,杂填土,埋设的管线,近堤、穿堤建筑物与土体结合部,堤身堤基结合面,不同期填土结合面,前期或往年管涌险情对于地层的扰动,等等。上述管涌实例表明,在堤基条件薄弱的堤段有管涌险情多发的特点,当对发现的管涌采取倒滤堆等措施进行处理时,很可能又会在邻近的某个位置发生新的管涌。1964年蒋家脑堤段管涌险情,随着江水位上升而不断增加;2019年黄陵垱管涌,由一个发展到多个,这都说明由于管涌险情具有的转移特性,如果仅仅针对已发现的管涌采用倒滤堆处理措施,出现新的管涌是必然的。
2 管涌模型模拟研究的启示
2.1 无防渗墙堤基管涌扩展的模拟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荆江大堤加固过程设计过程中,长江科学院重点开展了管涌险情的模拟试验和规律分析,成果见文献[4]。研究团队注意到荆江大堤管涌险情的复杂性,规模有大有小,与堤脚的距离有近有远。为了防止荆江大堤管涌破坏,堤防管理部门曾设定距堤脚100 m作为汛期巡查范围。堤基整险加固的范围曾定为距堤脚400 m;1987年后又定为200 m。这样划定范围是否合理可靠,取决于对管涌发生、发展机理的认识程度。研究团队还了解到观音寺堤段蔡老渊内的管涌已存在70多年,而堤基并未破坏。为了弄清荆江大堤管涌扩展的机理,采用砂槽模型开展了管涌模拟试验。试验用水平渗透仪长71 cm,宽21 cm,高40 cm。表层用水泥砂浆和黏土模拟弱透水黏性土层,并造一孔模拟管涌口;下伏砂层开展不同厚度的对比模拟,底部为砾石层。试验对比的条件还有管涌口直径、管涌口与上游边界的距离。基于试验成果,文献[4]分析得出的结论包括:堤基发生管涌并不一定导致大堤溃决;管涌发生的位置可远可近;堤基渗透破坏的最终形式是流土;按照防止管涌发生来进行渗流控制设计或确定堤基保护范围会造成很大浪费;荆江大堤堤基保护范围设为距堤脚100 m已足够,其保证率或可靠度在98%以上。结合在长江流域多年防汛技术指导工作中直接观察和调查的管涌发生、发展和堤坝溃决过程,提出了管涌模拟的随机模型,并进行了试验验证[9-10]。采用这一模型,通过对土体中管涌扩展过程的模拟,得出管涌并不必然扩展导致堤坝的溃决这一重要结论。
1998年大洪水后不久,Yin[11]采用饱和稳定渗流模型研究了堤基中不同长度管涌区及其渗透系数的改变程度对渗流场的影响,分析由此引起的最大流速和总流量的变化,但并没有真正模拟管涌的扩展过程,而是把每一种长度管涌区对应的状态作为稳定状态处理,且不论管涌区的长短,其直径都看作是不变的。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毛昶熙等[12]针对“无害”管涌的问题,开展了砂槽模型试验。试验用玻璃槽有0.3 m宽的窄槽和2.5 m宽的宽槽,长均为8 m。模拟二元土层结构的材料包括顶面的玻璃板和下面装填的粉细砂。根据试验结果,毛昶熙等[12]分析得出了距堤10~15倍作用水头之外的管涌无害于大堤安全的结论,并认为与其之前采用简便方法估算的有害管涌最远距离为150 m的结论较接近。毛昶熙等[13]还探讨了管涌向堤身方向发展距离的公式计算方法,通过对案例的计算,分析认为计算结果与试验研究结果相近。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丁留谦团队[14]在砂槽模拟试验基础上开展了管涌抢险范围的讨论。砂槽长2.8 m、宽0.8 m、高0.7 m,用粉细砂模拟单层堤基和双层堤基中的强透水层,玻璃板模拟双层和3层堤基的表层弱透水层,用粉细砂层与砂砾石层组合模拟3层堤基的强透水层。基于堤基管涌破坏的允许水平比降,推算得到不用抢险的管涌位置的范围;基于试验得到的最小临界平均比降值,推算认为可将管涌与堤脚距离小于10倍作用水头作为必须抢险的范围。丁留谦等[15]还开展了双层结构堤基管涌发展的有限元模拟研究。通过对试验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得到了相近的规律。文献[15]特意强调模型概化时忽略了若干物理现象,模拟是近似的。刘昌军等[16]进一步完善该数值模拟方法,通过对试验模型的模拟,研究了模型尺寸效应的规律,根据结果分析认为试验模型尺寸对管涌的临界水头和发展过程都有较大影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刘杰长期致力于土体的渗透变形特性研究。刘杰等[17]2008年发表的试验研究成果中,砂槽模型总长5.8 m,宽、高分别为0.65 m和0.8 m。模型(含堤身)比尺为1∶40。选取3种不同细粒含量的砂砾石,以及中砂和黏土,组合为4种双层堤基。黏土与砂砾石组成的双层堤基模型中,黏土层预留了直径10 cm、深达砂砾石层的孔洞,以模拟黏土层已经发生穿孔破坏的条件。根据试验结果得出的结论包括:最薄弱的双层结构堤基是上部为薄的渗透性较弱土层,上下两层土层渗透系数相差100倍以上的组合,渗流险情演进过程为表层流土破坏,砂砾石层连续管涌破坏,并造成表层土破坏区向堤身方向发展,最后使堤身失稳;而100 m以外的表层流土破坏,不会造成下层砂砾石层的破坏,因而不会影响堤防的安全。刘杰等[18]2009年发表的成果中,模型槽尺寸仍为5.8 m(长)×0.65 m(宽)×0.8 m(高)。堤身用不透水的刚性盖板模拟。模型上部土层为低液限黏土,下部土层为砂砾石层,离堤脚一定距离在黏土层中预留排水孔以模拟管涌口。上述2个试验中砂砾石的细粒含量分别为17%和23%,均为管涌型土。根据试验结果分析认为,管涌路径上砂砾石的细颗粒流失后,变成砾石占比更高、甚至纯砾石的强透水通道,虽不影响自身整体骨架的稳定性,但流量剧增,加剧上覆黏土层的变形破坏。
河海大学陈建生教授的团队也投入很多精力研究堤防管涌的扩展规律。他们针对双层堤基管涌开展的2个阶段模型模拟试验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2011年和2013年。2011年发表的成果[19]中,模型槽长150 cm,宽、高均为70 cm。模型槽顶面为活动盖板,具有竖向移动自由度和隔水作用。盖板与其下面填设的7.5 cm厚黏土一起模拟双层堤基的上部弱透水层。强透水层采用由细砂与砾石混合的非连续级配样填筑而成。盖板开有直径为10 cm的出水口,模拟表层弱透水层的缺陷,在黏土层被顶穿后会成为管涌口。试验显示了管涌发生的先后2个过程:上覆黏土层被顶破;下伏砂砾石层被水流带出而形成管涌。管涌发生后水流剧增,但由于管涌出口规模的限制,使得水流不畅,出水口水头上升,沿程测压管水头也一度上升。将上游水头下降至出水口高程以结束第1次试验,然后再重复提升水头,开始第2次试验,直至流量出现突变,意味着再次形成了管涌。如此反复再进行了3次试验。重复试验结果表明,管涌再次发生时的上游水头明显低于上次发生时的对应值,说明已经发生过管涌的堤基,再次经历洪水时更容易发生管涌。2013年发表的成果[20]中,模型槽长100 cm,宽、高均为30 cm,顶面为固定的刚性玻璃板。盖板下面填设5 cm厚黏土模拟双层堤基的上部弱透水层。强透水层填筑采用细砂与砾石混合的新的非连续级配样。盖板和黏土层预留直径为5 cm的出水口,模拟黏土层被顶穿形成的缺口。试验中观察到管涌通道加剧上覆黏土层的破坏,反过来又使得管涌涌砂量增大,加速地层被掏空的速度。
周红星等[21]在研究北江大堤管涌过程中,开展了二元结构堤基弱透水覆盖层的试验模拟方式对比研究。试验模型填样空间长60 cm,宽20 cm,装填26 cm厚的细砂模拟强透水层,表层弱透水层的模拟对比采用了玻璃板、水泥砂浆和密封加压水袋3种材料,并预留直径3.5 cm的半圆形孔模拟管涌的出口。分析试验结果后认为,表层弱透水层采用不同材料模拟的结果差异很大,采用刚性材料时,类似于闸底板冲刷试验;而密封水袋也与表层黏土层的作用差别很大。
贾恺等[22]探讨了双层结构堤基管涌通道扩展的模拟计算方法,引用河流动力学的相关公式,考虑砂粒相对暴露度、脉动流速、起动标准和管涌通道水流特性等因素提出通道扩展的判定条件,建立有限元计算迭代流程,对管涌通道横截面进行了数值模拟,并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说明了方法的可行性,同时考虑顺管涌通道方向扩展的三维模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2 有防渗墙堤基管涌扩展的模拟研究
长江科学院开展了悬挂式防渗墙条件下堤基管涌扩展过程的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考虑到管涌模型比尺问题的复杂性,难以将模型还原到实际工程,采用内空长70 cm、宽29.6 cm、高54 cm的砂槽模型进行试验,开展扩展过程及其受防渗墙制约的规律研究[23]。对试验模型开展数值模拟研究,数学模型先后考虑了非稳定渗流与管涌扩展过程的相互作用[24]和非稳定渗流、管涌扩展过程与上覆土体坍塌的相互作用[25-26]。模型中将管涌区作扩大渗透系数处理。研究结果均表明管涌的扩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休止,悬挂式防渗墙对防止管涌的发生作用不大,但是可以制约管涌的扩展,防渗墙越深,制约作用越大。
清华大学也开展了管涌扩展的模型试验[27]和数值模拟[28]研究。试验槽内部装样尺寸120 cm(长)×25 cm(宽)×20 cm(高)。通过黏土泥浆自然沉积后风干12 h形成固结黏土,以模拟堤基表层弱透水层;在水中分层撒中细砂,形成砂土层以模拟堤基的强透水层。通过对彩色示踪砂粒的分布、出砂量的分析,认为防渗墙对于管涌的发生与扩展都有影响,防渗墙越深,对管涌扩展的制约作用越大。数值模拟时,将管涌通道中水的流动用管流理论进行模拟,未发生渗透变形的区域用基于层流的渗流分析方法模拟,一系列模拟表明:管涌口离堤越远,管涌扩展达到稳定(即休止)时管涌通道发展长度越短;悬挂式防渗墙虽然难以阻止管涌的发生,但是可以抑制管涌的发展。
张超等[29]通过砂槽模拟试验,研究了有无悬挂式防渗墙以及不同土层结构条件下的管涌发展过程。砂槽装样空间为85 cm(长)×30 cm(宽)×30 cm(高)。模型顶部为刚性有机玻璃板,下设5 cm厚的黏土以模拟堤基表层弱透水层,有机玻璃板和黏土层预留直径4 cm的缺口,以模拟管涌口。黏土与砂砾石组成的双层堤基对比开展了有无防渗墙的试验。三层结构堤基中,黏土与砂砾石层之间有1 cm厚的细砂。悬挂式防渗墙用1 cm厚的有机玻璃板模拟,插入强透水层深度为6 cm。3个试验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悬挂式防渗墙能够提高管涌贯通的水力比降,且双层、三层结构堤基的管涌发展形式不同。
陈建生等[30]采用文献[29]同尺寸的砂槽模型试验模拟了悬挂式防渗墙条件下不同细粒含量的砂砾石层管涌扩展过程。模型顶面为有机玻璃盖板,槽内装填黏土和砂砾石土层模拟双层结构堤基。预留直径4 cm,贯穿有机玻璃盖板和上部黏土层的圆孔,模拟管涌出口。砂砾石层试样对比使用了细粒含量分别为26%,23%,20%的3种级配样。基于试验结果,本文分析认为,砂砾石样的细颗粒含量影响管涌发生时的水力比降和管涌扩展过程及其危害程度:细粒含量大,临界水力比降越大,绕过防渗墙前后的管涌扩展路径主要是沿着砂砾石层顶面,扩展速度快,容易导致上覆黏土层的坍塌,并造成模型的整体破坏;细粒含量低的砂砾石样,管涌发生时的水力比降较低,管涌扩展路径偏向于土层内部,且对土样骨架稳定性影响较小。
2.3 启 示
(1)管涌发生发展规律的模拟是研究热点,已经发表了很多成果,但是一些结论性成果与实际应用的需要还有很大距离,例如,关于有害管涌和不必抢险管涌分布范围的建议,没有得到防汛抢险实践的应用和认可,甚至没有在专业领域内取得一致意见。
(2)管涌扩展的影响因素很多,作用规律复杂,已有的研究还只是针对少数简单条件开展的,研究结论缺乏普遍性,甚至与实际工程条件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成果应用受到限制,甚至还没能起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3)已有的模型试验研究,模型尺寸都偏小。所考虑的模型比尺,没能反映土样颗粒的缩尺、管涌附近复杂的三维渗流流态、管涌口规模、土样细颗粒总量对管涌区域供砂能力的影响等。文献[6]调查到的管涌口直径达5 m,堤防仍然没有溃决,可以想见现有室内试验模型规模对于管涌扩展过程可能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会迫使管涌加速向上游扩展,使实际可能休止的管涌夸大为导致模型破坏和堤防溃决的管涌。
(4)大多数模型试验都预设了管涌口,其规模在试验进程中不会变化,试验成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规律性,有的研究观测到初期管涌口水头上升。实际上,管涌口与管涌通道一样,应该不受模型制约而自由扩展。管涌口的扩大,会起到消减水头的作用,类似于一个没有设置滤层的减压井,管涌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水力比降有可能会降低。随着管涌规模进一步扩大,只要没有殃及到堤身附近的土体,有可能演变为一个减压池,管涌演变逐渐趋于休止。所以试验模型对管涌口规模的人为约束,也会夸大管涌的扩展,不当地促进模型整体的破坏和堤防溃决。
(5)现有管涌扩展过程的数值模拟方法,或者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物理过程,使得模拟结果失真,或者尽可能多地考虑了真实的物理现象,但使得模型模拟的规模受限,未能应用于实际工程的模拟。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管涌演变规律的研究,要通过大模型、甚至原型试验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值模拟研究需要发挥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模拟管涌伴随的各种物理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并在过程中不断进行管涌区是否扩大、管涌区土体自身结构稳定性、管涌区上覆土体结构稳定性等多种判断,通过试验验证后,应用于实际复杂条件下的规律性研究。
3 管涌危急性及其影响因素
3.1 基本概念的讨论
为了正确理解管涌的演变规律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需要厘清有关基本概念。
管涌和管涌破坏,实际上分别是室内渗透变形试验中对应于渗透变形和渗透破坏的形式之一。室内渗透变形试验,为一维水流条件,取试样进出口截面之间的距离为渗径长度L,在不断提升的供水水头下,分别形成稳定渗流条件,测得整个渗径上的总水头损失ΔH,除以渗径长度得到的水力比降I,实质上是平均比降,即I=ΔH/L。
在试样发生渗透变形之前,实际上是材料试验,忽略材料的非均匀性,得到材料渗透性这一宏观特征。当试样发生渗透变形时,或者试样在出口断面上出现流土,或者试样内部细土颗粒发生迁移和流失,宏观上表现为流量增大,水变浑,计算得到的渗透系数增大;微细观上,土样的有效渗径长度,或者土样颗粒组成和孔隙特性发生了变化,水流由一维流态转变为三维流态。当渗透变形发展使得整个试样的渗流阻力突然显著下降或者消失时,意味着试样整体发生了破坏,称为渗透破坏,此时试样渗透性的测试已经没有意义,试验结束。
有一些细粒含量较低的管涌型土,虽然在试验过程中发生了渗透变形,但是在实验室供水条件所允许的最大试验比降范围内,即使整个渗径上的细土颗粒都已流失,但是土样内部的粗颗粒骨架仍然维持稳定,试样仍然可以承担相应的水头损失,渗透性也没有显著增加,水流变为清水,这时会得出在最大试验比降下试样没有发生渗透破坏的结论。
由上述过程可见,试样发生渗透变形之后,试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材料试验,而是实质上的三维渗流结构模型试验。渗透破坏实则是模型的整体破坏。
回到前文所述的管涌模型模拟试验和实际堤防工程中,就会发现,其所称的管涌与渗透变形试验中的渗透变形(含管涌)概念相对应,管涌逐步演化,可能最终导致模型破坏和堤防溃决。也就是说,实际堤防工程中,管涌的发生及其演变都是管涌现象,不宜用管涌破坏的概念,管涌演变的结果是休止或者溃堤。
3.2 管涌危急性的概念
无论是本文第1节回顾的实例调查和统计分析,还是第2节回顾的已有模型模拟研究,都有一个理想目标:提出无害管涌或不必抢险管涌的判别方法。然而,管涌扩展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影响的方式很复杂,多因素综合作用更加复杂。这就使得提出的判别方法或标准的可靠性都只能是相对的。同时,堤防工程的安全事关保护区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抢险的决策任务由行政首长承担,其承受的压力很大,也很复杂,不仅限于技术层面。类似无害管涌这样简单明确的概念,虽易于理解,却难以在实践中被接受和应用。
建立管涌危急性或管涌危急程度(criticality of piping)这一概念,旨在定量地评估管涌的特性和趋势,避免无害管涌等类似简单定性概念可能造成的偏差。管涌危急性定义为:在堤防可能经受的洪水荷载作用下,为避免管涌不断演化而危及堤防安全,需要采取抢险处置措施遏止其进一步演化,或者启动决堤预案的紧迫程度。根据管涌危急性,可以对管涌进行分类施策。
3.3 管涌危急性的影响因素
张家发等[31]通过典型堤基渗流场的计算分析,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堤身堤基渗流场影响因素的作用规律,包括作用水头、堤身渗透性、堤基地层结构和地层渗透性及其厚度、外滩和深泓切割条件,并指出实际情况下的地形、地质和工程条件很复杂,应针对具体条件进行分析研究。渗流场的分布是管涌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基础,影响渗流场的因素也会是影响管涌危急性的因素。这里暂不开展定量的规律性研究,也不打算展开各项因素的分析讨论,而只是对几项特殊因素的作用方式进行讨论。由于作用水头的复杂性,因而将决定作用水头的洪水特征和堤内水位分开来讨论。同时,对于险情的演变规律来说,管涌的位置成为非常敏感的因素,必须纳入讨论范围。很多堤防在加固工程建设中实施了垂直防渗墙或者减压井等渗流控制措施,使得一些影响因素对渗流场的分布和动态、管涌发生和演变的作用规律更加复杂,有必要纳入讨论。
3.3.1 洪水过程
堤防工程实际经历的洪水荷载是复杂的洪水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洪水水位值。堤防工程经历高洪水水位的长时间浸泡或历时较短的洪水,其表现及险情的发生与演变是不同的。已达标工程的超标准运用[32]和未达标工程的超负荷运行,尤其需要考虑实际经历的或预测将要经历的洪水过程。
管涌发生后,在某一个洪水过程中可能不断地扩展和演变,也可能休止;在下一个洪水过程中,原来的管涌又可能启动扩展过程,或者在另一个年度的洪水过程中管涌又可能复活。具体到某个管涌,既需要根据当前洪水过程分析研判危急性的状态,也需要根据将要经历的洪水过程预测危急性的趋势。
可以根据洪水过程中管涌演变的特点,从洪水过程提取一些关键特征值,以方便归纳概化洪水条件,开展洪水特征对管涌演变作用的定量研究。
3.3.2 堤内水位
堤内水位往往是指堤防保护区内对堤基渗流场起控制作用的最低水位。减压井、减压沟是主动设置的堤内水位条件。堤内的湖、塘、沟、渠、井,往往是堤基渗流场的定水头边界条件,也往往是堤基渗流安全的薄弱部位,对于渗流场和渗流险情的发生发展起着控制作用。2016年长江干堤的50处险情,有不少是与塘、渠有关,也有的是与减压井失效而未能有效地控制渗流场有关。
第1.4节的荆江大堤黄林垱段管涌,是在长江水位还没有达到设防水位的情况下,施工企业抽水,使塘内水位下降3 m后,相当于作用水头上升了3 m,塘内发现管涌。抢险人员首先想到的抢险方式是设导滤堆。在做导滤堆后,以及在后来抽水入塘进行反压的过程中,又先后发生了8个小管涌,就充分说明了导滤堆只能起到对已发生险情的针对性处置效果,要解决整体性的问题,需要首先调整下游水位条件,或者针对整个塘内表层弱透水层厚度薄的问题,满铺一定厚度的排水反滤层。具体决策需要在比较人力、物料、设备、时间等因素及实施的难易程度后确定。
3.3.3 管涌位置
管涌位置往往是指管涌口所在位置,可以是管涌在堤身上出现的具体部位,也可以是在堤内出现的管涌口与堤内脚的距离。
2019年8月,笔者参加了对湘赣两省7月份出现的9处决堤和溃坝险情的现场调查分析。水利部要求调查的总共7处堤防险情都发生在乡村地区的长江支流堤防,有1处是无等级的堤防险情,其余都是5级堤防的险情;2处为堤身堤基险情,5处为堤身险情。这些低等级、甚至无等级的堤防,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加固工程建设延后,甚至还没有立项。在7月份的连续大雨后升级为暴雨、大暴雨的过程中,河道出现了超标准洪水,甚至超历史记录的洪水,堤防严重超负荷运行,甚至洪水漫顶,造成了严重的险情,实际上有5处发生堤防决口。另有一处,抢筑的子堤起到了挡水作用,虽然子堤漏水造成堤内滑坡,但是通过抢险止住了滑坡,防止了堤防决口,算是一个抢险成功的案例。还有一处是在超标准洪水作用下穿堤钢管周围土体发生接触冲刷,形成涌水通道,类似一个大管涌,虽未造成决口,但是在堤身迎水面抢抛块石和袋装砂土逐步消杀水势后,挖开堤顶,形成便于施工的缺口,再填筑黏土,实现闭气。这种在高洪水位下破堤抢险的方式极具风险,所幸管涌位置较高,抢险获得了成功。
经历2019年参加对长江支流堤防险情的调查分析,与近些年对长江干堤险情分析,尤其是研究背景中提到的2016年汛后对险情的核查,认识到堤防险情发生的一个显著规律:在已经完成达标建设的堤防工程,主要是堤基险情;在未达标堤防,或者低等级,甚至无等级的堤防,主要是堤身险情,或者堤身堤基结合部的险情,后者危急程度甚高。
2017年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垸的管涌险情距堤内脚约60 m,初现时,管涌口直径约15 cm,水浑,险情迅速扩展,抢险反滤围井被冲毁。这说明对险情危急性和可能扩展的规模认识不足,反滤围井过小。管涌快速扩展,导致地面塌陷,及至堤身沉陷,所幸没有决堤。该险情充分显示了近堤堤基管涌的危急性。
管涌逆水流方向扩展所达到的位置,对于管涌危急性的判断很有意义,可是因为隐伏于地下,这一位置一般难以掌握,除非管涌造成了地面塌陷,甚至形成了新的管涌出口,否则只有寄望于能够用地球物理方法进行准确的探测。
3.3.4 地层结构条件和土体性质
对于堤身管涌来说,结构条件是指堤身断面的结构形式和几何特征,土体性质是指堤身的土性。对于堤基管涌来说,结构条件和土性是指管涌及其扩展途径上的地层结构和土体性质。
无论是堤身险情还是堤基险情,都要注意是否与建筑物有关。土体与穿堤建筑物或者近堤建筑物的接触部位容易出现填土不实或者接触缝等隐患,刚性建筑物的支撑作用使得土体发生隐蔽的接触冲刷后不容易造成地表变形而被察觉,一旦发现,险情可能已经扩展了很长一段时间,危急程度很高,容易造成决堤。
1998年江西省九江市的长江大堤决口就与邻近的码头工程有关[33]。2016年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新华垸红旗闸溃口也是一个典型。刚刚完成加固的堤防就经历超标准洪水的考验,险情发现后,发展很快,堤防决口后,红旗闸依然耸立在洪水中。本文引言中提到的2016年长江干堤50处险情,与穿堤建筑物相关的有6处[3]。
地层结构和土体性质在已有研究中被考虑得最多,本文第2节已经指出,由于模型规模的限制,模拟研究中概化的地层和土性条件与实际工程相差较大,对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和可靠性有一定影响,这里不再讨论。
3.3.5 渗流控制措施
堤防工程各种渗流控制措施都是为了防止或减少堤身堤基渗流险情的发生。对于已经发生的管涌来说,已经大规模实施的垂直防渗墙和在部分堤防中实施的减压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险情的扩展过程和险情的危急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天然堤基渗流场起重要作用的作用水头,在实施垂直防渗墙或减压井后,会有不同的作用规律。即使经历同样的洪水过程,建设防渗墙之后,与建设防渗墙之前,或者与没有实施防渗墙的堤段相比,作用水头应该更高,堤防更安全,否则就有可能是防渗墙深度不够,或者质量存在缺陷,未能达到预期的渗流控制效果。同样的洪水条件下,建设减压井之后,与建设减压井之前,或者与没有建设减压井的堤段相比,下游水位取决于井口高程,一般会低于堤内最薄弱处的高程或水位,使得作用水头更高;否则,就可能是减压井未达到理想的渗流控制效果。尤其是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相同或相近洪水条件下作用水头的上升,意味着减压井可能发生了淤堵,甚至失效。
封闭式和半封闭式防渗墙与防渗依托层形成可靠的防渗体系,可以起到显著的渗流控制作用[34],防止防渗险情的发生,也会制约险情的扩展。悬挂式防渗墙,一般难以对渗流场起到明显的渗流控制作用,对于渗流险情的发生影响不大,但是本文第2.2节提到的研究成果都说明,悬挂式防渗墙可以改变险情的扩展途径,降低险情的危急程度。
正常运行的减压井,有一个有效的控制范围;合理间距的减压井列,可以使其控制范围不受管涌扩展的波及。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堤防险情演化机制与隐患快速探测及应急抢险技术装备”正在研究将减压井措施用于防汛抢险的可能性,力图达到防汛抢险与汛后除险加固工程相结合。
4 管涌危急性分类的意义
管涌发生后,根据危急程度进行的合理分类是分类施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管涌险情处置针对性和科学性的重要途径。危急程度低者,只需要作为巡查的重点予以观察;随着危急程度的增高,需要更急迫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处置。为此,需要开展基于危急性的管涌分类方法和标准研究。这里还没法提出具体的分类方法和标准,先就危急性最高的一类,即致溃型管涌展开讨论,从中也可以更加理解管涌危急性分类的意义。
致溃型管涌(piping tending to breach)是指管涌的危急状态或危急趋势会危及堤身安全,预判到引起堤防决口的可能性,需要立即采取抢险处置措施遏止其进一步演化,或者立即启动决堤预案的管涌。
根据危急状态识别的致溃型管涌,已使堤防处于可能发生决口的关键时刻,人员转移是第一要务。
根据危急趋势识别致溃型管涌,主要看管涌是否匀速,甚至加速向堤身方向发展,以及堤防可能决口所需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堤身管涌,以及管涌扩展过程没有收敛迹象、短期内可能扩展至堤身附近的堤基管涌,可以划为致溃型管涌。
5 结 论
本文回顾了荆江大堤的管涌实例,以及围绕管涌开展的模型模拟研究工作,启示了管涌危急性和致溃型管涌概念的建立,并分别展开讨论,主要结论如下:
(1)管涌具有复活特性和转移特性。
(2)管涌发生发展规律模拟的一些结论性成果与实际应用的需要还有很大距离,需要通过大模型、甚至原型试验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值模拟研究需要发挥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模拟管涌伴随的各种物理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3)对管涌危急性具有特殊影响的因素包括洪水过程、堤内水位、管涌位置、管涌附近及其扩展路径上的地层结构条件和土体性质、渗流控制措施等。
(4)根据危急性对管涌进行分类,是管涌分类施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管涌险情处置针对性与科学性的重要前提。
(5)一般情况下,堤身管涌,以及管涌扩展过程没有收敛迹象、短期内可能扩展至堤身附近的堤基管涌,可以划归为致溃型管涌,需要立即采取抢险处置措施遏止其进一步演化,或者立即启动应对决堤的预案。
致谢本文受益于多年来参加的长江流域堤防抢险、险情分析与核查、决堤险情调查分析专家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