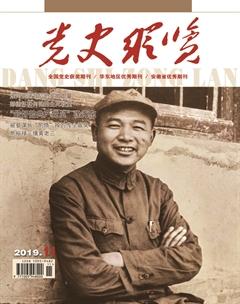“针刺麻醉”出台的前前后后
罗元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振兴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国医学界进行了不懈探索,并重视对针灸这一传统中医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此作出指示。
毛泽东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的周泽昭谈话时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
1955年4月15日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看望针灸专家朱琏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醫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当天晚上,在杭州刘庄,毛泽东又对朱琏提出:“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在对针灸这一传统中医技术研究过程中,“针刺麻醉”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韩济生教授说:“针灸止痛,有人说是有3000多年,有人说更长的历史,但是对其进行科学深入的研究,确实还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
2004年10月13日,韩济生应邀做客新浪网,谈及我国针刺麻醉的研究和应用的往事。
他说:“1958年的时候,所谓敢想敢干,如果说扎针能够止痛,那我扎针能够预防疼痛吗,待会儿就要手术了,没有麻药能不能先扎针止痛呢?这就是当时一句话,叫‘针刺麻醉。那时候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国际上都知道了,中国有一个针刺麻醉,扎针以后就可以开刀,那时都非常的稀罕。后来外国人来参观,后来就传得越来越开。有的人说,中国人扎针不痛能做手术,能讲出道理来吗?讲不出来,这不是我们泱泱大国有的,当时的医学部长说,你可以找一部分人来研究扎针为什么能止痛。”
韩济生自己一开始也不太相信针刺能够产生麻醉作用。
1958年,时任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的彭瑞聪带着韩济生一起来到北京通州,在当地的胸科医院看开胸切肺手术。韩济生亲眼看见一位20岁左右的女患者在针刺麻醉下接受肺叶切除大切口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患者说话喝水完全没有表现出疼痛的迹象。
这件事让韩济生相信“针刺”真的有镇痛作用,他认真思考:“针刺”为什么会止痛?它的规律是什么?
韩济生在自己的生理课堂上询问班上的学生,愿不愿意做被试者,试验一下扎针后痛觉的情况,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手。
1965年,韩济生和学生们采用在皮肤上施加逐渐增强的阳极电流来引起疼痛感觉,发现一个毫安就能引起痛觉,这一数值被称为“痛觉阈值(痛阈)”。当在“合谷”穴上扎针以后,痛阈慢慢增高,30分钟后增高80%左右,并保持在高点;停止扎针以后,痛阈慢慢恢复,半衰期为16分钟。
“针刺后的镇痛效果并不是立即显现,需要20到30分钟左右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停针后麻醉效果也不会立刻消失,而是缓慢下降”。这与临床中一般针刺麻醉施针“诱导”半小时后才能开始手术的实践经验相一致,基础研究结果与临床观察完全符合。
韩济生逐步寻找到了“针刺麻醉”的规律。
1972年,韩济生继续进行科研。他在分析了1965年得到的人体实验结果后,觉得这很像是有一种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参与其中,便开始从动物脑组织中寻找假想中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我们给兔子扎针,把兔脑里的液体抽出来打到另外一个动物脑子里,那个动物没有接受扎针,可是痛觉也迟钝了,说明针刺镇痛确实有其物质基础。我们白天实验,晚上做统计,数据积累得越多,曲线越光滑,规律性也渐渐明确,我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提出假说,可能有神经递质参与,然后一个一个去确定,一个一个去排除。”这些化学物质,有的是已知的神经递质,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等,有的是作用类似于吗啡的肽类物质,如脑啡肽、内啡肽、强啡肽等。
当施加于穴位的电刺激脉冲频率改变时,脑内产生的化学物质也发生改变,并找到了它的规律,例如每秒2次的低频电刺激引起脑啡肽和内啡肽的释放,每秒100次的高频电刺激引起脊髓中强啡肽的释放。
“如果说我一辈子有所发现的话,‘穴位上不同频率的电流刺激,会令大脑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这意味着,大脑工作的‘密码被我们发现了!”韩济生说。
韩济生接着说:“当时给周总理的报告基本上搞清楚了针灸会止痛的原因。通过针灸传到脑神经里面,它类似于吗啡的作用,但不是吗啡,是内啡钛,这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反响。现在,在国际上召开跟疼痛有关或者跟针灸有关的会议都要我们参加或做报告,没有的话好像是缺了一块。所以说,到现在我可以说我们国家在针刺研究方面是站在国际顶端的。”
据可查阅的资料记载,针刺麻醉分别于1958年起源于上海和西安,开始仅用于扁桃体切除术等小手术。针刺麻醉技术的发展,是帮助针灸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重要开始因素。
《针刺麻醉应用于胸部手术:42例临床分析》的报告引起了轰动
1959年3月30日,北京结核病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培养的博士高永波,在广西柳州结核病医院实施了一例针刺麻醉下右上肺叶切除术,获得了成功。
1960年5月21日,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学术会议在青岛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地代表约300人。就在此次大会上,来自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现上海肺科医院)的手术部主任裘德懋教授,关注到了高永波的针刺麻醉手术报告。
会议结束之后,裘德懋回到上海,立即重复了高永波的操作,但他第一次尝试却失败了。
于是,裘德懋派人到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寻求合作。当时的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主任孙宝玺马上召集针灸学博士党波平、陈德尊、金舒白等一同开会,在场同志一致认为针刺麻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两部门达成了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安排,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决定,安排具备扎实的西医学基础和外科沟通技巧的唐松岩博士到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开展工作。
1960年7月5日,唐松岩与外科医生徐学僖、赵振普成功地使用针刺诱导麻醉代替药物麻醉,为54岁的男性患者陈履平实施右上肺叶切除术。手术持续了3个半小时,使用了超过100个腧穴,部分思路采用高永波的经验,手术全过程病人神志清醒,可以聊天,并且术后无明显疼痛记录。病人在术后的一晚睡得很好。
随后,唐松岩和外科医生谢庭槐、龙涛,在苏联专家访问团的观摩下,又成功地使用针刺麻醉为23岁的大学生周国良实施开胸手术,手术很成功。手术过程中,周国良没有出现明显的疼痛。在场的医务工作者和相关研究人员非常兴奋,纷纷向上海市卫生局报告手术的结果与针刺麻醉的发现。
1961年8月14日,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杜大公参观了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观察41例针刺麻醉下肺叶切除术,听取针刺麻醉研究小组的报告,之后他对医务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研究使用针刺麻醉予以鼓励和肯定。至1961年9月,共有42例肺切除术在针刺麻醉下进行,其中37例(88.1%)成功完成,只有5例(11.9%)失败。
1961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小剂量针灸穴位注射与针刺麻醉论坛上,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与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联合发表了题为《针刺麻醉应用于胸部手术:42例临床分析》的报告。报告强调针刺麻醉下手术的特点是“干针刺”(简单的针刺手法),没有使用麻醉药物。总结针刺麻醉的优点是:使用工具简单,无药物麻醉引起的副作用,患者在手术过程中醒着,术后护理更方便,身体恢复更快,患者可咳嗽除痰,无需插管。
这个报道立即引起了轰动。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手术室,观摩了针刺麻醉下实施的肺切除术。
可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医学界对针刺麻醉的联合报告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支持和感兴趣的意见很多,同时反对的、质疑的声音也很大。许多医院最初对针刺麻醉感兴趣,但在舆论压力出现后,又纷纷停止了针刺麻醉试验。然而,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针刺麻醉研究工作者从来没有放弃,许多研究人员自愿作为受试者,为针麻积累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于光远向毛主席报告,针刺麻醉的研究应该鼓励。毛主席说:“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它!”
1964年初,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于光远抵达上海,进一步考察针刺麻醉。在听取报告后,于光远认为:“针刺麻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交了报告。大家要鼓足干劲,党和政府会提供支持,保障大家继续前进。”
此后,于光远向时任中国国家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传达了上海的针刺麻醉研究的相关进展。过了几天,钱信忠就派了两个人到上海来,没有暴露身份,只是说北京卫生局来两个人看看,其中一个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副院长、生理学家沈其震。参观以后,沈其震说:“开始我是不相信的,看了才知道是真的。我回去会向卫生部报告的。”
随后,钱信忠安排了另一个由10人组成的团队,由北京结核病医院负责人辛育龄率领赴上海,其中包括3名外科医生、3名麻醉医师、3名针灸师和1名外科护士。他们留在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并接受了3个月的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术的培训。回到北京后,辛育龄团队成功地进行了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术。
这以后,钱信忠又先后三次来上海视察。视察之后,他说:“我很高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手法要再简化,穴位要再减少。”
1964年6月30日,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发布了《教育与健康状况》,对针刺麻醉研究工作进行了表彰。时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杨西光观摩了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针刺麻醉。在上海市委大力支持下,上海第二个针刺麻醉研究中心也在上海华山医院成立了。
1965年1月2日,于光远来到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表达了他对针刺麻醉的看法:“针灸麻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我们应该支持针刺麻醉研究。如果项目需要人,我们就给人;如果需要钱,我们给钱。我们应该设计一个漂亮的手术室,方便外国游客的观摩。我们针刺麻醉的研究处在国际先进水平,已经是无可非议的,现在我们应该把对手甩得更远。去年,科学中心研讨会,我向毛主席报告,针刺麻醉的研究应该鼓励大跃进。毛主席说:‘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它!毛主席还说,中国人要有抱负。日本坂田昌一发现基本粒子,我们中国人对世界应该有自己的贡献。”
此后不久,国家卫生部拨款60万元人民币,用于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修建一座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3层楼建筑,专门用于针刺麻醉研究,还配备了具有尖端科技水平的生理记录仪和动脉血气分析仪,同时订购来自海外相关领域的英语期刊。
随着针刺麻醉在临床上的成功,针刺麻醉机制研究也开始了。1963年,神经科学博士张香桐、封岩和来自济南的心理学家胡寄南,在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观摩了针刺麻醉手术过程。访问期间,为了测试针刺麻醉的功效,张香桐亲自尝试了一下。他让一位针灸师给他做了一个小时的针刺麻醉,表示自己在针刺前后确实感受到了身体感觉的不同。
参观完后,张香桐问:“切口前,针灸针需要捻转多久?”得到回答:“30至60分钟。”张香桐说:“针灸麻醉也许不仅有神经生理作用,也可能有神经生化作用。一些与疼痛相关的化学物质(神经传递介质)已经在国外被发现。针灸会产生这种物质吗?因为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物质,它们就可以作为研究目标。我们应该让神经生化专家参与进来。”很快,几位专家带着他们的学生团队,建立了相关的研究项目。
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和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共同撰写了《针刺麻醉应用经络穴位于胸腔(肺)手术的临床研究报告》,其中186例针刺麻醉用于肺切除术总结,并上报国家科委。1965年12月,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正式文件,内部发表了这份报告,承认针刺麻醉是具有国家重要性的一级成就。
就在针刺麻醉研究进入全盛期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导致针刺麻醉研究几乎全部中断。
周恩来接见研究人员时说:“你们大家应该进行广泛的合作,针刺麻醉的机理必须弄清楚!”
1970年,周恩来在接见针刺麻醉研究人员时说:“你们大家应该进行广泛的合作,针刺麻醉的机理必须弄清楚!任何新东西总是有缺点的,我们应该研究好、使用好它!”
1971年7月18日,《人民日報》正式向世界宣布了中国的针刺麻醉研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由白宫办公厅主任率领的由30多名美国官员和媒体记者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上海,并观摩了一台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所有人都表达了惊讶和极大的兴趣。这次访问之后,美国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有很多关于针刺麻醉的报道和采访,针刺麻醉极大地引发了西方医学界对针灸的兴趣。针灸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引入美国,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针刺麻醉在中国的成功。
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召开了一次会议,确认了针灸的镇痛作用,这帮助针灸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获得了更多的认可。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