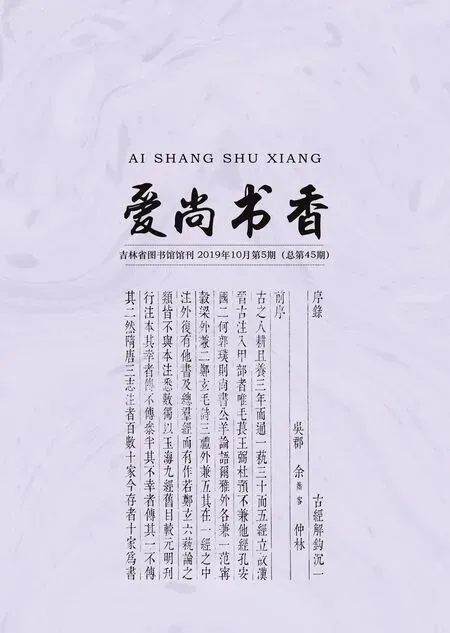爱花爱猫的冰心
李 辉
生活中,鲜艳多彩的花儿,总是装扮着人们的环境,陶冶人们的情趣。在富有感情的人们那里,花儿,不再是孤立的、冰冷的纯植物,而是温暖的、真诚的爱之体现。
冰心是爱花的。
三十多年前的五月,北京正是繁花似锦的季节。走进冰心老人的静雅秀美的客厅。八十高龄的冰心老人,矮矮的个头,脸庞清瘦,几年前的骨折,使她至今行走不便,更少外出。
她讲起话,语调委婉柔和,带着南国女性特有的温柔,一如她的小诗。我们交谈着,谈她的小诗,谈她的小说,谈她和文坛同代人的友情。她的记忆力那样好,半个多世纪前与某某作家的第一次见面,她竟然说得那样清楚。
她笑,开怀的笑,甜蜜的笑,融进窗外射进的温煦的阳光,也融进了窗台上、桌子上那一盆盆鲜花散发出的清香。
一会儿,冰心递过几份印着铅字的征订单,原来是月季花征订单。一个由待业青年创办的月季花种植场,热情洋溢地向人们推荐新鲜月季花。文中还感激地写到:“冰心先生很关心我们这一事业,她曾嘱咐我们一定要育花又育人。”
的确,冰心对此特别热心。她兴致勃勃地说:“你知道这件事吗?你拿去几张吧,可以帮助宣传宣传。”老人的热诚,溢于言表。我看她身后那一朵朵红的花,白的花,那张挂着微笑的慈祥的脸。
冰心爱花,不正是她爱生活的体现吗?她以一个女性细腻温柔的爱去写作,去和读者交朋友。花,爱,作品,从窗台的花,手中的纸,脸上的笑,我仿佛看到了无形的,却又确实存在着的联系之线。
冰心五四时期的创作,是以爱之主题著称的。母爱、对自然的爱、对儿童的爱,是她反复讴歌的内容。读她的小诗,小说,会赞叹委婉和清丽,飘忽在作品中的爱之气息,给人温暖。
花,她在生活中倾心相爱之物,在创作中则成为她的爱之理想的寄托物。最为突出的,无疑是她的成名作——《超人》。
冰心写小说,是用诗之笔去写。无论《斯人独憔悴》,抑或《超人》,她似乎都不曾将人物性格塑造看得那么重,而是着意用清新秀丽的文字,用饱含诗意的情绪,写出她对人生的忧虑和思考,哲理诗化,正是她在小说中力求表现的。
《超人》中对爱的赞美,是曾贯串在她的诗中的基调。有意思的是,整个作品中爱的体现者,不是别的,是花。主人公何彬这个以冷漠待人生的超人的转变,是以花为催化剂的。
何彬不相信人们之间是有爱的。他不理睬别人,也自然没有温暖。于是,“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
然而,当何彬一旦看到禄儿的信,看到禄儿送给他的花,他心中十几年来用冷漠筑起的壁垒一下倒坍了,如同雪人在阳光下消融。冰心是这样写的:
禄儿趁他闭眼睛躺着时,送进一篮金黄色的花,并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我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报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门口看了几次,桌子上都没有摆着花。——这里有的是卖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见过没有?——这篮子里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种的,倒是香得很,我最爱他。我想先生也必是爱他。”
信中讲了许多孩子心中的话,孩子把花同母亲对自己的爱联在一起。作品的精彩处是何彬信念发生变化,感情剧烈起伏的时刻,这里花儿向何彬展开了“强攻”。“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儿,回到床前,什么定力都尽了,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
他哭了,是悔恨旧时的冷漠?是感激孩子的天真和纯洁的爱?是惊诧于花儿的魅力?他变化了,提着禄儿送给的花篮离开了,开始走向新生活。他给禄儿留下一纸悔恨和重又回到心中的热情。
他说:“我这十几年来,错认了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爱和怜悯都是恶德。(尼采)……我必不忘记你的花和你的爱,也请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爱,是借着你朋友的母亲带了来的!”
母亲,花,爱,三者终于在“超人”那里化为一体了。何彬答应送给禄儿一篮花儿,那是用一缕柔丝,将泪珠儿穿起,系在弦月两端,摘下满天的星儿,来盛在弦月的圆凹里的一篮花。
自然天真的禄儿,还难以理解何彬的比拟,他只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看,他奇怪为什么只见信,不见花篮。只好仰着黑胖胖的脸,呆呆地望着天上。从有形的具体的花,到无形的抽象的花,其实意味着从个别的爱扩充到广泛的爱。
冰心用美丽的语言描绘出无形的花篮,反映出她的艺术构思,这无形的花篮,在冰心来说,就是爱,而这爱一般人是难以领会深刻的。
洒进窗户的阳光,忽明忽暗,那是一朵朵云彩飘过。桌面上花影渐渐拉长,那是太阳在缓缓移动。收好冰心递过的月季花征订单,我顺便请她为《北京晚报》写篇文章,她应允了。
“写什么呢?”她想了想,又说:“我觉得医院的病房里应该有花瓶。人住在医院里,重要的是精神愉快。你看我们老人,看看花比什么都舒服。叶圣陶上次住院,我去看他,带了一把花,可就找不到地方放。”“那您就写这个内容吧。”“好!”
没几天,一篇文章寄来了,题为《花瓶》。冰心在文章中建议病房里应该有花瓶,看望病友最需要的是花朵。“看望你的朋友去了,他们留下的花朵,放在床头,它的光鲜和清香,总会使你想起你和你的朋友之间,或其他的美好往事。”一篇短短的不到千字的文章,字里行间,仍跳动着当年写《超人》时的年轻的心!
冰心生活中爱花,是她的性情意趣所在。人们常评论冰心的风格属于阴柔之美,从她对花的偏爱上,不是也可以看到她的个性的特点,看到她的创作风格的内涵吗?作家的个性影响创作,人们说过多少次,要是能深入细致地观察一下作家的那些生活兴趣细节,大概还是会大有裨益的。
冰心年轻时,在作品中赞颂母爱,在生活中,几十年从未减少对花的喜爱。当她住在病房里,寂寞,怅惆萦绕于心时,友人送的花会带着友情温暖她的心。
当她看望朋友时,如果带上一束花,便寄托了她的亲切的慰问。花,一直是她联接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媒介,无怪乎到了晚年,还那么热心地扶植待业青年的月季花种植场。
我看到她那颗充满母爱的心,仍然那么年轻,活泼,她盼望着花儿如她所描述的那样,带着爱,出现在每个家庭的窗台、桌面,出现在每个老人的床前。其实,不仅仅是花,许多能体现柔情的小物件,冰心都是偏爱的。早在二十年代的《给小读者》中,她就这样对孩子们说:
“小朋友,我们所能做到的:一朵鲜花,一张画片,一瞥温和的慰语,一句殷勤的访问,甚至于一瞥哀怜的眼光。在我们是不觉得用了多少心,而在单调的枯苦的生活,度日如年的病者,已是受了如天之赐。”
何止病者,在冰心的感情世界里,温和地待人是持久而普遍的。她以温柔和细腻去感受自然,去感受生活,去撷取生活的浪花,然后再将之用委婉清秀的文字,艺术地再现在作品之中。
她不注重冷静的细致刻划,却擅长缕缕情思的表达,特别是母爱的表现,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她的创作风格的阴柔之美。花,我们说不仅仅是了解冰心生活情趣的一把钥匙,也是了解她的艺术风格的一把钥匙。或许,这是武断的结论。
事情巧得很,距冰心写《花瓶》之后,刘白羽先生也寄来一篇散文《春的使者》,文章也是写花的——他写的是送花人。
元旦那天,两位青年人给刘白羽送花来了,他们就是冰心所支持的那个青年月季花种植场的送花人。原来刘白羽从报上得知,冰心是这个月季花种植场的第一个订户,便立刻给冰心打电话,请她帮助自己也订一份。花送来了。
每周两次给刘白羽送来鲜花。看着紫的、红的、白的、嫩黄色的鲜花,刘白羽陶醉了,他感慨:如果生活中没有鲜花,那将是何等的荒凉和寂寞!
冰心爱花,写花,讴歌花,她的作品就是一朵又一朵的花,给人以温暖的安慰,亲切的爱!
生活中的冰心,不也是同样给人带来爱吗?
想到请冰心题跋,是在1987年。十月,北京举办《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请柬题签由冰心题写。展览过后,我去看她,特意带去请柬请她题跋。
她在内页上写道:“说真话,干实事,做一个真诚的人。冰心,一九八七,十一,十六。”
半年后,我去上海看望巴金,请他也在这份请柬上题跋。巴金在请柬封面上写道:“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写,只是因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里燃烧,不写我就无法得到安宁。巴金,八八年六月十三日。”时隔多年, 两位老人的题跋,多了记忆温暖,多了思想的厚重与丰富。
每次去看望冰心,她都会签名送上新书,但不爱题跋。只有一次例外。1988年6月,她送我一本新出的《关于男人》,是刚拿到的样书,签名之后,她顺手补上:“这是现在我手里仅有的一本。”还开玩笑地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一年,冰心米寿。
冰心的心中一直拥有大爱!1988年,在“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上,萧乾发表感言:“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的确,冰心在精神上与巴金是相知相通的。每次去看冰心,她都会提到巴金。有一次,她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让我看,说它专门用来放巴金的信。
她和巴金的这种诚挚友谊,不只是有着几十年的交往,如何真诚做人方面有着同样追求。我想,两个人精神上从来没有孤独过。
冰心是以历史的反思态度,表现出一个智者的透彻与从容。
九十年代初我请冰心谈巴金。她谈得非常好。最后一句她说:“世界上的问题并不复杂,心里简单就行了。”心里简单,多好!
冰心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我去探望她。她说:“你来晚了,我的遗产都分完了。”我听了,哈哈大笑!
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九岁,也是高寿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