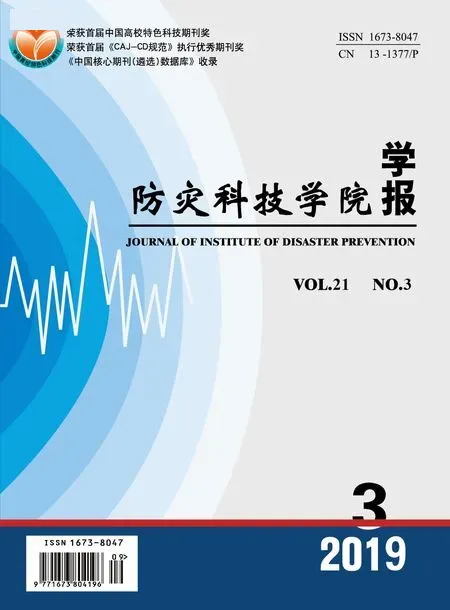东汉时期的地震记录及其时空分布
席境忆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0 引言
历史时期地震研究对于防灾减灾,特别是研究区域地震时空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对历史地震的研究通常分为两类:一、按朝代编年进行断代研究;二、对某次大地震展开综合研究。其中第一种范式受史料保存情况影响,出现了前后时期研究不均衡的情况,以宋代为界,明清时期研究明显数量偏多,宋之以前的研究数量较少。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保留了较多地震记载的王朝,因此东汉地震理应得到学界重视。自邓云特[1]开创统计历朝历代自然灾害发生频次的研究范式以来,众多学者相继效仿此法进行研究,但这一模式的弊病是史料的性质与真伪导致文献所见的灾害情况与实际灾害情况大相径庭。闵祥鹏即指出,这种程式化的范式导致大多数研究毫无新意,结论大同小异,已经失去了灾害史研究的意义[2]。但近些年来东汉震害研究出现了一些突破陈旧范式的新成果。高建国[3]利用郡国平均面积得出了全新的震级—有感面积经验公式。陈业新[4]从灾害的政治社会思想角度出发对两汉灾害进行检视。刘春雨[5]将山崩、地裂等灾害与地震并列讨论,但未能进一步指出三者之间的异同。王文涛等[6]则指出,东汉洛阳地震记载偏多并不能完全说明洛阳本地地震频发,而是与洛阳的都城身份密不可分。冯锐等[7]在高建国的公式基础上进行了全新参数推定,并对不同史料的书写特点进行归类。
以上研究从不同方面推动了东汉震害研究的进步,但亦存在尚可完善的地方。如前所述,东汉的文献记载中,与地震类似的地裂、山崩,这二者与地震是什么关系?我们虽然不能根据文献记载盲目推定当时的灾害时空规律,但能否得出文献记载本身的时空分布规律?这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建国以来,学界编订了众多历史地震资料汇编,例如中科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8]、 李善邦[9]、谢毓寿等[10]、顾功叙[11]、刘昌森[12]、刁守中等[13]的汇编,几乎都没有区分地震与山崩、地裂之间的关联,而只是收录带有“地震”“地动”字样的史料。这一做法虽然简便,却有可能遗漏诸多历史地震信息。高建国[3]便提出“地动”与“地震”的不同,其依据虽可商榷,但指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一些历史地震由于各种原因,不一定直接记载“地震”这种标志性的词语。
1 山崩、地裂与地震
1.1 山崩与地震的关系
东汉地震记载保存在《后汉书》《两汉纪》《东观汉纪》《三国志》《通志》等典籍中,其中《后汉书》保存了大多数这一时期的记载,本文即选取《后汉书》为研究案例。《后汉书》中涉及的地质灾害有三种:地震、山崩、地裂(或称地坼)。对于地震,大家都很清楚,重点是后两种,山崩与地裂。按照现代地质学的解释,山崩是由于降水或地震等原因导致的山体滑坡、塌方等山体崩塌事件,而地裂则指由于构造活动等内力或外力作用形成的地裂缝。但今人的这些地质学知识是在现代地质学建立后才得出的,东汉时期对于这些现象有另一种解释。比较常见的有,利用“天体错行”理论解释地震原因。这一记载常保存在《天文志》部分;另外还有利用五行理论解释地震原因的,这些记载多见于《五行志》;此外,有少数学者认为地震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与人事灾异无涉,这一观点以王充的《论衡》为代表(1)张树清、雷中生、李秦梅:《中国古代的地震成因理论》,《地震研究》1996年第3期,第302页。。
汉代对于自然灾害的探讨,多建立在“灾异论”的基础上。学界就灾异论已有相当多的论述[14-16],正是这种理论,使得当时对自然灾害的讨论,不可能像今天一样“理性化”。
《后汉书》是记载东汉历史全貌基本史料,其中所收录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中有专门记载地震事件。且范晔所做《后汉书》纪传部分记录的地震与司马彪《续汉志》记载地震事件大体吻合。考察东汉地震,当以此书作为基本依据。
人们对知识的理解应用始于对知识进行分类。在两汉时期,地震、山崩、地裂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汉书·五行志》记载鲁僖公时期一次山崩事件为“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17]。从这句简短的记载来看,似乎和地震并没有任何关系,但后文记“《左氏》以为沙麓,晋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书震,举重者也。”[17]意指这次山崩是由地震引起,但因为山崩比地震更严重,因此记录山崩不记录地震。但《左传》与杜注实际上均未提及“不书震”的缘由,甚至比《后汉书》晚出的孔颖达《正义》也未提及。可见班固声称这一解释出自《左传》并不可靠。查《汉书》此段论述,先后引用《谷梁传》《公羊传》《左氏传》《春秋繁露》《国语》及京房《易传》等文献。“不书震,举重者也”这一句式常见于《公羊传》。《公羊传》此事原文为“沙麓崩,何以书?记异也”。[18]《春秋繁露》相关事件记为:
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为之食,星陨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陨霜不杀草,李梅实。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19]
《春秋繁露》这段史料中涉及了前述所有沙麓崩、梁山崩(文公五年)、地震等一系列事件。从以上史料来源看,班固或有可能混淆了这几个不同的事件、文献,导致误记:将僖公十四年地震误看作《春秋繁露》同段中的文公五年山崩。此次山崩又与地震记载相连,随后班固套用《公羊传》“记异也”的说辞,写成了“举重者也”。总之,没有证据表明沙麓崩与地震有关。但班固这一记载并非无用,这一说辞能被纳入《汉书》,说明当时确实有地震“不书震”的情况存在,否则班固不会如此轻信。因此,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于地震、山崩关系的解释——当山崩是因地震而起时,有时会直接记载山崩,不记地震。
山崩的原因众多,除了山体本身结构的原因以外,绝大多数山崩都是由于地震、强降水导致。《后汉书》中记载了初平四年的一次山崩。“(初平四年)六月,扶风大风,雨雹。华山崩裂”。[20]华山可能也受到了这次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导致山体滑坡。宋代一则史料更具说服力。《华州志》记载“宋熙宁五年九月华州少华山摧陷于石子坡”。[21]这次山崩的原因就是“数年以来,谷上常有云气,每遇风雨即隐隐有声。是夜,初昬略无风雨,山上忽雾起,有声渐大,地遂震动。不及食顷,即有此变”。[22]连年累月的降水使得山体最终崩塌。
确立了这种认识,再看《后汉书》中一些山崩的记载就更容易理解。《后汉书》的山崩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单独一座山崩塌。二是一个小区域内多座山崩塌,如“(永初)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员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延光二年七月,丹阳山崩四十七所”。[20]三是多区域多座山崩塌。单独一座山的崩塌事件很难断言其与地震有关,一个小区域内多座山崩塌也难以推断,但多区域多座山体崩塌基本可以断定是由地震导致,因为单发的、不因地震导致的山崩很难影响到一个较大的区域。而一次较大的地震则可能在多个烈度较大的地区引发山崩。例如永和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20]这次地震便触发了山崩、崖岸崩塌、地裂缝等多种次生灾害。
《后汉书》还有很多这种记载,现列举如下:
(建和三年)乙卯,震宪陵寝屋。秋七月庚申,廉县雨肉。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京师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诏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赎,各有差。郡国五山崩。
(永寿元年)巴郡、益州郡山崩。
(建和)三年,郡国五山崩。[20]
这三处山崩记载中,第一处和第三处所记应为一事。明确表明了是由地震引起,第二处未直接表明诱因,但因各山相距甚远,故应非降水,疑因地震所致。《后汉书》中还有一则山崩史料,是延熹四年“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并颓裂”。[20]这则史料将山崩与地震连记,似乎存在关联,但细查地震地点和山崩地点,相去太远,定非地震所为。
历史地震研究最基础的一环是核定地震基本参数,如发震时间,宏观震中,地震烈度,地震震级等。历史地震烈度评估方法异于当代地震烈度评估。李善邦[23]最早提出历史地震烈度及震级评估方案。随后李群等[24]对方案进行了进一步完善。鄢家全等[25]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历史地震烈度表(简称2010表),这一烈度表方便实用。以建和三年地震山崩为例,此次地震引发郡国五山崩,查2010表,当对应X度区“山多崩裂”一条[25]。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地震由于缺乏仪器记载,历史地震烈度判定受研究者主观影响很大并不精确,这也就是为何不同研究者研究同一次地震会绘制出不同等烈度线图的重要原因。此外,烈度判定应当综合建筑物、结构物损坏和地表形变等多方面因素考虑,单纯从一个视角判断也容易出现较大偏差。
1.2 地裂与地震的关系
《后汉书》中与地裂有关的表述较为复杂,还有地坼、地陷等名。前者与地裂并无二致,而地陷与地裂所指有交叉部分,应注意分辨。
例如永建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师地震,汉阳地陷裂”。[20]《续汉志》记载此事为“顺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汉阳地震”。[20]虽然著作不同,但写作都应采用社会通行表述,因此此处“地陷裂”可以理解为由地震引发的地裂。
地裂与地震的关系更加密切。《后汉书》可见如下表述:
(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20]
同一事件,《续汉志》有“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国四十二地震,南阳尤甚,地裂压杀人”的记载[20]。类似还有元初六年,“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20]建光元年“冬十一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坼裂”(2)《后汉书》,卷5,第234页。《孝安帝纪》载“(建光元年)冬十一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坼裂”。同样之事,《续汉书·五行志》记为“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坏城郭室屋,压杀人”。检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可知,建光元年九月朔日为己卯日,十一月朔日为戊寅日。两月都可能出现己丑日,有一处当误。钱大昕也提出质疑,但未进行深入考订。沈家本在《后汉书琐言》中认为“此纪后文有冬十二月,不得重言冬,上文书九月,又书戊子,戊子与己丑相接,然则冬十一月四字为衍文也”。沈说应是,则此次地震应为九月。。建武二十二年的地裂和地震显然同义,元初与建光年间两处记载的地裂则是直接作为地震景观出现的。
地裂缝的成因较之山崩更为复杂,但这并非本文探讨的主题。现代地裂缝多发于一个或两个相邻城市这种小范围区域内。《后汉书》中关于地裂的记载与山崩类似,同样有三种:一地独发;一地多发;多地多发。第一种模式的记载较为细致,如“灵帝建宁四年五月,河东地裂十二处,裂合长十里百七十步,广者三十余步,深不见底。”[20]这一史料记载了地裂缝的尺寸,数据十分详细,但却未言及地震,故此次事件应并非地震导致。多地多发的记载数量也较多,记载的范围已然跨郡县,分布极广,显系地震所致。前文已经列举数例,都是说明地震情况再描述地裂,也有类似记载只说地裂,并未提及地震,此类记载有二:“(建和元年夏四月)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20]“(永康元年)五月丙申,京师及上党地裂”。[20]两处记载应视为地震所致。其中,《后汉书》在建和元年的地裂事件前,还曾记录一次地震,即建和元年“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20]两次事件均居于四月,让人大呼巧合,恐也存在关联。
2 东汉的地震文献记录的时空分布
2.1 文献记录中发震时间规律
《后汉书》的地震记录呈现出很强的时间分布规律,即永初元年以前的地震事件记录极其稀少。这一点学界的讨论较少。冯锐[26]曾指出,有学者依据文献记载,认为东汉时期地震集中于中晚期的看法是荒谬的。但他随后解释,东汉前期地震记载较少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政局安定,并就此得出结论,“我国历史地震的系统性记载实际上是从汉和帝开始的”。对于这一解释我们尚存异议。至少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可见许多地震记载。以《汉书》为例,仅本纪部分,就有《惠帝纪》《高后纪》《文帝纪》《景帝纪》《武帝纪》《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哀帝纪》等。如果仅以地震记载数量来权衡是否形成系统性记载,那么至少在西汉就已经形成了,反而是东汉前期,这种传统却丢失了。这岂不荒谬?陈侃理[14]在研究中也认为,官方灾异记录的制度自秦汉便已开始。再回过头来看冯氏的解释,如果真是因为东汉中后期政局动荡,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增加地震记载,那么政局同样动荡的西汉晚期为何没有增加地震记载?显然,这一解释是说不通的。
笔者认为,这或许和东汉地震记载的散佚有关。《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20]
依据此说,东汉时期众多档案典籍在长途迁徙过程中不断被毁坏、遗失,后又经历战火,损失殆尽。涉及地震的记载很可能也夹杂其中,毁于一旦。
这个推断可以从《续汉志》得到印证。《续汉志》记载灾异事件是按照一定次序的,即先将事件分门别类,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在《五行志》前五个部分中,记录的灾异事件很少有发生时间早于汉和帝永元年间的。在第六部分记载日月变化时,则比较详细,有较多永元年以前的记录。这是因为天象星占,尤其是日月占的独特地位所致。司马迁在《天官书》中说“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大)[天]人之符”。[27]赵继宁[28]认为这代表着日晕、月晕,日月食、云气、风最能反映天人关系。另外,关于天象的记载与其他灾异事件记载分属不同机构,这也会导致二者文献留存情况不同。《续汉书·百官志》记载: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刘昭注:《汉官》(仪)曰:“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许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请雨、解事各二人,医一人。”)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刘昭注:《汉官》曰:“灵台待诏四十(二)[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十二人候气,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钟律。一人舍人。”)[20]
所谓“候风”“候气”“钟律”,李零[29]认为分别指是指阴阳五行中的风角、五音、五音十二律。这一看法大致不差,但显然候气与钟律互有交融,这与刘昭注的记载是矛盾的,需要调和。候气的重点是落在“气”上的,方法是通过音律进行占候。王玉民[30]指出“律”“历”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以律候气,候气定律”。沈括《梦溪笔谈》也记有候气,写道“司马彪《续汉书》候气之法,于密室中以木为案,置十二律管各如其方,实以葭灰,覆以缇榖,气至则一律飞灰”。[31]
这些记载清楚地表明太史令属下分工极细,不同人员专事不同观测记录。加之日月占本就在星占术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政治寓意最为重要,因此日月星象变化的记载更不易散佚,保留也更丰富。
2.2 东汉文献记录中的地震的空间规律
笔者采用ArcGIS软件将《后汉书》注明了地点的地震事件绘制成图(图1)。需要强调的是,地图上各点不代表地震震中,仅是有感地区。冯锐[32]指出,东汉时期地震记载只是写明地震有感区,所谓“xx地震”只代表这一区域有震感,并不能说明震中在此。因此,诸如“京师地震”等记载并不能用于说明洛阳盆地的地震活动。

图1 《后汉书》记载地震事件空间分布(3)底图未采用东汉政区图,而是利用当代政区。此图只收纳了史料记明地震发生位置的地震,对于叙述不清,如“郡国X地震”此类,一概不收录,对于山崩、地裂信息也不收录。此外,一般地震记录只言明州郡级别政区,作者在制图时选取这些政区的几何重心作为标记点位置,特此说明。Fig.1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s recorded in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从图中可见,东汉地震文献记载多分布在北方地区,几何形态呈现“十”字状,除今甘青一带分布走向为西北方向外,其余大体沿东西南北正方位分布。纬度集中在34°,经度集中在112°,东西与南北走向在今洛阳一带交汇,明显呈现出两个地震高发区,中心分别位于洛阳和陇西郡(广义来讲是凉州刺史部)。前文提到,这一时期的地震记载只是记载有震感的地区,因此洛阳地震记载繁多并不说明洛阳本身地震多发,而只是洛阳处在这些地震的有感区域内,加之洛阳是政治中心,一次轻微的地震也会被解读为政治事件。地图上南北分布与东西分布交汇于洛阳,这一点再次充分说明《后汉书》地震记载强烈的政治意味。(4)国家地震局地球所与复旦史地所编修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远古-元朝)》将两汉地震频次绘制在一张地图上,地图显示,西汉时期地震记载最多的地方是长安,这和本文结论可以呼应。另一个中心是陇西。这一地区并无太多政治含义,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段属于西北地震带的活跃期。
正是由于东汉地震史料保存不全面不平衡,因此我们不能就已有的史料得出东汉地震时空分异规律的结论。(5)学界多根据已有记载推测两汉地震发生规律,这是不科学的。但本文仅探讨文献记载的时空分布。其次,如前所述,地震活动周期并不与政权更迭周期保持一致,单独研究某一断代地震周期规律的意义主要在于辅助政治文化史研究,而对于防灾减灾来说意义有限。
3 结论
通过对《后汉书》等文献的分析,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地震、山崩、地裂三种记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历史地震研究中,不能忽视对后二者情况的记载(这一点不只局限于东汉)。其次,东汉地震文献记载的时空特征强烈。空间上呈现双中心的“十”字形分布,这一方面反映了地震与人事政治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局部地震活动频次。东汉早期缺乏地震记载,可能是由于相关档案文献丢失所致。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史料的不全面、不平衡,我们切不可根据现有史料盲目对东汉时期全疆域地震的时空分异规律妄下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