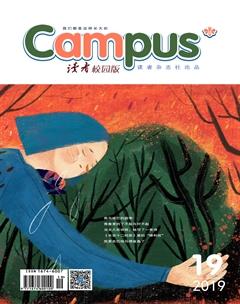青春里的了不起与对不起
闫晓雨

如果你知道10年后的自己依然不够优秀,还愿不愿意全力以赴呢?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人。10年前如此,10年后也是,青春期里的敏感少女长大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活在自己内心世界里的城市边缘人,这本身并不奇怪。比较特殊的是,偏偏我还是个焦虑感特别严重的人。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分文理科,家人都让我选理科,我却坚定地选择了文科。嘴上笃定,内心忐忑。
“我选择文科,是因为有更多写东西的机会。”我真正开始写作是在高二上学期,忽如一夜春风来,内心飘起的雪几乎要覆盖整个春天,不知道从哪里爬出来的小虫子蠕动着,松动了我原本贫瘠无聊的青春。我开始没日没夜地沉迷在文字中,如同一种本能,锃亮地,击醒了我。
当时家里还没买电脑,我就把厚厚的手稿带进网吧,再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在文本里。我郑重地投稿,再看它变成杂志上的铅字。
其实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写作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意味着什么,只是喜欢,只是忍不住。如同一个贴身的口袋,我看到什么漂亮的、新奇的、好玩的故事都想立马把它们装到里面去。偶尔拎起来,掂一掂,有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每个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神秘口袋,你可以称之为天赋,也可以称之为特长。有人幸运,很早就可以摸到这个口袋。有人的惊喜来得缓慢,读书以后,工作以后,会慢慢找到它。但可惜大多數人可能摸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口袋里的东西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10年前,我只是误打误撞选择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路。如果真有时光机可以回到当时的自己身边,我一定会给她一个拥抱,谢谢她,在我15岁的时候,用蛮力帮我找到了一辈子的热爱。
我还会去安慰那个自卑少女,不要担心自己不够好,因为你还年轻,年轻就意味着机会,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靠近自己想要的人生。
前几天,我读到1902年秋天,正处在青春期的奥地利作家卡卜斯写给好友里尔克的信,对方在信中回复道:“亲爱的先生,我要尽我的所能请求你,对于你心里一切的疑难要多多忍耐,要去爱这些‘问题的本身。现在你不要去追求那些你还不能得到的答案,因为你还不能在生活里体验到它们。―切都要亲身生活。现在你就在这些问题里生活吧。”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我这次回家乡小镇是为了参加好朋友楠楠的婚礼,婚礼办得很热闹,站在她身边的我,是伴娘,和我们曾经约定好的一样。
这不是嫁出去的我的第一个小姐妹了,从大学毕业到现在,陆陆续续,我已经参加了好多次婚礼。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办单身Party,在布置好气球、蜡烛的房间里说悄悄话,在唱到《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时,大家伙儿莫名其妙就红了眼眶。那时的我们,虽然步入社会,但到底没受太多侵蚀,还是有力气折腾的。
到楠楠结婚前一天,我们都懒得出去嗨了,几个人喝完下午茶,就坐在车里哼唱着周杰伦的歌曲。天空飘浮着的云朵,聚散离合,像极了现实。
我开玩笑地说起10年前自己的心愿:如果不能嫁给爱情,那我想嫁给自己的青春。
有点儿羞耻,其实我从小就想嫁给自己好朋友的哥哥、弟弟或者是隔壁班的同学,总之就是非常想让自己所嫁之人或多或少参与过自己的青春。
不过现在,隔壁班的男孩不知去向,自己曾经暗恋过的和暗恋过自己的人都已成为“故事的小黄花”,在这样一个悠闲的午后,被三月的风打乱吹散。
我想起10年前也曾有可爱的动不动就脸红的少年,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站在教室门口等我。那种自觉而默契的雀跃感后来很少再有。
当年没说出口的“对不起”,最终只化作―声叹息。和懂不懂得珍惜没关系,有些人的出现,就只是能陪对方走―段路。
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有段话说得很平实,却直戳人心:“没有人告诉我长大以后的我们会做着平凡的工作,谈一场不怎么样的恋爱,原来长大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会犯错,还是会迷惘。”
其实这些年来,我真没经历什么特别的跌宕起伏的、能够被称之为旖旎风光的故事。不过是正常的上班下班加夜班,爱人被爱共幻灭,有特别努力的一面,也有把自己关进小黑屋的“丧丧”的一刻。
落了灰的生活胶片一卷又―卷,“至暗时刻”倒真没遇到。状态不好的时候也绝对不允许自己彻底沉沦。坐在小区的木椅上和老朋友打电话,出门散步,坐很久的公交车去欣赏北京的夜景,每天尽量保证完成工作,不给身边的人添麻烦。不管心情多糟糕,都不能让赚钱的机会逃掉。这就是我成年后经常要面对的状况。
有一句流传已久的歌词“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失去的才是人生”——我不同意这句话。真实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一种得到是灵光乍现,我们一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事物,工作、爱情、机遇,都是基于自己过往的种种行为和选择。
没有办法,我们的人生不是一页清单,可以简单盘算,而是一场盛大而庞大、参与人数众多的舞台剧。
如果可以回到10年前,我想,我不会改变自己的青春轨迹。我只会对那个无知亦无畏的女孩说,尽情去享受这些时光吧。如同余世存所说:“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