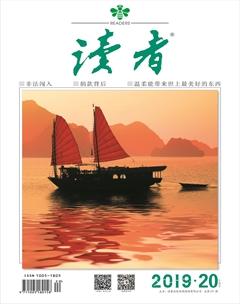神奇的左手
冯骥才
谈到雨果,我想起当年读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二部的《滑铁卢》时,有几句写景的文字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门前草地上,倒着三把钉耙,五月的野花在耙齿间随意地开着。”
我当时就想,这不是作家的思维,而是一种画家的思维。这种例子在雨果的作品里还有一些。雨果哪来的这种绘画思维?这次我明白了,他本人也是个画家,一个真正的画家。
巴黎孚日广场雨果故居的第二层,几乎是雨果个人的绘画展。此前,我不知道雨果善画,所以起初我以为这是跟雨果同时代的一位画家的作品,大概由于内容上与雨果有什么特殊关系而被挂在这里。当陪同的法国朋友说这是雨果本人的画作时,我非常震惊,因为这些作品看上去非常有个性,技术上也完全称得上出自一个职业画家之手。

东方景观/维克多·雨果/1837年
雨果的画尺寸不大,他用铅笔、钢笔、水彩画笔(毛笔)和一种墨水似的黑颜色作画,此外他不再用其他颜色。这使他的画看上去有点像中国的水墨画。他喜欢在棕色的纸上作画,这样一来还有点像中国的古画呢。他喜欢画古堡废墟、樯倾楫摧、荒村野岭、狂风恶浪,以及妖怪与神灵。这些画大都是他文学想象的延续。他的漫画人物很像小说的插图。他的技术非常纯熟,好像他天天都在作画,运笔的速度很快,笔墨挥洒得自由又放纵,画面上有很强烈的氛围。
他的画阴郁、浓重、迷惘、荒凉、古怪,而且有一种神秘感。神秘感是很难画出来的。像八大山人、徐渭、米罗、蒙克、马蒂斯的画都有一种神秘感。雨果的神秘感大概来自一个作家的心灵。因为作家所关注的事物总是具有神秘感的——无论是一種生活还是一个人的个性。还有一些主题,比如爱情、命运、生命、死亡以及地域文化等。
如果没有神秘感,作家就失去了写作的欲望。这也是许多作家老了之后,大彻大悟反而写不出东西来的真正缘故。就本质而言,文学的魅力便是一种神秘感。由于作家的这种天性,雨果对遥远的东方兴趣极浓。他的故居三楼有一间茶室,他称其为“中国茶室”。
这间用来款待朋友的小客厅,完全是他自己设计的。他用很多从中国舶来的物品装饰这间茶室,有家具、壁毯、神像、瓷器、琉璃、木雕、竹帘画和卷轴画。我认出,轴画为《三星高照图》,竹帘画上是《白蛇传》的故事片段,神像为浙江东阳一带的朱金木雕,瓶子应是乾隆年间民窑的,素白釉的观音像是定窑的。房子中间摆着一座朱砂大漆瓶式古玩架,一看便知是清代早期的物品。

雨果故居陈列品


为了强化东方情调,整个茶室使用古老中国喜爱的颜色,如石青石绿、朱砂赤金,显得庄重又沉静。他还请人制造一些中国式图案的浮雕挂在四壁上,如神怪奇兽、珍禽异卉、杂技人物、博古器物,其形象都是神奇飘逸、雍容典雅的,这便是那个时代(1840年以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社会集体想象”了。这种温文尔雅的想象与遥远的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述一脉相承。但是到了1840年以后,西方人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变了,变成了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气质》中的那个样子。
话说回来,雨果的“中国茶室”同样体现了他绘画中那种对神秘事物的兴趣与关注。他不是对表面的视觉效果感兴趣,而是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他的内心。只有好的画家才这样,因为真正的画家都是为了呈现自己的内心才画画。
一个有多种才能的人,动用他所具备的第二种才能时,一定源自内心的渴望。因为,文字只能描述心灵,却不能将心灵可视地呈现。唯此,雨果才用左手拿起画笔。任何一种艺术都只能表现某一部分内容。文字写不出钢琴发出的瞬息万变的声音,也描绘不出调色板上那成百上千种色彩。
所以,只有当我们看到了雨果、歌德、普希金、萨克雷、布洛克等人的绘画时,我们才会更全面而深刻地了解他们。我所说的了解,不是指他们的才能,而是他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