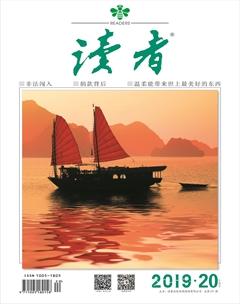从巴黎到池上乡村,我找回了平衡
蒋勋
2010年,我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经历了那场生死劫难,我突然觉得,是不是应该换一个环境,为自己的身体节奏做点调整?多年来,在台北生活,在巴黎读书、绘画,我似乎永远生活在大都市,是不是应该做些调整?
年轻的时候,我常常背着背包四方游走。我去了巴黎,去了纽约,去了世界上很多地方。我走过风华,也走遍空寂;看遍美景,也看过荣枯。而今,从心所欲的我更愿意回到池上——这是地处台湾东部的一座小村庄,写作、画画、散步、读经,以最少的物质需求过最简单的生活。
我找到了自然的秩序,也找到了自己内在呼吸的秩序。我明白了孤独即生活。
这几年来,我每天早上走1万步,傍晚走1万步。用手机拍摄了六七千张照片,随时随地记录这片土地的四季更迭、节气变换,分辨五谷,看云观岚。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只是一个平衡。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在池上,我找回平衡,让时间慢下来。
池上的农民,是我真正的老师
很多人回到自然里,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会嗅到水稻在抽穗时散发微微香味,稻穗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胴体,仿佛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再慢慢变红。
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农民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家。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而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景象,了解并學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
人不会青春永驻,如何在青春的盛放之后,在绿荫中安静地享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好的,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池上的农民,是这一年半里我真正的老师。农民在土地里劳动大半辈子,身上有一种稳定性,丰收时到土地庙拜拜,而遇到歉收的年景,虽然一年的努力白费,但他们还是会去土地庙拜拜。
我常常问自己:我真的傲慢成这样吗?有成就,感恩;如果没有,还能感恩吗?我有时会怨怒,可是农民永远感恩,他们觉得永远要敬天地,因为其中有你不知道的因果。

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偶像,之前可能是托尔斯泰、猫王、披头士,我现在的偶像却是农民。原来真正的伟大是平凡做人,做平凡到别人不知道的人。
身体也有日历,需要找回自然的秩序
刚刚来到池上时,我被一间简陋的房子吸引住了。这间房子原来是退休老师的宿舍。我一进去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红色砖墙的黑瓦平房,刷着绿色的油漆,有很多窗户,还有很大的院子。恍惚间就觉得那是我10岁左右随当公务员的父亲所住的宿舍,我立刻决定住在这里。
我用木板钉了一张画布打算作画,却经不住诱惑,经常往外跑。刚开始的一两天,我待到晚上8点钟也没画出来。去街上吃晚饭,发现所有餐厅都关灯了,就挨户敲门。村民很惊讶:为什么会有这个时候吃饭的人?我这才发现,原来身体也有日历,身体也需要找回自然的秩序。
对于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身处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大概是没有感觉的。过去,文明跟自然之间是有沟通和对话的,但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身体跟自然被一个无形的东西隔开了。
在都市里,我们几乎丧失了对晨昏的感觉,开灯就是早晨,关灯就是晚上。来池上后,我开始按照池上的晨昏作息,晚上8点钟入睡,早晨四五点起床工作,坚持下来,身体竟然好了许多。
有比时间、岁月更昂贵的东西吗
今日的乡村还有许多同样美丽的角落。听到一个妈妈拿着两个新摘的丝瓜,像是抱怨又像是欢喜地向左邻右舍询问:“一早起来,门口摆了两个丝瓜,谁送的啊?”没有人回答,大家笑着,仿佛觉得这个妈妈的烦恼是多事。
我也常吃到他们腌的梅子,晒的笋干、菜脯。有一天得到叶云忠家的鸡汤,味美甘甜得不可思议,我问加了什么,他们说:“只有腌了14年的橄榄……”
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像藏着宝,14年的橄榄、18年的菜脯,市场上买不到——不是价格昂贵,而是时间珍贵。在一切求快的时代,我们失去对物质等待的耐性,没有耐性等待,会知道什么是爱吗?
有比时间、岁月更昂贵的东西吗?我们还有耐性把橄榄放在瓮中,等待14年吗?我们还有耐性让菜脯放18年吗?不发霉、不变酸,这18年,是如何细心照拂才能有这样的滋味?面对许多菜脯、橄榄,小小的物件,我总是习惯合十敬拜,因为岁月如金,这里面有多少今日市场买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