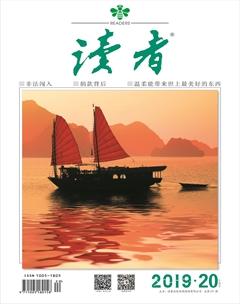一条路走到黑的家伙
张炜
打开文学史,也许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些作家一生都在书写一个大的主题。当然某个阶段会有一些旁逸斜出,但大体上还是一直向前的。比如托尔斯泰、鲁迅或李白、杜甫,再比如当代的马尔克斯和索尔·贝娄——他们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以及故事的背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固定化了。
打开索尔·贝娄的书,发现他永远在写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穷困潦倒,面对诉讼、黑人的逼迫,面临着黑手党和离婚等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有些不满足,会想:怎么又是犹太人?怎么又是这一类故事?但是作家特别自信,也特别有力量,所以他们才敢一直这样写下去。这个难度很大。
一个画家可以无数次画一朵梅花,画几只虾、几匹马,画得再多、再重复,不但不被诟病,反而会获得赞美,他会因此被称作画梅、画虾的大师,画马的大师。但作家不行。作家在写作对象以及其他方面的重复,一定会被指摘。所以从事文学创作,路会越走越窄。这次成功地写出一种人物,下次就得绕开,而且还得绕得很远;写出一种思想,以后离这种思想得远一点;采用一种结构,以后离这种结构方法也要有点距离。
但正因为如此,文学对整个文化传承和文化积累,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思想和文化艺术的含量也最高。所以说文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文化结构的核心。

文学之所以具有这种崇高的地位,是因为它具备极端的发现和创造的属性。这种创造形式逼迫创造者不断地走向深处和高处,直到最后抵达。
可是那些大作家一生诠释的却几乎是同一个主题,表现的是同一个生活领域。因为这些作家有更大的野心,有特别的自信和能力。只有一般的作家才不停地变换,从主题到人物,再到故事。他缺乏持久的探索力和创造力,没有走向纵深的坚韧的开掘力,所以只能更多地求助于外部色彩的变化。
杰出的作家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都挺住了,胜利了。他们作品的细节让人感觉似曾相识,人物或场景似乎在某些时候闪现过——如果耐心地读下去,又会发现探索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不同的作品汇合起来,形成了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他不断地拓展这条河流的宽度和深度。
托尔斯泰也许一生都在写“托尔斯泰主义”,所谓的勿以暴抗恶。马尔克斯一辈子在写孤独和魔幻。福克纳总是写那个庄园,白人、黑人以及土地的故事。他们一生的主题是贯穿始终的,描述的生活领域也是相对稳定的。可是这非但说明不了他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萎缩,反而表明了他们更加强大,更有自信。事实上只有他們才能够这样做。
他们不需要外部色彩的装饰,不需要变来变去的机灵。他们走在一条大路上。
当然,重复是可怕的,不仅是情节的重复,还有语言的陈旧、思想的停滞、意境的狭窄。故事倒是容易出新,描写领域也容易挪移,但是对于艺术和思想的开掘,对于人性经验的延伸,往前走一寸都是困难的。
杰出的作家在这些根本的方面是日益精进的,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持续追究、寻根问底——只有不会阅读的人才会说他们重复,不知道这种“重复”,恰恰是最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