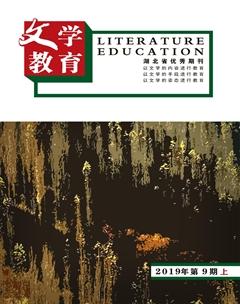“在场”与“旁观”
一直以来,如何处理个人与现实的关系,始终都是诗人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不但关系到诗人对生活的现实态度如何,更关系到他是以显性还是隐性的表意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我们非常欣赏单刀直入、直接介入现实存在的那样的勇敢诗人,比如杜甫、白居易,前者以直接批判的姿态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三吏”与“三别”等诗篇,后者直接秉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理念写出了大量的“新乐府”;但同样我们也欣赏那些以婉转、隐喻的方式来批判现实或者发掘内心的以退为进的诗人,比如屈原、李白、李贺与李商隐,他们深潜胸臆的优秀诗篇也折服了后世无数诗人。大体而言,前者是以旁观者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然后进行介入;而后者则多是直接在场,有身历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身历性的诗歌无论写外在的发生还是内在的隐秘,都有在场的佐证。故而体验的自足性是深刻的。石棉的身历性诗歌就体现出明显的这种特征。比如他写“不确定性”,把楼房比喻成塔或者树,这样人进入楼房便就有了两种想象方式。很显然,这种体验完全是由作者的内心所决定的,如果作者把楼房比喻成三种或者更多的事物,那进入楼房的想象便随之有了相应的种类上的改变。这是自足性的一种理解。另外一种自足性理解,则体现为体验的深刻性。比如石棉的《夜半醒来》,写鬼魂们在院子里聊天,然后作者想向他们打听一些事情。很显然,这些鬼魂就是村里此前死去的乡亲们。作者无论对于身历的人还是身历的事都是关心的,但作者不写现世,而是通过对“死去者”的强烈关注来呈现这一点。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令人震撼的。其《可恨的遗传学》写家族的疼痛,表现那种对亲人又爱又恨的内心焦灼,也令人感到不安。由于这种疼痛乃是一种命定的疼痛,所以这种体验只有身在宿命感之中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体验乃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的,必然是深刻的。
当然,以上方式所做的理解,并非就是否认“旁观者”诗学的深刻性。有时候,愈是冷静的观察愈能体现出这种深刻。比如诗人写《城西小巷》,其中的“锁匠在树下挂出一排钥匙,他坐着/摆弄旧锁芯、锉刀/总要弄出点声音,碰撞或者磨损的声音”,这样的描写,虽然是日常的,但又带着普遍性的深刻。诗人说,锁匠总要制造出一点声音,这是存在的一种象征,因为对于人而言,生活本身没有什么,就是“具体的情节”。再比如诗人写“一阵风”,风中的那一只斑鸠,在秋风到来之时,“她睁着眼,接受此刻/世间最浩大的袭扰,似乎从未想过/应该从现有的世界里移开”。这亦是生活之一种。“有意制造声音”和“睁眼接受袭扰”,这背反式的合一,游移起来不正好就是这个纷扰的世界的全部么?
以龃龉或迂回之术来处理现实的模式,还有一种故事体。诗人通过虚拟人物或者事物的方式来讲故事,而将自己置身于故事之外,成为一个旁观者。然而这个旁观者又恰恰是清醒的,他深谙故事中的“黑幕”,但是叙述起来却又显得冷静异常,但在最后又必须给予这个“黑幕”以无边的“诅咒”,以期待换来一个快刀斩乱麻式的光明前景。我觉得石棉的《这些草活着是为了被割倒》就是这样的一首好诗。诗中的草、阳光、虫子和收割机都是带有隐喻性的意象,诗人以它们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来措置当今世界中所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让人隐隐约约感受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充满了隐忧。这首诗虽然是一个模糊的表达,看不到正面的反抗,但是诗人对历史情境的处理却是深邃的,因为它给阅读者带来了深层次的震惊,并且让人颤栗。诗歌的结尾很显然是一个童话性的表达,因为诗人的理想太过于“理想”了,我相信诗人以“割草机轰轰地开过来”这样的表达所要坦露的寓意一定是期望“斩草除根”的,他或许没有预料到“这些草”会有“春风吹又生”的顽抗力以及死灰復燃的“能力”。然而诗人有一种神圣的责任,那就是他必须为全人类的“理想国”负责,所以他的叙述必须要是决绝的。也唯有如此,它才符合诗人的情性与格局。我相信,谁都不会认定这是一种怯懦的表达,尽管它避开了“直面现实”的叙述策略。它固然是一种旁观者的叙述,然而那种要介入的力量却显得异常强大。它是一种“变形”的艺术,然而现实感却丝毫没有缺席。相反,这其中通过转换聚集了双重的力量,因为这首诗同时具备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文学形态,仅此一点,你的想象力就已无法与文本之间的张力相抗衡。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