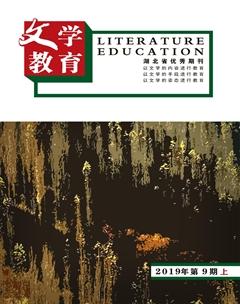可恨的遗传学
石棉
1.关于不确定性
大冷的天
看西边的楼房竟比以前瘦了很多
像塔,也像树
我走进去。天冷,声音也寂静了
我独自在里面走
要是走在塔林,我会变成
冥思的僧人
要是走在树林里
我就应当变成一头
暗怀杀心的野兽
2.夜半醒来
鬼魂们在院子里说话
谈论麦苗、番茄,这类
生前赖以活命的植物
谈论黑夜,反光的高塔,圆球状阳间
苦难的更替和无限
多么惊讶呀
它们洞悉世界的奥妙
我去院子坐下
风轻,朗月照透天穹
我感到清爽,像脱掉了沉重的肉身
时间停滞,身边坐满鬼魂
我想打听一些事情
我想知道,夏天枯死的秧苗
在阴间长势如何
是否结了满意的籽粒
死于盛年的乡亲们
是否依然靠一把蛮力
才能够在阴间勉强活下去
3.城西小巷
把叶子掉光,把落叶
铺满城西的小巷,两排慈眉善目的老树
冬天里,只做这样一件事
锁匠在树下挂出一排钥匙,他坐着
摆弄旧锁芯、锉刀
总要弄出点声音,碰撞或者磨损的声音
岁月在这里更像是一些
具体的情节,有时是梧桐树迎风流泪,有时
是锁匠垂头打磨手上的老茧
4.景 物
空荡荡的老街
如果此时有人走过
我会把他写进诗里
跟不懂得落叶的女贞树
写在一起——
天空像一匹洗旧的床单
路边悬挂着瑟瑟颤抖的果实
脚下几片
别处飘来的黄叶。我跟一个
互不相干的人
走在相同的景物里
5.秋末书
葫芦挂在架子上,抱紧细小的藤蔓
秋风正在吹大它们的身体,也催着枝叶老去
下一秒,时间的举动难以预知
我坐在泡桐树下
置身于不息的衰老中,静默如风中薄暮
而荫影渐大,蚂蚁蜷缩于棕黄的身躯
匆匆绕过落叶。它们忙于练习藏匿之术
它们刚刚出生
已经错过了和风细雨的好时辰
6.可恨的遗传学
我身体上绵延不绝的痛
像是前年才从母亲的身体上传过来
很多时候,我恨这微妙而荒诞的
遗传学,它用一个必然性打破了
我幻想的偶然性
我甚至恨外公,他的疼痛传给了母亲
他在卧病多年的床上
只教会了我们忍耐。前年腊月
在他葱茏的坟茔前,我说:看看呀
我带来的是您生前的痛
您爱过的人间种种,我爱着
您恨过的人,我忘记了他们的模样
7.一阵风
树枝上那只斑鸠望着我
余光之内有碎石、枯草,山川倾斜
我原谅这多余的恐慌
她的胆怯远大于无知
她艰难的排卵過程
远大于她草木同寿的一生
秋风顺势滚下梯田
枯败的草枝劈头盖脸地扑过来
她睁着眼,接受此刻
世间最浩大的袭扰,似乎从未想过
应该从现有的世界里移开
风远去,光静止,小树林窸窣闷响
下午依然是明亮的下午
什么都没有失去
树叶飘落了一程
重又站回原来的枝头
重又站成伟大的一群
死而复生的一群,浩浩荡荡的一群
(选自《诗刊》下半月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