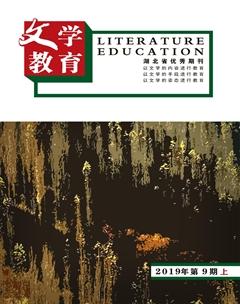“符号学”与抗战叙事
我一直好奇且想一探究竟的是,当批评家写小说的时候,他的话语、思维、表述等是否与其他小说家无异?又或者,他在何种意义、何种层面上,会有意无意地将多年的专业训练渗透于小说的感性层面?对于这些问题,房伟的小说或许能够给予我们一些答案,提供一些有意思的叙事启发。
作为房伟的抗战系列之一,《阳明山》体现了他对于当下抗战叙事的省思,呈现出与此前叙事完全不同的格局。他一直所不满的是抗战叙事的庸俗化、陈腐化,其中也包括被娱乐化和大众化的抗日剧。“手撕鬼子”等夸张情节严重地悖离了历史的真实,也悖离了最基础的叙事逻辑和人性逻辑,不但不能激发起我们对于抗日战争应有的庄严、肃穆、缅怀之感,反而徒增笑谈,降低了其可信度与严肃性。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对于抗日战争和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题材,我们无论怎么书写、无论用多少时间精力对它进行各方面的历史性还原和思考,都不足为过。在这一点上,房伟用抗战系列充分而严肃地表达出了一代作家的历史态度。他收集了众多的抗战史料,熟知那些史书和影视剧里没有的丰富细节,他书写了发生在南京、北京、重庆、香港、日本等地的抗日故事,颇受好评。《阳明山》是发生在台湾的抗战叙事。这个地理空间的选择在历史/现实的双向维度上显示出了书写的多重可能性与复杂性。一方面,它与房伟在台湾做访问学者的现实经历相关;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台湾作为抗日史和国史中的创伤性存在,它的创面形态、叙事潜力、历史渊薮都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和讲述。
房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理论训练融入到了小说叙事之中,这使得《阳明山》成为了一个肌理繁复的独特存在。它是先锋的,又是朴素的;它关乎历史,又立足于现实的血肉;它是理念的表达,又涵纳着中国人太多太深的痛切回望与思考。
小说通过抗战将军某公与海归王博士在阳明山下的对话徐徐展开,他们谈论的核心是抗日战争。两个人的相同点是都拥有关于抗战的沉痛的血色的家国记忆,都对此有着情感和态度上的正面认识。不同之处则是,某公曾与日军短兵相接血肉相搏,对于抗战有着直接的经验;王博士则是家族中有长辈死于日军之手,对此有着间接的体验。当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年龄、经历、学识、性情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他们关于抗日战争的阐释也有着显著差异。
在两个人的对话中,房伟将某公设置为倾听者,将王博士设置为讲述者,王博士所讲的并非抗战史实,而是以深厚的西方理论和学术素养,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抗战与抗战书写进行评判。我想,这里面应当有着房伟自己在学术生涯里的兴趣指向,以及当他发现理论并不能完全合理解释现实时便意欲以别种文体予以呈现的“野心”。
王博士以“符号学”为“工具”对刀、剑、照片、抗日剧等“意象”进行了评说。他在中国的“刀”与“剑”中看到了冷兵器时代的美学及其承载的中国人的道德观、文人气;他在日本人屠杀中国男人、强奸中国女人的照片里,严肃地读出了生与死、善与恶、救人与杀人、生机与灭亡等二元对立里的大悲痛、大浩劫;在抗日神劇里,他不无沮丧地发现,“电视剧对人的诱惑力太大了,它是消费社会兴起的符号象征。人们不再需要战争为生活提供意义,只需要其提供娱乐与刺激。”当大众文化把历史改写为轻飘绵软的消费符号时,那段充满了侮辱、损害、屠戮、戕灭的历史便遭遇了又一次“毁灭”,这是对人们精神与记忆的“抹除”,这种“毁灭”同样是致命的,可怕的。
王博士的解释没能让某公满意。与其说这是“符号学”带来的隔阂,莫如说是两代人、两套经验、两套话语在历史界面上的颉颃。在我看来,他们的言说都是合理的,都有其意义和价值。然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像某公那样的直接经验正在随其主体而慢慢走向消亡,这毋庸置疑也无法挽回。因此,在今天,如何书写抗战,如何构造新的叙事话语来准确地再现和阐释历史,以提醒后来者不要遗忘曾经有过的“血色中国”,就显得格外重要。
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写法太不“小说”,但娜塔莉·萨洛特早就说过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在当下文坛,作家们“怎么写”的方式实在是太同质化了,房伟通过抗战系列所做的努力正构成了对于历史叙事方式的弥补、丰富和多元化。《阳明山》是“符号学”的阐述,也是对抗战史的一次锐敏观察和智性表达。我以为,关于抗战和历史,每一代作家都应当面对、了解、探究并以其特有的心性、思维、逻辑和叙事方式作出回应。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