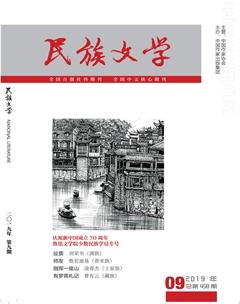跳跃的河山
李俊玲
1
一个人矗立在老家的大山上,某个稍微开阔的地带,看着山下的枯柯河,那些河水呈现出夏季浑黄的颜色,远眺是凝固的粗线条,丝毫不见奔涌之势。极目之处,层峦叠嶂的山峰,一座连一座,波浪一般涌向远方。这时,日头渐衰,白云如驹,大地之上的一切在日色的变化下保持着静态的延绵,大山此时是那么的宽厚和沉静。在这样远离闹市的地方待着,日子似乎总会显得漫长,寂寥,孤单。山野,一种自由的隔离,也是一个彻底释放天性的原始之地,这时的我对着叠叠青山,对着深邃蓝天,会生发出想吼上几句的冲动,让自己的声音打破周遭的静寂,穿过群山,抵达天的那一边。这时的我,想到了祖辈们传下的那些遗落民間的山歌,那些歌带着一辈辈人的孤苦和快乐,传唱千年,如眼前的山河,历经了无数季节的更替,依然在光阴流转下跳跃着不朽的音符。
2
大山是静默的,花草树叶是静默的,而大山又是喧闹的,风过雨来,鸟鸣溪溅,一切都生动而鲜活。动与静构织成了多彩的四季。大山是布朗族的领地,这是人们可以肆意撒野的所在。在面对着亘古不变的河山时,流云以各种姿态在头顶缓缓飘过,一种旷达与寂寞交融的情愫总会涌上心头。在山野里独自行走,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歌会像云雀一样飞落。人们在行走和放牧时,都喜欢用山歌排解孤独,恋爱时用山歌来传达情谊,搭白时用山歌来交流思想,甚至骂架时也用山歌来泄愤和诉说。所以,总会有那么清亮悠远的山歌飘过峰峦,在山谷久久徘徊,在野地上起起落落。那些或欢快或悲郁的旋律是山里人的一种心灵呐喊,以此纾解自己的悲喜,在空旷的山林恣意释放自我。山歌,很多时候就是放牧人的自我放逐。
从前,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水沟边都可以听到布朗人的山歌,在布朗族居住的地方有“只要会说话,就会唱山歌”的说法,每个人从记事之日起,长辈们便在各种节日活动中用歌的方式向他们传授天文、地理、历法、节气、种植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山歌这本无字的书给予了布朗族精神的富足。布朗族的山歌太多了,灿若繁星,按套路所唱的叫“古本山歌”,有规定的词句和曲调,一般用于正式的场合。仅平时唱的古本山歌曲调就有数十种,如采茶调、送郎调、栽秧调、遗物调、想男调、访钱调、蜜蜂调、杀鸡调、要物调、采花调、花鼓调、踏歌调、赶马调等等。这些调子歌词大都是固定的,比如要物调的歌词:一要天边小月亮,二要月里梭罗根。一要礼物格是城里买来的玻璃镜,二要月里格是银匠铺子做出金子头上戴着那一根。如固定的十二属山歌、十二花名等山歌内容,开头第一句都固定的有十二花名:请你阿哥从头来帮破,第二句则根据每月开什么花而相应提问。固定的古本山歌就是一种活着的教科书,人们在唱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教,是对于生命、生产、生活的另一种呈现。这固有的模式代表着祖先的谆谆教导和生活提炼,曲调与词句不可半点更改,这样的延续使得古本山歌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在野地唱,也可以登堂入室,在家里的火塘边唱。人们对于古本山歌,唱的时候更像是一种叙说,喋喋不休的叙说,叙说人生的经验,叙说万物的起源,叙说岁月的流逝,叙说做人的道理与尺度。这样的叙说,既带着仪式感,也带着随意的轻松感,让布朗族的精神世界安适恬淡。
与古本山歌相对的就是随口而出的“野山歌”了,布朗族称之为“花花山歌”,“跑马山歌”,这类的山歌是即情随心表达的。所谓花花,便是形式多样,跑马,就是随意驰骋,随性表达,如脱缰之马,自由奔放,想到什么便脱口而出。山野对歌时,这是最佳的表达方式,得罪也罢,讨喜也好,只要畅快,对方如因此恼怒,会较劲地对上三天三夜也不罢休,最高级别的吵架就是这样,讲究而彻底。大山的寂寞和沉闷造就了许多谐趣横生的山歌,野性、直白、大胆、干脆、痛快、辛辣。这就是人类,“他们总是兴奋地从这悲愁惨苦的世界上摄取最后一分的快乐”(林语堂语)。那些呆滞的石头,流动的云彩,奔腾的河流,摇曳的树木,怒放的花朵,呼啸的山风,悦耳的鸟鸣,那些燃烧的夕阳,流散的泥香,雨后的彩虹,歌唱的溪流,撒欢的牛马都会让人生出一种情欲的快乐,而这份快乐只属于大山和野地。我就曾在采茶的山坡听到过这样一段对歌,至今难忘,一个小伙先开腔:“对门对路对石崖,阿妹生得好人才,今天叫你亲一口,明天死了划得来”。姑娘恼怒那个野小子的无礼,马上回敬:“朝阳茄子红一半,背阴石榴五花心,想做姊妹下辈子,想亲你叫蜜蜂叮”。小伙子的唐突,姑娘的睿智引来茶园笑声一片。在这里,没有顾忌和躲避,人性中最真实的部分往往展现在自然天成的环境里。在山野,人脱离了礼仪、规矩的束缚,没有众目睽睽的观望,没有熙熙攘攘的碰撞,便丢弃了作为社会人的各种桎梏,表现出真实奔放的那一面,人在与自然的交流中开启了生命的智慧,情感的表现也赤裸而真实。
3
对歌这种只有山地才有的交流形式催生了诸多的故事,演绎着太多的爱恨怨惜。有的人因为在对歌中相识相知,浓烈到一定程度便不管不顾结为夫妻。我们老家就有一对已逝的老夫妻,当年就是通过对歌,一对就不可收拾,最后冲破重重阻力走到了一起。女的是河外山的人,放牧时对歌认识了男的,因她是汉族,遭父母极力反对,那时汉族和布朗族基本上不通婚,自由恋爱更是遭到家族的打击和排斥。而旧势力总压不倒真感情,小伙每天把牛放到坡地,对着山那边就开始吼起来。那些勾魂一样的山歌,可以穿透人心。从互相打趣到彼此安慰,从试探到互吐真情,树叶绿了又黄,两颗心便在彼此的歌声里慢慢贴近。我无缘见到这对夫妻,只听到他们的儿女说,当年她母亲背负着不要脸的名声,也得不到亲人们的祝福,独自偷偷跑来和父亲结婚,都是因父亲的山歌诚心而有趣。怎么有趣,如何诚心,不得而知,不过我想,那个逝去的汉族阿奶是最为睿智的女人,一个有趣而真诚的男人一定不会让你生活得太差劲。果然,老两口哪怕日子再艰难,也白手起家恩恩爱爱相濡以沫走完了一生,他们逝去时一前一后只差一天,这样脚跟脚双双下葬的爱真如那句山歌所唱:金打扁担银打钩,哥是扁担妹是钩,扁担银钩不分开,你亲我爱到白头。活着你我同碗吃饭同床睡,死了也要同坑入土同墓门。这样的誓言是唱着许下的,却不带半点戏耍,许下了就用一辈子来履行,山里人对于爱也如同山一样,稳、重、千年不移。
对歌的主要部分便是情歌了,爱情是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在任何地域,任何民族,爱情都是这大地之上被永远歌咏的不竭之源。爱让人充满了希望与寄托,爱让人焕然一新活力无限。只有爱才可以让人在艰难中不懈地劳作,任劳任怨,甘之若饴。而大山的野地里滋生出的爱也带着原始的力度和蛮劲。那些像群山、白云、流水一样自然而生的山歌带着最天然的味道,也带着最赤裸的胆量。尤其是对情爱的表达,那么的肆意。我曾在收集布朗族山歌的过程中为这样的语言而惊叹,我惊叹于这些没有读过书却能把意思和意境表达得如此绝妙,把情感表达得如此彻底的人们,他们所创作的那些歌词是生活的历练,也是自己血液的流速,真实,自然,彻底,快意。
有一段情歌是这样的:“郎在坡头放早牛,妹在房中梳早头,郎在坡头招招手,妹在房中点点头。”很简单的四句话,白描一样便勾画出了一幅非常动人的场景,两个热恋中的年轻人,在美好的晨曦中用各自的肢体语言默默交流,彼此心领神会,秘而不宣中透出强烈的期待之情,让人听了便会浮想联翩,你似乎可以想象到女孩子的娇羞,男孩子的迫不及待,那些俯首吃草的牛羊,和竹楼中静心梳头的阿妹脸上浮起的那片红云……还有一首情歌,堪称布朗族情歌的典范,我一直觉得这位创作者是任何语言大师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歌词如下:“月亮出来亮旺旺,跟着月亮克找郎,背时月亮不等我,一脚踩进烂泥塘。月亮出来黄又黄,想郎想郎真想郎,吃饭想起郎模样,一连咬断筷三双。月亮出来黄又黄,想郎想得面皮黄,别人问我怎么了,我说伤风着了凉。”(克,是方言,去的意思。)这是一个在热恋中却被迫分离的女子对情人刻骨的思念。歌词简单却打动人,在叙述相思的苦涩中也透露出主人公深情而幽默的一面,月亮出来亮旺旺,那轮天上的月亮是那么的圆,勾起了人无尽的相思,而月亮却不听主人公阿妹的话,隐进云层,让找郎的阿妹踩得满脚泥浆。背时,这个词用得俏皮而无奈,把月亮拟人化了,更生动形象。吃饭时想起阿哥的样子,居然把筷子咬断,虽然夸张,却能理解这样的思念是何等的刻骨铭心。相思之苦磨人蚀骨,人也变得病病恹恹,而这时,内心涌动的浪潮只能拍打自己,无法示人,在外人面前只能撒谎说伤风着凉。这样的歌词直白中暗藏羞涩,隐晦中透出勇敢,将一个为爱痴狂的女子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女子,男子的相思也让人过耳难忘:“昨晚等你么你不来,我的妹,我烧了几抱大弯柴,抱个石头坐下等,哎哟,石头成灰也不来。上坡来么坡又高,我的妹,爬到坡头跌一跤,这跤不是哥想跌,哎哟,心想阿妹脚打飘。”几句话便把一个憨厚而钟情的男子形象刻画出来,爱情让人执着而慌乱,想到阿妹就心不在焉,连走路都脚打飘。爱情使人着魔,也使人痴傻。你不得不说,民间的很多山歌能手的创作力与那些大山大江一样,有着鬼斧神工的魅力。情歌对唱中,则以“呃——呀这——麦罗”开头,中间配有“呃——啦呀——啊”的滑音,结尾有“呃——呀——”或“欧怀——欧怀——呕还”等等折音、滑音。一咏三叹的歌唱,使得对唱悠远缠绵。
4
对歌中也分很多种类的山歌,抬爱山歌(赞美與欣赏对方),苦情山歌(幽怨地哭诉),戏耍山歌(彼此打趣玩耍),对象不同,情景不同,山歌也有所不同。作为布朗族来说,“走夷方”也是曾经的生活必须,像多数的滇西少数民族一样,多数人在庄稼收后,就结伴外出“走夷方”,夷方具体应该是指通往缅甸、泰国的边境地带,比如西双版纳、思茅、德宏等。边境的贸易往来让夷方成为做生意的最佳之地。布朗族为了获取那些所谓的洋火、电筒、刀具和生活用品,不得不驮着马帮开始了漫漫征途,在那个封闭的年代,赶马人是享有至尊的待遇的,他们像勇士一样出征,冒着生死未卜的风险,为大家带回来稀缺的物资。所以,大家都对赶马人尊重有加,出行如送壮士,回家如迎贵宾,不过谁也不太愿意嫁给赶马人,俗语说:“赶马郎赶马郎,常年四季不拢家,哪个要嫁赶马郎,被褥都会起霜花。”道尽了赶马人的苦涩,家人的寂冷。在这样复杂的境遇中,还是有那么一批年轻力壮的少生愿意走夷方,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诱惑太大了,而路途上的寂寞和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就算路途险恶,猛兽出没,或者土匪挡道,不知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凶险和不测,也阻止不了他们外出的步伐。“叮当叮当,驮起小马下镇康,镇康爱我有谷米,我爱镇康的小姑娘。”这些欢乐的小调子是一种催化剂,让赶马人可以苦中作乐。在林海中穿梭,那种孤独感有时会让人窒息。于是,有马帮走过的地方就有调子回响,穿梭于重峦叠嶂的大山中,这些调子是巫师,可以驱走寂寞,安抚自己,可以壮胆壮行,振奋人心。布朗族的赶马调由此孕育而生。其中一首是这样的:“大山开路大江让,赶马阿哥去夷方,头骡走得么錾子步,二骡脖铃叮当响,大辣太阳背着走,起身露水湿衣裳,欧怀怀,欧怀怀,打湿打湿么又晾干。”这是赶马人自己诉说途中的情景,白天黑夜地赶路,寒暑交替中,苦乐自知,不过,豪迈与无畏之情充斥其间。布朗族流传甚广的这首赶马调是以情歌对唱的方式来表达的:“说你阿哥,好吃不过罗锅饭,哎哟,眉花一笑,人家的哥啊,好耍不过出门人,哎,我的哥。”“说你阿妹,我三个石头支眼灶,就地扣个洗脸盆,哎哟,眉花一笑,天作房来地当床。哎,我的妹。”这首歌在布朗山算是人人会唱的一首,歌词表达出了一个女子对于赶马人的羡慕,在她们的眼里,能畅游四方,走出大山是多么的潇洒和快意。好耍,这一个词足以说明了一切。而作为赶马人的男子也顺应了这样的羡慕,把自己路上的生活用三句话来描述,三个石头搭起就可以做饭,挖个坑就当洗脸盆,更为豪迈的是天是我的房,地为我的床,多自在。虽然如此随意却也流露出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苦涩,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赶马人出门的日子也并不像乡里人想的那样,好耍也有不为人知的艰难。这首歌曲调特别优美,旋律悠远深情,长长的尾音高地迂回,勾人魂魄。唱腔上,除了具有圆润、委婉、明亮、清晰的特点之外,还有特殊的颤音与滑音。用布朗民间歌手的话说:圆润就是折得起,清晰明亮就像小蜜蜂过江。我以前无法理解为何旋律好听要用“蜜蜂过江”来形容,唱得好也赞叹说,有蜜蜂音。直到回老家,在老叔种的板栗地里休息时,看到了他养的一群蜜蜂,飞来飞去地采蜜,顿时豁然,蜜蜂是布朗族身边最会歌咏的小动物,它每天嗡嗡地采集花蜜,在人们听来,这劳作之声是最甜美的歌咏,于是便将山歌唱得好的夸赞为蜜蜂音。至于蜜蜂过江,我想也应该是那种嗡嗡声汇集起来有种穿透和回旋的力量,那些悠远的旋律便有此特质,可以穿透山谷,过江过梁,穿透云层,在林间回荡,甚至可以穿透耳膜,抵达人心,三日不绝。
5
苦情山歌是诉说的一种方式,一种释放的最佳出口,有点像委屈时的怨诉,也像吵架时的喋喋不休,指桑骂槐的表达。一般是在诉说相思之苦,离别之恨和远嫁之怨。苦情,这个词特别有意思,苦涩的情感,这是人世间最无法割舍的一种疼痛吧。大到生离死别,小到委屈愁苦,人们依然用歌的形式来表达着自己内心的痛,像古人的唱词,任何的情感都以唱的方式呈现。只是这样的曲调要凄婉哀怨得多。我在山地里极少听到苦情山歌,只有在出嫁的时候,才听到过。哭嫁对云南的少数民族来说是很普遍的一种风俗。女儿要出嫁了,作为父母和长辈在出嫁的前一夜便开始用哭和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舍。按理来说,女儿喜结良缘,父母应该高兴,而对于深居大山的布朗族,出嫁便意味着长久的分别,那些高耸的大山,奔腾的江河似乎变成了难以跨越的屏障,回一趟家不容易,在交通不便的过去,嫁得远一些的姑娘从此便是与父母天涯两望的感觉。看着自己辛苦带大的女儿即将成为人妻,即将到另一个陌生的地域生活,即将肩负起一个家庭的重任,父母的担忧、焦虑和不舍便在哭嫁中得以尽情释放。
儿时,我曾在老家楂子树看到过一次哭嫁,新娘哭得无法走路,伤心让她忘记了是自己大婚的日子,她扶着自己的门,迟迟不迈步子,迎亲的队伍等候着,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着,似乎经历了最痛的生离死别,我甚至以为那是一场丧事。出嫁的前一晚注定是无眠的,女孩子带着满心的期待,也带着对家人的眷恋,复杂的心情让女孩无所适从,父母亲看着即将离去的女儿,欣慰中也有诸多的酸楚。彼此的心境都矛盾和不安,首先是母亲抱着女儿哭,边哭边交代一些事宜,比如过去要好好招呼一家老小,要学会照顾自己,要懂得生活的节俭和不易,持家有道,要团结妯娌孝敬公婆,要记得有空回家看看爹妈……当所有交代结束后,彼此已哭得泣不成声了。这样的场面我见过两次,我惊呆于这样的哭诉,忧伤而不失礼数,失落却充满憧憬,这是人性中最为可贵的一面,在不舍和依恋中,想到的依然是教授女儿做人做事的道理,想到的是为对方着想的淳善关怀。在布朗族的家庭中,人们自我舍弃的东西太多了,宽厚与爱总是让贫瘠的生活永葆温暖的色彩。算计和自私离大山是遥远的,在这里,付出和隐忍是布朗族总体个性的底色。
母亲哭完,姨妈舅妈开始哭,各人站在各人的角度告诉新娘,做人的道理,生活的道理,离别的忧伤,哭嫁是一种变相的人生教授,这样的教授情真意切而终生难忘。哭嫁有“隔娘调”“隔女调”“哭哥嫂”“哭姐妹”“骂媒人”“哭出门”等诸多的调路,这样的形式也特别有意思,有的嫂子也会借机和即将远嫁的小姑子哭上一场,将自己的境遇在哭嫁中哭诉出来,说白了就是指桑骂槐,说出自己的苦楚,“不当媳妇你不知孝顺人,当了媳妇你才知苦滋味。”一个女人对于家庭的承担从哭嫁中就可以体会出来。难怪布朗族称哭嫁为苦情山歌,以前出嫁的女子大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自主的婚姻对她而言,充满了诸多的未知,命运叵测,谁知道到了男方家自己会有怎样的生活。有的婚姻甚至充满了恐惧和茫然。所以,在哭嫁中,人们的表达都是苦涩和哀怨的。
6
带着野趣的花花山歌只有在山里才可以唱,家里是禁止唱那些随心所欲的山歌的。家里是有敬畏的场所,那些肆无忌惮的曲调和表达在篱笆和围墙构筑的家里被悉数收敛。而在家,人们哼唱的除了古本山歌,都是那些旋律轻快的柔和的小调,尤其是主妇们,用那些暖暖的歌曲来抒发自己对孩子对家庭的爱。似乎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摇篮曲,那是母亲来自天籁的歌声,透着浓得化不开的母爱。布朗族也有自己的摇篮曲,在火塘边,在床边,在有母亲的地方,就有摇篮曲。歌词很简单,寥寥几句话却晕染了母亲对孩子的舐犊之情。“妹妹你喏喏睡睡,妹妹你喏喏睡睡,阿妈克赶街街,阿妈克赶街街,买给你小花糖糖,买给你小花糖糖,嘟噜噜嘟噜,嘟噜噜嘟噜。”就是这样简白的语言,哄自己的孩子快点睡觉,妈妈去街上给他们买心心念念的小花糖。这样的叙事儿歌流传了一辈辈人,哼唱至今,温情从小小的摇篮边、火塘边飘荡开来,像精神食粮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布朗儿女。每个大山长大的孩子,耳边都会回响着妈妈这样软软柔柔的哼唱,孩子长大了,成家了,他们也用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姿态,同样的方式为自己的孩子唱起这首老歌。这是一种招魂的密语,你无法去修正和改变它,只要是布朗族,听到这样的歌曲,心里总会升腾起一股暖意,那是来自大山深处的母亲不尽的爱意和呵护。这首歌被改编了很多次,被无数次搬上舞台传唱,每当我在台下聆听时,总会禁不住热泪盈眶,我想到了大山,火塘,炊烟和母亲。这一切具象的东西只源于一段温暖的旋律。
7
当我再次回到老家,和一位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歌手聊到山歌这个话题时,她浑浊的眼里闪过了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转瞬黯然,叹息说:老了,我们唱不动了,现在的年轻人也不会唱了,都听手机唱了。是啊,现在没人放牧了,没人靠脚力行走了,没人会以山歌的方式传情达意了,电话、微信替代了所有的表达。大山的信号使得人们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通联,繁忙与热闹开始浸入山野。
我曾想,人是否只有面对寂寥与孤独,只有面对着那些带给自己无限畅想的大地时,才会想法搜罗出各种乐趣,激发出无数灵感来聊以慰藉,填补生活的空白。山歌就是这样的产物,人们舍不得辜负自己的情感,辜负这光阴之下的河山,于是便倾其所有,用歌的形式来给自己的生活添上那么一抹别样的色彩。山歌,是远古时代慢生活的精神盛宴,就像留声机是旧上海贵族的专宠一样。在那个一切都静谧、封闭、缓慢的年代,人们用无穷的智慧编创出了诸多歌曲,谐趣横生,妙语连珠,那些流传下来的山歌像流淌在布朗族血脉里的因子,自然而然,根深蒂固,延續至今。这样的编创和传承是尊贵的,日月山川,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天地万物在人们眼里都可以变为某种音符。大地是一本敞开的书,人们不断翻阅,汲取着营养,让自己苦闷的生活过得有些许的滋味。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活法。
如今,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娱乐空间的不断拓展,人们在视听世界里的甘心沉溺,势必会失去对于自然最原始的触动和感受,失去天地带给自己的温度和质感,失去挥发想象的原动力。数码、快速、自媒体,这些带着金属感的词汇,会加剧人的急躁与不安。我们似乎没有闲暇静下来,来面对这保持不变姿态的河山,面对光阴流逝下对于万物的怦然心动。我们的生活变得时尚而快捷,却粗糙而呆滞。在看似丰富的娱乐生活下,人类很可能有一天会丧失感动,丧失自我。
看着眼前的河山,想到凋敝的山歌,张炜的那句话浮于脑际:“当人完全躲避了粗粝的现实生活,收获的就只有浅表的哀怨和欢愉了。”多希望,当我们换了一种生活模式时,我们的精神依然强盛与繁茂。此刻,多想有那么一曲山歌清亮地在耳边响起,在山间回荡……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