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恒,怀心,就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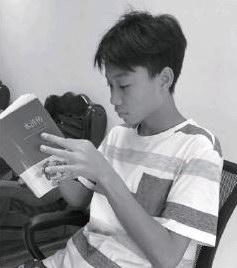
作者自画
昼伏夜出,非老鼠也,小羊咩咩石荣桢。喜静亦好动,爱阅读与旅行。
广场还回荡着我两岁时外公扶着我的自行车后面“鹅,鹅,鹅……”的笑声;仿佛姥姥(外公的父亲)还坐在那把小木椅上,悠悠地看着那抹斜阳;喜欢听姨妈及舅妈家长里短……
武汉大学的樱花,横店一场寻常的雪……平凡一景,却总有触动内心的地方。
这就是我,不—样的人间烟火。
江上舟摇,楼上帘招,风又萧萧,雨又飘飘,何日归家洗客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幽幽的笛声冲破湿润的空气,穿过小巷,萦绕在人的耳畔,时如高山流水,时如风吹麦浪。顺着笛声往里走,巷子中散发着一股浓香,忧郁而神秘。愈往里走,香味愈重。顺着香味,循着笛声,继续向前。终于,到了熟悉的地方——恒笛木匠坊。
哦,刚刚那是古木的檀香!我不想打断正沉浸于笛声中的木匠,于是便放轻了脚步,跨过门栏。两侧依旧是那两道木屏障,这么多年了,檀香味还是这么浓郁。上面刻着“八仙过海”。仙人各显神通,钟离点石把扇摇,果老骑驴走赵桥,彩和手执云杨板,国舅瑶池品玉箫,洞宾背剑清风客,拐李提葫得道高,仙姑敬奉长生酒,湘子花篮献蟠桃。人物惟妙惟肖,衣裳的一褶一皱清晰可见。海上惊涛连天,水天一色,云雾缭绕。整幅画面一气呵成,可见刀工缜密稳重。
笛声骤停,他手持笛子与鼻尖平行,仔细端详了一番,面部的皱纹集成一束,轻轻摇着头,嘴角却又突然上扬,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果不其然,他提刀,左飘右落,不大不小一块木片被削下,整支笛子美观了不少。“来了就过来坐坐吧。”他只是抬了抬手,但却不失礼貌,“有没有喜欢的,可以送你一个,别把自己当外人……”
“不了。”我表示谢意,目光却锁定在一支龙笛上,下面镌刻着一行字——明日龙起震宇鼎,华中傲气压芳群。“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他突然站在我身后,我转身请教。他皱起眉,却隐藏不住眼角透出的笑意:“龙,中华之魂,它孕育着中华民族的恒心……”我仔细看这条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口旁有须髯,额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腾云行水,护佑一方。对此我不禁赞叹,好手艺!他却一笑,低下头,挥了挥手:“不敢当,不敢当
一这不是我刻的,你想知道是谁刻的吗?”
好奇心促使我在饭桌边坐了下来,饭菜再香都不如故事有诱惑,他手舞足蹈地讲了起来……
原来我爷爷曾和他一样,是镇上数一数二的木匠,爷爷靠这支龙笛一举成名,成了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如我爷爷,便丧失了往日竞争的激情,自甘堕落。就在准备宣布退出木匠界的前一天,我爷爷却宣布这支龙笛是他刻的。他哪敢接这份虚得的荣譽,但同时我爷爷也退出了木匠界……
“我爷爷以前真这么厉害吗?”我久久未提箸。“嘿,那当然,想当年他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一提起我爷爷,他就十分激动,滔滔不绝。这是他唯一讲的不靠谱的话题,他意识到有些失态,便收敛了一点。他坐下来,抿了一口茶,继续道来:“若不是你爷爷,我也不会再传承这门手艺,他唤醒了我的恒心!”
他将剩下的茶一饮而尽,又沏上一壶茶,撑了撑腰,端起先前的笛子,这次吹了一支波澜不惊的曲子,笃定地望着窗外。
望着他的背影,我不禁心生感慨。他现在是镇上第一木匠,也是最后一个木匠雕刻手艺人,这么多年,始终是他。一阵过堂风将笛声吹出门外,吹入整个小巷,钻进每一个角落。
我听得痴迷,不小心洒出一点茶。我久久地凝望这一滩水,用手指蘸上,在茶几上写了一个字——恒。他注意到了,漫步走来,沉思了一小会,在后面加了一个字——心!
夜晚在此借宿,枕着幽幽檀木香,枕着一颗炙热的恒心,我久久难以入眠……
(指导老师:吴秀英)
写作背后的故事
文中男二号,背后灵魂高能老木匠爷爷,是湖南醴陵一个小镇上,从我呱呱坠地,就与我“纠缠不清”的,我的外公十几岁开始做木匠,小板凳、小椅子、沙发、餐厅形象牌、龙神老爷的眼睛……无一不经他之手。
文中男一号,可能是另外万千叔叔、伯伯或爷爷中的一位。“他”只是个狭义的木雕匠,广义上却代表着一群无人问津、默默孤守一方的手艺人。“他”最具代表性。
村中的人数也不多,完全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村头鞋匠针线不离手,村尾铁匠火炉烧得旺。修家用电器的也骑着车,扯着嗓子吆喝着。大家都忙忙碌碌过着自己再寻常不过的生活。
“他”的“恒笛木匠坊”也开在这村中。不同于常人的是,“他”的店分前后,前头招呼客人,后头自己创作。登门拜访的也都是村里的人,也许从邻里刚放下手里的活而来,又或许挽着裤脚,扛着锄头从田里上来的。也不曾进来,进去的也只是朝里屋招呼“他”一声,匆匆留下一句,“家里头椅子坏了,寻个时辰来看看”。粗犷的嗓门,声响回荡久绝。无可奈何的“他”,放下绣刀,寻上去,闷闷敲上一通。
能记得“他”是刻笛子的人,除了我也不多。也许是每一代人的不同,审美亦是不同,他总能从我的评价中挑出新灵感,又积极投身于新创作。放下过刻刀,但并非一直放置,“他”时常会重新握起。
多亏国家政策的支持,市政府把手艺人召集在一起。不少人感叹,欣喜落泪。我向“他”贺喜,“长年守恒终有果”。“他”先喜了一阵,又沉住气,但却未曾抱怨一句,只是娓娓道来,“人们需要家具,我提榔头;人们需要手艺,我操绣刀”。
“他”是谁?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