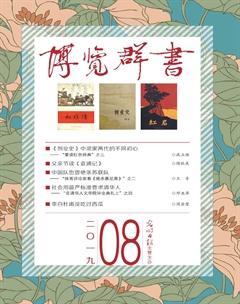父亲节读《袁浦记》
傅秋爽
2019年的父亲节,尽管网络商们一再煽风点火,也还是少了些购物狂欢的浮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比心灵陪伴、滋养更能体现这一生的缘分。什么才是父亲最需要的?儿女们再思索。我要把什么奉献给我挚爱的孩子?父亲们更在想。三联新书《袁浦记》,字里行间满满都是父子深情。
作者孔建华,身长、清癯,微黑,不苟言笑。生于江南鱼米之乡,久居京城,就职行政机构,标准京官一枚。饮食却不甚考究,一碗素面,果腹即可。为人少活泛,研究问题做事,认真耿直,略嫌执拗,像个老派学究。与人交,简单、质朴,重然诺。其襟袍宽敞、古道热肠在遇事深交后不经意间才能慢慢体味出来。曾经诧异宦海多年而古风犹存的矛盾。直到读完他的散文集《袁浦记》,才隐约寻到其中的逻辑。
以心为文
最初,写作的动议来自作者要给儿子讲述家族和家乡的故事。这恐怕是一个游宦在外,生怕挚爱的子孙断掉根脉的游子最想要做的事了。因为他想让孩子明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未来临歧路,不困惑,不迷失。这份情义沉甸甸,胜过金山银山。作者出生在人文荟萃的江南,家乡袁浦距六和塔15公里,是钱塘江、浦阳江、富春江三江聚首的千年古镇。塔和水,仿佛作者生命的象征。水,似流年。他在故乡度过人生最初的二十年,然后远赴京华,又是二十年。而这四十年恰恰是中国社会发生地覆天翻变化的时期。故乡袁浦经历着从原始耕作到农耕生活方式彻底消失的沧桑巨变,是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曾在水边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的袁浦少年,远离乡土,久别故园,年近四旬,蓦然回首,家乡的山水草木,就那样“不思量,自难忘”悠然倾泻于笔端。书中,写自己的父亲、母亲、舅舅、姑姑,那些离开的和健在的亲人;写自己的小学、中学和一个又一个老师,那些过去了但忘不掉的往事;还写播种、收获种田人各种逃避不掉的苦楚和易于满足的喜悦。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是那样鲜活灵动,字里行间,泥土一般肥沃地生出欢欣的花朵。家族是什么?是文化的传承。故乡是什么?是文化的母体。塔,如青山。作者总是记得母亲的话:做人要记人家的好。这话,已经深深植入心底,裹进行囊,带到远方,伴随自己,一路成长。他当然还要把这句话传给儿子,让他自带阳光温暖,看世界的眼充满慈悲与欢欣。陶东风说孔君之文“有夏丏尊、丰子恺、汪曾祺之遗风”真是精准。
以诗为文
袁浦独秀江南,因为有三条最美大江环绕,三江之水的宏大,两岸花木的葳蕤,形成壮阔与细腻相和谐的统一,培育着作者性格,养成了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
怀念故乡自古就是游子经常吟咏的主题,最著名莫过于元代“杏花春雨江南”,名句出自虞集寓居京城时所作《听雨》:“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道尽故乡妩媚与绵绵不尽的思恋。而孔君笔下的江南层次则厚重丰富得多,色调更趋沉静古雅。
《袁浦记》的诗意,除了来自于感情的美好,同样来自于文字的锤炼剪裁。伊看:“我眼见人民公社解散,眼见乡政府挂牌,欣逢分田到户,是拥有八分地的纯正农民。”虽曰散文,但是何等整洁明快,毫无拖泥带水的芜杂,无处不在的是诗歌的节奏和韵味。
诗意與写作的惜字如金密不可分。许多处,凝练简洁如“环滁皆山”一般经典。如描绘故乡“境内有座山,叫浮山。有个庙,叫红庙。有个湖,叫白茅湖。有三条江,钱塘江、浦阳江和富春江。” 简直到了增一字则繁,减一字则缺的境地。写作过程中,作者并不肯做过多的渲染。大多纯用白描手法,凝练地描绘田野一草一木、人物一举一动,行文多用四言,有《诗经》之遗风,而画面也是细节的生动与天地的苍茫浑然一体,读来别有韵味。
他喜用数字,喜用方位词,常常营造出“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的意趣。他描绘最初居住的草舍时说“边上有棵枇杷树,两个菜园,一个池塘”,画面感极强,像极了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笔墨。
以美为文
孔君嗜书如命。古今中外,凡举佳作,博采众长。他的笔下,有农家辛勤劳作所得甚微的悲辛,更有陶渊明笔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相互亲近;有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切,也有辛弃疾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由衷的欢欣。笔法上更是深得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之精髓,以景写情,情景交融。有人说读《袁浦记》,那悠闲恬然的节奏,朦胧的诗意,不禁让人想起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边城》,想到汪曾祺的《故乡人》。的确,作者描写环境,刻写人物,有沈从文的传神笔触和无处不在的人情味,也溢满了汪曾祺对生活浓到化不开的珍爱和欣赏。作者用抑制不住的欢欣,描摹着生命万物的喜悦和世间百态的温情。
以画为文
也有人说孔建华笔下的故乡,是活脱脱一幅可以静观卧游的“富春山居图”,这样的评价似乎委屈了他。作者描绘家乡,充分地调动着声音、嗅觉、触觉,运用着色彩、光影、线条,勾勒出它的恢弘与气势,渲染出它的瑰丽与壮美:
家住袁浦,大江流过我的家。钱塘江从北门流,号子田头稻熟时,坐船上闻得见谷香。富春江从南门流,油菜花开时,坐船上看得见金色。浦阳江从东门流,麦浪滚滚,坐船上听得见席卷声。这还不够,每年月球和地球心动,给袁浦献花,用一江钱塘大潮作它的丝绦。吾乡袁浦,是桃花源。
这完全是一个可赏、可游、可触摸、可感怀的空间,任谁都会被这三江汇集的气势所撼动,为这毓秀钟灵的自然而惊叹,骄傲自豪之感油然。这个空间360度旋转无死角,无际的画卷,伴着交响乐的华丽乐章。
以文为史
文中,作者没有一句针对时代的褒贬。但是通过忠实记录一个家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不断发生的变化,通过再现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个深刻变革时代的历史画卷。画卷在自如舒卷中展示着磅礴与恢弘,显示出举重若轻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功力,点点滴滴都化作对时代力透纸背的礼赞,孔君从事促进文化发展工作,深深懂得文化磅礴恒久的力量,潜意识中有着对文化传承的责任和义不容辞的担当。这种文化自觉,已融入血液,化成文字,“袁浦过年,我把炒糕花、请阿太啦、吃年夜饭、正月拜年、掼龙灯、跳竹马、听戏文,一股脑儿,写进《年去岁来》,收入《袁浦记》”。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记录下故乡城镇化过程中那些行将消亡正在被人们遗忘的农村生产生活史,记录下曾经鲜活存在过而今却正悄然消失的各种民俗。从这点上说,《袁浦记》又具有以文为史的价值和意义。
接续亲情
写《袁浦记》这样的文字对孔建华来说,并不具有立德、立言、立功之效能。他仅为纪念亲人而为文,为陪伴孩子成长而运笔,43岁的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为自己12岁的独子铁儒接续家族的血脉和亲情,在他看来,这是一件作为父亲必须要做的事。一种食品可不可以吃,一部书可不可以读,一个电视连续剧可不可以看,人们总是会说:“敢不敢,愿不愿,让你的孩子来试试?”能不能让血肉骨亲来享用,这是衡量质量和健康与否的金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建华奉献给观众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
(作者系北京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