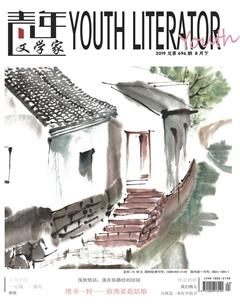和弦
孙瑞萌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能够走得更远。
——题记
距离正式演出,只剩下三天。
风起的时候,竹子一杆杆摇曳摆动,飘落了一地又一地的叶子。浅浅的香江里,柔软的水草安宁地躺在河心,几针银鱼仿佛永恒静止在空中。当香江花园琴行各个节目紧锣密鼓地排练时,一个撕裂了的十六分音符,从门里窗里穿过稀稀疏疏的竹叶,像枚石子掷在浅浅的河心,漾起阵阵涟漪,那一针又一针的银鱼飞快地四散潜到水草底部去了。
我抱着琴谱在门口停了几秒,奶奶轻轻地拍拍我的背,怜爱地笑着示意我进去。我小心翼翼地走进空气好像凝固的大厅,隔着落地窗,看着奶奶对我挥挥手后慢慢转身。叶川老师点燃的烟搁置在节拍器旁,音响上节拍器的指针快活地左右摇摆着,长长的一截烟灰快要掉落在地上。雨婷已经坐在了琴凳上,她直直地盯着已经有些泛皱的谱子——那是我们练习了许久的《克罗地亚狂想曲》。我放下琴谱坐在旁边,她微微靠边挪了挪位置。节拍器再次哒哒响起,她像惊鸟一般地飞出,手如鹰的翅膀一样盘踞在黑白之间。这么久了,当她纤长的手指如急厉的雨点扑来时,我仍旧像只笨拙的小鸭,马不停蹄地追赶她的步伐。“今天已經周二了,合作多久了还是这样的问题,雨婷你急着投胎啊,还有你,怎么总是慢半拍!”遽然,叶川老师厉声说道。我们只能缄默不语,整个房间只剩下节拍器哒哒作响。
音符,教会了我怎么弹琴,却没有教会我如何走近身边的人。在错乱的节奏中,我们像往常一样结束了一天不尽人意的排练。奶奶也一如既往地早早等在了门口,这样耐心的陪伴和等待已经有五年了,最初我大拇指落键时总是压键、小拇指也完全用不上力,她始终陪我练琴练到深夜,如今我满腹心事地走出排练大厅,望见奶奶单薄苍老的身影,一股酸楚涌上鼻尖,我埋下头,牵着她的手缓缓走向巴士小站。
站牌下,雨婷像只白鹤亭亭静立,她比我先来琴行两年,平日里总是形单影只,少言寡语,步履匆匆,独来独往,大家对她了解甚少,她左手腕上的一道红色疤痕,让人颇为好奇。“雨丫头,走那么快干嘛?”奶奶慈祥地笑着说。“啊,奶奶!”雨婷客气地答道,随即便低头看手机了。我拉拉奶奶的衣角,奶奶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车还没来,奶奶打包了热可可,喝着暖暖吧!”雨婷礼貌地接过,莞尔一笑。奶奶徐徐地说:“现在的孩子累啊,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但一群人能够走得更远呢!”话音刚落,雨婷微微望向奶奶,又望向我,嘴角轻轻弯起弧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之后的三天,雨婷和我弹奏《克罗地亚狂想曲》时,节奏竟为配合我而舒缓了几分,前所未有的默契由此滋生。我们并肩而坐,步调一致。我虽看不见她的表情,但能感受到她音乐中不曾有过的亲切与温暖。以手为马,以心为翼,定能到达未去过的远方。
“下面请欣赏钢琴演奏《克罗地亚狂想曲》。”舞台灯光璀璨,照耀着我们交握的双手。我们齐齐落座,微闭双眸,任手指在琴键上轻快地舞蹈。从低音滑到高音,又从高音徐徐降落,时而清脆如珠落玉盘,时而急越如飞瀑,时而低回如细语呢喃,时而烈如咆哮的深海……黑白交错在指尖跳跃,五色交辉于心田蔓延,心灵的翅膀在黑白山水之间飞翔,直到东欧的克罗地亚:
我们仿佛奔腾在浪涌里,战火吞噬了克罗地亚,硝烟弥漫在背后……夕阳倒映在血泊之中,坦克轰炸过的废墟上开出一朵白色的小花,我们置身于原野大地上人群的愤怒和抗争里,随着音符穿越火线,在枪林弹雨中与马克西姆一道,弹奏着生命的和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