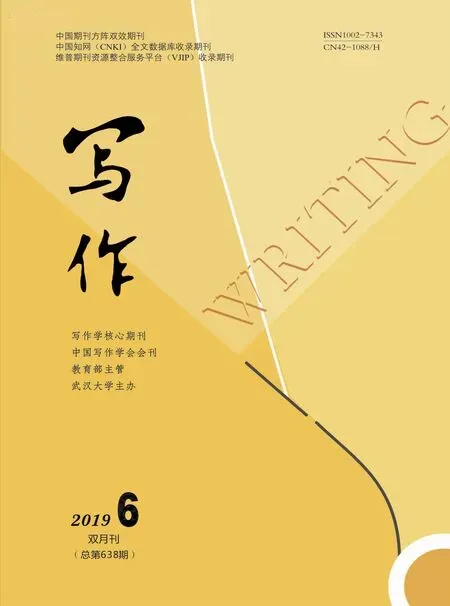1930年代中日现代诗歌写作比较
陈 璇
20世纪30年代是中日两国现代诗歌从交互式影响关系到尖锐对立的重要转折时期。虽然两国的现代诗均是在西方诗歌的刺激和启发下产生发展而来,并且日本曾一度扮演着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文化桥梁”,但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逐渐摆脱了日本的路径依赖,特别是对20世纪20年代盛行于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接受,中日两国几乎同步。然而,中日战争的爆发导致两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创作意识上的激烈对抗以及发展路径上的大相径庭。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下,大部分日本诗人投入到“侵华诗”的创作,日本诗坛涌现出大量鼓吹战争、美化侵略的“现代诗”,使诗歌沦为军国主义国家意志的宣传工具,从而使现代诗艺的探索遭到冻结,导致艺术退行。而我国的现代主义诗人在民族危难中将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与民族的苦难现实相结合,通过诗的创造实现了中国人现代性的精神探索,将现代汉语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另一方面,“侵略”与“反抗”并非这一时期两国诗歌关系的唯一底色,日本反战诗人与中国诗人的交流为中日诗歌在和平与发展时期的平等对话埋下了火种。本文将聚焦193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的现代诗歌写作状况,通过诗歌作品的文本分析,深入探索这一历史时期中日现代诗的互动关系,并在论述方式上侧重于对我国现代诗坛而言仍缺乏了解的日本现代诗歌的阐述。
一、1930年代上半叶中日现代诗歌发展概况
1930年代上半叶的中日现代诗歌发展状况具有以下两点共性:第一,现代诗坛流派林立,现代主义诗歌蓬勃发展;第二,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已从共时性接受向历时性接收转变,并与世界文学潮流发展同步。
我国新诗从诞生到发展初期受到了日本文坛的显著影响。以梁启超、黄遵宪、鲁迅以及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冯乃超、穆木天等创造社成员为代表的留日文人群体对我国新诗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倪正芳以拜伦在中国的传播为例,将日本对中国诗人的影响方式概括为“日本桥梁之四维”,指出日本不仅为我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开展文学活动的平台,也为我国文人接触西方文学资源以及直接利用日本已有的文学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①倪正芳:《拜伦与中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第27-32页。。与此同时,日本文学思潮的流变同样影响了我国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两者具有显著的同调性,对此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1998年)已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言。然而,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降,留日诗人群体的主要诗歌活动已经较少看到来自日本的直接影响。例如“创造社”成员穆木天与蒲风、杨骚等人于1932年创办中国诗歌会,而穆木天本人的诗歌创作也已摒弃了在日本受到熏染的象征主义诗风,转向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与此同时,我国现代派诗歌于1930年代兴起。以戴望舒的《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集相继刊行,《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戴望舒参与主编的诗刊,与创刊于全国各地的现代诗刊,构成了我国蔚为大观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图谱。“在20年代末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以戴望舒为领袖的现代派诗潮,蔚为气候,风靡一时,‘新诗人多属此派,而为一时之风尚’,成为30年代诗坛上与提倡写实主义与大众化的中国诗歌会代表的‘新诗歌派’,提倡新格律诗的后期新月派鼎足相峙的三大诗派之一,与它们一起,构成了新诗短暂‘中落’后的‘复兴期’”②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日本现代诗坛呈现出现代主义诗派与普罗诗派分庭抗礼的局面。从根岸正吉、伊藤公敬合著的“劳动诗集”《歌于最底层》(1920年)、诗刊《播种人》(1921年创刊)、《文艺战线》(1924年创刊)到该刊同人于1925年结成日本普罗文艺联盟,普罗诗派逐渐发展为日本现代诗坛的重要一极。另一方面,1920年代后期《诗与诗论》《MAVO》《蔷薇·魔术·学说》等现代派诗刊相继创办,呼应了西欧超现实主义、新达达、主知主义等艺术潮流。1928年,春山行夫创刊的《诗与诗论》汇聚了安西冬卫、饭岛正、上田敏雄、北川冬彦、近藤东、竹中郁、外山卯三郎、三好达治、泷口修造、西肋顺三郎、堀辰雄等诗人,成为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主阵地。春山行夫提出要确立以欧美开展的新诗运动、新诗精神为现代诗歌导向,打破既往日本诗坛“无诗学”的状况,明确区分“近代”与“现代”。
中日两国现代派诗刊的大量涌现以及诗派林立的状况说明,截至20世纪30年代两国的现代诗歌发展均已步入与世界诗潮同步的阶段。日本学者坪井秀人指出日本“192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刷新了此前后发于西欧,并从模仿它而发轫的日本近代诗的历史,以与世界(这里的‘世界’限定指‘西欧’)之诗并驾齐驱(synchronize)而傲然于世”①坪井秀人「日中戦争と詩」、『現代詩大事典』三省堂2008页、516頁。。吴晓东指出“在现代中国文学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象征主义的传播构成了一条持续而贯穿的线索……在传播方式上,对象征主义的介绍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在第一阶段(1919-1927)以共时性倾向为主,各种象征主义倾向和象征派作家几乎同时涌入中国文坛,在第二(1928-1937)和第三阶段(1938-1949),则在共时基础上又体现为历时性特征,表现为与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进行中的历史过程的一种同步关系”②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由此可见,从1920年代末期开始,中日两国诗歌均已展现出从对西方文学的共时性接受向与世界文学同期发展的历时性共振转变的趋势。特别是对兴起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潮,两国诗坛均对此进行了自觉吸收。以T.S.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第一位将艾略特介绍到中国的是于1924年至1926年间留学剑桥大学的叶公超;而首先将艾略特译介至日本的是于1922年至1925年间留学于牛津大学的西肋顺三郎。两者均在英国留学期间阅读《荒原》而深受触动进而将其介绍至各自文坛。
由于两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世界同步性,我国在外国文学接受上已不再依赖于“日本桥梁”。“创造社”成员等留日群体的文学活动重心于1930年代也从日本转移至国内,中国文人通过日本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现象已不再显见。抗日战争爆发前,在中国,现代派、“新诗歌派”、后期新月派三足鼎立;在日本,普罗诗派与现代主义诗派分庭抗礼。战争爆发后,中日现代诗的发展均发生了重要转折并体现出截然相反的命运轨迹。
二、现代主义诗艺在中国的拓展与在日本的停滞
1937年以降,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侵华文学”与中国“抗战文学”尖锐对立。与日本“国家主义文学同盟”(1932年)、“文艺恳话会”(1934年)、“日本文学报国会”(1942年)等日本国粹主义文学团体相抗衡的是我国“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1931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等抗日文艺组织。1937年,日本国内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成立所谓“笔部队”,众多日本作家、诗人被派遣至中国考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明确表述:“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学刊物方面,与日本《我思》③《我思》刊名的日文表记为“コギト”(Kogito),来自于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四季》《日本浪曼派》④《日本浪曼派》创刊于1935年3月,终刊于1938年3月,以保田与重郎为首,以近代批判和古代赞歌为主要内容,提倡“向日本传统回归”。须要注意的是,该刊刊名中的“浪曼”一词不同于一般汉字表记的“浪漫”。等国粹主义刊物相对立的是《抗战文艺》《诗创造》《中国新诗》等以抗日和民族救亡为宗旨的文学刊物。在创作意识上,两国诗人也呈现鲜明对立之势。以穆木天(1900-1971年)与日本诗人三好达治(1900-1964年)为例,二者曾先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前者于1926年,后者于1928年),并于同一学校同一专业同一时期接受了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熏陶。自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木天的创作扎根于中国被压迫的社会现实,强调“现时代的诗歌,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呼声,并不是几个少数的人待在斗室中的吞云吐雾的玄学的悲哀的抒情诗”⑤穆木天:《关于抗战诗歌运动》,《文艺阵地》1939年第3期;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999版,第238页。,并通过诗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批判。而三好达治则于战争时期抛弃了习得的西方文学精神,转向国粹主义诗歌创作,对日军的侵略行径进行了美化和宣传,在1942至1945年间刊行所谓“战争翼赞三部曲”。
此外,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抗战时期迎来了艺术拓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现代主义诗歌艺术遭遇停滞乃至退行。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诗人们开始积极探索现代诗艺与抗日救亡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诗歌创作道路,他们“一面撇开了艺术至上的观念,撇开了人生的哲学的说教,撇开了日常苦恼的倾诉,撇开了对于静止的自然的幸福的凝视;一面就非常迅速地……把自己投进了新的生活的洪流里去,以人群的悲苦为悲苦,以人群欢乐为欢乐。是自己的诗的艺术,为受难的不屈的人民而服役,使自己坚决地朝向为这时代所期望的,所爱戴的,所称誉的目标而努力着,创造着。卞之琳、何其芳、曹葆华,都写了好多诗,这三位诗人,最显著地受到抗战的影响,他们都同样地为自己找到了他们新的栖息的枝桠”①艾青:《抗战以来的的中国新诗——〈朴素的歌〉序》,《文艺阵地》1946年第6期;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然而,战争时期的日本现代诗坛,现代主义诗刊却纷纷凋敝,诗人们或放弃诗歌创作,保持沉默,或龟缩到艺术至上主义的园囿,或转向国粹主义。坪井秀人指出“基于个人主义进行高度知性表象的日本现代主义诗歌方法论在战争诗的时代经历了不可修复的断绝”②坪井秀人「日中戦争と詩」、『現代詩大事典』三省堂2008年、516頁。,“太平洋战争对诗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冻结了盛行于2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主知主义的诗歌意识与视觉主义的语言实验,取而代之的是向国体共同性的同化……”③坪井秀人「大東亜戦争と詩」、『現代詩大事典』三省堂2008年、394頁。军国主义日本对外不断侵略扩张,对内施行严苛的言论管制,以及现代诗人们集体失语,放弃反抗乃至转向,导致日本现代诗沦为国家意志的宣传工具,现代诗艺的探索丧失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
三、以“侵华”为主题的日本现代诗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现代诗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在国家政策导引下,大量时局诗、战争诗进入量产阶段,成为该时期日本现代诗歌沦为政治工具的表征;第二,《我思》《四季》等国粹主义诗刊取代现代主义、普罗诗派的地位,成为诗坛主流;第三,诗人的创作意识从现代主义转向国粹主义。
(一)侵华诗的量产
日本文学史中并不存在“侵华诗”这一说法,而是将侵华战争时期以侵略中国为题材,对日军侵略行径进行鼓吹和美化的诗歌作品统称为“战争诗”,在指称上淡化了这类作品的本质属性。在国策的引导和鼓励下,侵华诗无论从创作群体,还是从创作数量上,都达到了较大规模。
明治一代的老诗人首先为响应时局而发声。1932年1月,日军策动“上海事变”,3月明治诗坛的“明星”诗人与谢野铁干(1873-1935年)当即发表《爆弹三勇士之歌》。同年8月,土井晚翠(1871-1952年)刊行诗集《向亚细亚叫喊》,收录大量战争应援诗。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近卫内阁于同年10月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并于翌年制定“国民总动员法”,祭出“八纮一宇”“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等欺瞒式口号试图将侵略战争合理化。“七七事变”之后半年内,日军的战火从华北五省蔓延至上海,并于1937年12月发动了惨绝人寰、震惊国际社会的南京大屠杀。这一时期,高村光太郎(1883-1956年)、中勘助(1885-1963年)、佐藤春夫(1892-1964年)等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有力地应援了日军的侵略扩张。
高村光太郎于“七七事变”后的第二个月即发表诗作《秋风辞》④收录于诗集《伟大之日》(『大いなる日』1942年)。。高村首先引用了汉武帝所作《秋风辞》起首两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作为副标题,接下来写道:“秋风起兮白云飞/今年向南急行的是吾同胞之队伍/等待在南方的是炮火/街上百般之生活皆搓捻成一/毋宁以泪洗胸/哀叹昨日思索之亡羊者/苦于日日食不果腹之面色青白者/街巷中只能做着浮浪之梦者/如今只化作澎湃着热气之死。/草木黄落时/吹遍世间每个角落的夜风虽未变/但造访今年这个国度的秋天/是祖先们也不曾见过的庞大之秋/遥远他方的雁门关,古生代地层迸裂纷飞/过去雁门关向西而闭/今天雁门关面东而碎/越过太原,涉过汾河,望向黄河/秋风一连吹过了胡沙、海洋和座座岛屿。”诗人将日军1937年的侵略行径比作无坚不摧、无往不至的“秋风”,借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美化了日军侵华的不义之举。由“秋风”一句引领的八行诗便以一个文化上位者的姿态歌颂了一路收割着中国百姓生命的日军暴行;由“草木”引领的后八句诗结合时局,预言了日军定能突破雁门关,拿下山西,侵吞华北,无往而不利的强劲走势。然而事实却是在该诗发表后不到一个月内,由贺龙指挥的八路军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取得了“雁门关大捷”,这无疑是对高村等日本“爱国诗人”莫大的讽刺和有力的回击。
继高村之后,中勘助刊行的诗集《大战之诗》(1938年)、《攻陷百城》(1939年)中不仅收录了歌颂日军“战果”迅速扩大的《山西》,而且收录了将南京大屠杀的惨绝人寰置若罔闻的《南京》。佐藤春夫曾以“中国通”自居,并参与过鲁迅作品的翻译推介,曾与田汉、郁达夫①郁达夫于1938年5月14日的《抗战文艺》上发表《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对佐藤春夫在中日战争爆发之际的转向表达了讽刺和愤慨。等有过密切交往,然而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其当即发表《立于卢沟桥畔而歌》对“暴支应援”“圣战”美化颂扬。高村光太郎、中勘助、佐藤春夫等诗人代表了日本诗坛中坚力量对日军侵华的应援,以上诗作均是日本“现代诗中实质性的战争诗的最初代表”②鈴木亨「第八講 第二次大戦下の詩と精神」、『講座日本現代詩史3昭和前期』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275頁。。此后,高村光太郎于1940年至1942年历任日本大政翼赞会文化部中央协力会议议员、日本文学者会设立委员以及日本文学报国会创立总会的诗部会长,成为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民诗人”的领军人物。
由山本和夫编辑、山雅房出版的《野战诗集》(1941年)系诗坛边缘的日本年轻诗人创作的代表。诗集收录了加藤爱夫、西村皎三、长岛三芳、佐川英三、风木云太郎、山本和夫6位“支那事变从军诗人”的作品。诗集的目录“再现”了他们跟随部队深入中国腹地的侵略步伐,如加藤爱夫的《大场镇》《在嘉定》《苏州》《渡扬子江》《南京入城》《黄河》《渡大运河》《在即将攻陷的徐州附近》《徐州入城》《徐州》《在安庆》《泸州》《赴汉口之路》《汉口初夜》《黄鹤楼》,长岛三芳的《庐山》《鄱阳湖》,佐川英三的《北京之眼》,风木云太郎《广东入城之日》等。这使该诗集已然成为日军侵华的历史注脚。
从明治老诗人们的先声附和,到大正诗人们的有力声援,再到青年诗人们的高声呐喊,从诗坛巨擘到边缘诗人皆执诗笔参与到“爱国诗”的大合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青年诗人联盟(2月)、大日本诗人协会(6月)、全日本女流诗人协会(7月)、诗人协议委员会(8月)纷纷成立。侵华诗的量产成为日本现代诗歌军国主义工具化的表征。
(二)以《我思》《四季》为主流的日本诗坛
1930年代以来,在日本当局打压下,日本普罗诗派的发展日益衰落。1933年2月,普罗文学旗手小林多喜二被日本特高警察虐杀,给普罗文学敲响了丧钟。在诗坛白色恐怖日益深重的大趋势面前,一向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现代主义诗人体现出缺乏抗争意识的软弱性。村野四郎指出“国家权力与弱小的现代主义者的意图相比,是无与伦比的强大的。现代主义诗人们……的悲观主义甚至连游击队一般的抵抗威力都没有”③村野四郎「第一講 昭和という時代」、『講座日本現代詩史3昭和前期』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13頁。。与现代派诗人的软弱形成鲜明对照的四季派诗人强有力的发声,吉本隆明指出“昭和十年以降,提起诗就立即意味着‘四季’派的抒情诗。这一派的诗已经超越了单纯一个现代诗流派的问题,它甚至对整个诗概念的整合都产生了巨大的规约力”①吉本隆明「『四季』派の本質——三好達治を中心に」『詩学叙説』、思潮社2006年、221頁。。《四季》的创刊分两期,第一期(1933.5-1934.10)为堀辰雄主编的季刊,共出2册;第二期改为月刊,由三好达治、丸山薰等共同编辑,从1934年10月至1944年6月,共出81册。《我思》创刊1932年3月,停刊于1944年9月,通卷146号。两刊取代了现代派、普罗诗派地位,持续时间几乎贯穿了日本“十五年战争”始末,成为诗坛主流。
《四季》集结了日本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主要的现代诗人,包括三好达治、萩原朔太郎、田中克己、中原中也、伊东静雄、保田与重郎等。其中,堀辰雄、三好达治、丸山薰从《诗与诗论》群派分化出来,意图纠正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主张将日本的传统抒情方式与现代诗相结合,创出主知的典雅的抒情诗。《我思》同人包括保田与重郎、田中克己、中原中也、草野心平、萩原朔太郎、高村光太郎、立原道造等。该刊深受德国浪漫派诗人施莱格尔、荷尔德林的影响,主张高扬浪漫主义旗帜并彰显日本古典美学精神。1938年11月第78号刊的《我思》裱纸内页赫然印刷着大字“汉口占领,皇军大胜”。在《我思》基础上,以保田与重郎为中心,神保光太郎、龟井胜一郎、中岛荣次郎等联名创刊国粹主义文学杂志《日本浪曼派》(1935年3月至1938年8月,共出29册)。从主要的编辑者、撰稿者可见,“四季”派同人三好达治、堀辰雄等一方面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接轨,一方面以神保光太郎、保田与重郎、田中克己等为中介,与《我思》和《日本浪曼派》等国粹主义文学一脉相通。
(三)从现代主义到国粹主义的创作转向
日本现代主义诗艺探索的停滞与乃至退行,一方面与日本国内言论统制下现代主义诗刊纷纷废刊,诗人失去诗歌活动阵地有关,一方面与诗人创作意识的国粹主义转向密切关联。以下以高村光太郎、三好达治和田中克己的创作为例,论述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现代诗人的创作特点。
1.高村光太郎:向日本汉诗传统复归
高村光太郎曾留学欧美,倾心罗丹,译过惠特曼和维尔哈伦,在战争时期却放弃了从欧美文学中汲取的讴歌生命与自由的精神,转而投向国粹主义的怀抱。高村曾于1906年至1908年间留学美、英、法等国期间,由于人种差异而倍受歧视,这种屈辱感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以一种“反西方”的泛亚主义的方式表现于诗歌当中,体现出与军国主义的强烈共鸣。大冈信在《现代诗鉴赏讲座》(角川书店1969年)中指出“曾于《在雨中歌唱的巴黎圣母院》这样的诗篇中热烈称颂过欧洲精神的高村,刺痛其内心深处的‘黄色人种’的劣等感,现在以一种强烈的道义的自我主张形式被补偿,在成为其精神内部之‘叫喊’的诗歌中结晶”。以《秋风辞》为代表,高村光太郎摒弃了现代性的创作意识,转而向明治文明开化以前日本汉诗文传统复归。
“诗”这一文类概念在日本经历了从汉诗系向西诗系转移的过程。在西方诗歌传来之前,“诗”在日本即指汉诗,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仿制镜”“国姓爷”②関良一「第一講 伝統詩歌と近代詩」、『講座日本現代詩史1』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3-4頁。式地移植。1882年,在被视为日本现代诗嚆矢的《新体诗抄》中,编撰者井上哲次郎首次提出“夫明治之歌应为明治之歌,而非古歌,日本之诗应为日本之诗,而非汉诗,此乃作新体之诗之所以然也”③井上哲次郎:《玉之绪之歌·小引》;转引自陈璇《中日现代诗歌写作比较研究——19世纪末现代诗始发点对“新体”的想象》,《写作》2018年第5期。。日本汉诗在西方文明大量袭来之时不可抵挡地衰退,至20世纪初,“诗”最终成为指称起源于西方poetry的“新体诗”的专有名词。而1914年高村光太郎的诗集《道程》的问世,恰恰标志着日本现代诗在形式上摆脱了七五定形律的束缚,确立了口语自由诗的发展道路,并实现了明治、大正以来,具有现代意识的日本诗人通过积极地接受和转化西方文学来摆脱汉诗传统的影响,树立“现代日本诗歌典范”的努力成果。然而,在《秋风辞》中,高村通过对汉诗汉典的摄取与模仿获得诗意生成机制,从日本现代诗的发展角度来看,这无异于创作意识的倒退,体现出高村向日本文化传统中对汉文化“宿命式”的复归,于是此处形成一种吊诡现象——用来补偿其“黄色人种”劣等感的“道义的自我主张”的恰恰是其蔑视和侵略国度的古典诗歌,这到底是一种文化的自信还是不自信?而借汉诗美化侵华日军“圣战”的行径本身也说明了日本战争诗的自我欺瞒性。
2.三好达治:向日本传统感性复归
三好达治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之后,相继翻译了波德莱尔、梅里美、弗朗西斯·雅姆等大量法国诗人诗作。其作品亦深受这些法国诗人的影响。其第一本诗集《测量船》(1930年)将日本传统的抒情性与西欧象征诗的批判性融合一体,开拓了新的抒情趣味,三好借此确立了诗坛地位。然而自《故山迎英灵》(1938年9月)一诗发表以来,三好的创作逐渐向战争诗转移。此后《草千里》(1939 年)、“战争翼赞诗集三部曲”即《捷报至》(1942 年)、《寒柝》(1943 年)、《干戈永言》(1945 年)的相继刊行,标志着三好成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坛“最有力的国民诗人”。从初期的《测量船》到后期的“翼赞诗集三部曲”,诗人的创作意识发生了重大转变——西方现代文学影响日益淡薄,传统诗歌形式与语言的运用大幅增加,抒情方式上也从个性化的情感表达转向忠实于大众宣传的“万能”的意象表现。《昨夜落于香港》即为三好此类诗歌的代表作。“昨夜落于香港/主基督降诞祭日黄昏/那维多利亚峰的山寨上/翩翩然他们的白旗招展!/百年来,他们是东亚海域/倒买倒卖的海贼/是魔药鸦片的押卖行商/巧取豪夺了香港——//那香港岛上/东海猛鹫纷飞交织/巨弹雨下/重炮炸裂/净化万物的凶猛火焰焚尽了连日来的病灶/此刻在那奸恶与诡诈与骄慢的一个世纪的荒蛮无理之后/……啊终于将那曾经东亚之天地最大的悖德与最大的屈辱/拂拭而去了”。该诗收录于1942年刊行的《捷报至》,创作背景为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侵占。诗人将日军的战机轰炸形容为“东海猛鹫的纷飞交织”,“净化万物”的烈火焚烧,而香港则是其笔下的“最大的悖德与最大的屈辱”。
吉本隆明指出三好诗中 “这种情绪的残忍感觉是三好将原始神道进行论理的开掘所带来的传统感性的一个顶点”,而这种“传统感性”的本质与原始人的自然观无异,即“从日常生活的需求出发,将渔猎或屠杀其他部族天然地作为一种手段,杀戮、巨大铁量的冲突、思想的对立,这一切不过是进入他们自然认识范畴的某个部分”“他们无法区分对社会的认识和对自然的认识。权力社会也被纳入他们的自然观范畴,于是权力社会与权力社会的国际性抗争,撼动的也仅仅是他们的传统感性”①吉本隆明「『四季』派の本質——三好達治を中心に」『詩学叙説』、思潮社2006年、234-237頁。。吉本认为三好等四季派诗人所体现出的残忍感性与原始人的野蛮无异,因此将此类战争诗的创作称之为“返祖”退行。而三好、高村等诗人之所以会抛弃曾经习得的西欧文学精神,向国粹主义转变,源于在他们的观念意识里,“西欧的现代意识与日本的传统意识基本无矛盾、无对立、无瓜葛地以原始形态并存”。当战争爆发,必须做出取舍时,他们的“西欧教养便如尘芥般消弭得无影无踪,之后如同庶民的大多数所遵循地那样,完美地返祖退化而去了”②吉本隆明「『四季』派の本質——三好達治を中心に」『詩学叙説』、思潮社2006年、231頁。。而这正是现代性与封建性(反现代性)并存的日本社会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诗人创作意识的集体退行导致了现代性艺术探索的停滞,因此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其本身的现代诗歌艺术而言亦是沉重的打击。
3.田中克己:浪漫主义与国粹主义相抱合的诡异秘境
《我思》同人田中克己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诗集西康省》(1938年)和《大陆远望》(1940年)中收录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献与传闻。在《大陆远望》序言中,田中言及“大陆”(中国)之于其创作的意义:“这数年间,带给我作诗刺激的是大陆。作诗时,我总远望着它,并始终将它置于我的意识里,因此这数年应该是我人生中诗写得最多的浪漫时代。”然而,田中所谓的“大陆意识”依然是将“中国”置于军国主义的侵略意识下,将日本恒常民众的残忍感觉与优美典雅的审美意识相并置,创造了一种“艺术至上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抱合的诡异秘境”①鈴木亨「第八講 第二次大戦下の詩と精神」、『講座日本現代詩史3昭和前期』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278頁。。
田中在《皇纪二千六百年》(收录于《大陆远望》)中这样写道:“当第一缕阳光/……/将富士山顶染成了鲜红之时/近卫步兵第一连队吹响了起床号/我家儿子睁开了眼睛/西方尚在沉睡 在睡梦中/每个人都做着深深期待之梦/于是在北京、济南、太原、开封、安庆、南京、杭州、南昌、武昌、广东、南京这十一座省城当中/不眠的哨兵等候着清晨……”在后记中,诗人讲到这首诗初发表时将皇军占领的城池只写了九个,“不好意思非常抱歉弄错了,但也因此为皇军占领的无以计数的中国城市再一次感到欢欣。”在《大陆远望》一诗中诗人以问答的形式写道:“‘你为何一直望着那个方向/那片海的彼岸有着粗蠢的容貌/有着五千年的诡诈与流血的历史/黄色之民组建村落建设都市/在那里日日是争吵的喧嚣与愚蠢的奔忙/除此之外,你还眺望着什么’/……”。这里田中克己展现了与德国纳粹分子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如出一辙的人种优越论。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看到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现代诗在军国主义统治时期,普罗诗派遭遇毁灭性打击,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方法遭遇“冻结”,以侵略为主题的诗歌创作成为主流。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除了社会时局的影响外,离不开诗人主观上的艺术选择。高村光太郎、三好达治、田中克己等诗人主动放弃了现代性的诗艺探索,转而向日本旧诗文传统复归,以传统感性迎合时局号召,使诗歌沦为军国主义国家意志的宣传工具。
四、1930年代的中日诗歌交流
对抗并非战争时期中日现代诗关系史的唯一底色。中国诗人与日本反战诗人小熊秀雄、金子光晴在战时的文学交流意义深远;另一方面,从世界性的现代主义诗潮传播角度看,燕卜荪、奥登等西方诗人在中日两国展开的文学活动又将中日现代诗歌发展纳入到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范畴。
(一)反战诗人小熊秀雄、金子光晴与中国诗人的交流
小熊秀雄(1901-1940年)出身于日本北海道,其诗歌创作从前卫诗运动出发,后积极投身普罗诗运动。1935年刊行诗集《小熊秀雄诗集》《飞橇》。其第三部诗集《流民诗集》(1947)本应于1939年出版,但受时局影响却未能如期刊行。1940年因长年贫病交加,小熊死于肺结核,享年39岁。在《飞橇》《长长秋夜》等长篇叙事诗中,诗人借饶舌与幽默的表现手法进行了尖锐的社会讽刺和深刻的人间洞察,其视野不仅仅局限在日本,还扩展至中国、俄罗斯、朝鲜乃至北海道原住民阿依努族人等,不失抵抗精神的同时无损诗歌语言的清新。小熊作品所展现的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样感染了中国诗人雷石榆和蒲风。雷石榆在留日期间曾于诗刊《诗精神》发表诗文,并于1934年11月该诗刊同人的《一九三四年诗集》出版纪念会上与小熊有过直接会面,现存有二者的诗文往来稿件30余通。蒲风曾于1934年冬赴日留学。1936年4月,蒲风访问了当时正在流亡中的郭沫若,并询问其是否读过小熊的《飞橇》②蒲风:《郭沫若诗作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237页。。秋吉久纪夫认为蒲风的诗集《黑陋的角落里》(广州诗歌出版社1938年)幽默讽刺的创作风格鲜明地受到了小熊的影响①秋吉久紀夫「小熊秀雄と二人の中国人留学生」、『中国現代詩人論』、土曜美術社、2013年、142-163頁。。
“正好这个时候,郁达夫带着郭沫若秘密地来到了我家,于是就请他为书的封面题写了鲛这个大字。送去印刷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爆发了。”(《诗人》)诗人金子光晴(1895-1975年)回忆诗集《鲛》(人民社1937年)出版前夕郁达夫为其题写封面,反映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怀有正义感的日本诗人与中国诗人们的精神契合与密切联系。诗集《鲛》收录了金子游历欧洲、东南亚,包括中国的上海和香港等地之后创作的诗篇。其中大量作品讽刺了昭和初期日本政府弹压的社会现实,凸显了金子的“反骨”。日本战后诗人田村隆一曾感言“太平洋战争之下,仅有金子光晴一人续写着真正配得上‘战争诗’之名的诗”②田村隆一「地獄の発見」『田村隆一全集6』、河出書房新社2011年、463頁。。对于中国而言,金子光晴不仅与中国诗人郁达夫、郭沫若有过极具象征意义的交际,并且是在中日战争期间,走过中国的战场之后直言不讳地说出“日本是侵略者,是强盗,是人类文明的倒行逆施者的唯一的日本诗人”③鈴木亨「第八講 第二次大戦下の詩と精神」『講座日本現代詩史3昭和前期』、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283頁。。

(二)威廉·燕卜荪与W.H.奥登在日本和中国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后期象征主义诗潮兴起,作为国际性的文学运动,其影响范围涉及中国和日本。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危机与战争恐怖的时局下,威廉·燕卜荪与奥登等欧洲诗人在日本和中国展开的诗歌教学与文学交流活动,更加深了中日两国在世界性后期象征主义诗潮传播下的内在关联。
燕卜荪于1931至1934年间曾先后任教于东京文理科大学、东京大学。在日本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氛围中,燕卜荪工作了三年。1937年至1939年与1946年至1951年,燕卜荪曾两度来华工作,以第一次影响最为深刻。在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穆旦:由来与归宿》、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周珏良《穆旦的诗与译诗》等文章均对燕卜荪任教西南联大的情景进行了追忆。可以说,燕卜荪在日本和中国的教学活动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奥登与依修伍德于1938年1月19日至6月12日期间访华,此后奥登创作了1930年代 “最伟大的英语诗篇”④Edward Mendelson,Early Auden,London:Faber &Faber,1981,p.384.十四行组诗《在战时》。随着奥登的亲身来访以及燕卜荪的介绍,中国掀起了“奥登热”。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中国新诗诗人群体深受奥登诗歌的影响,最终推动了中国现代诗向前发展。日本左翼诗刊《新领土》(1937年5月创刊,1941年5月终刊,共出48册),刊名便来自于奥登的文学阵地New Country。日本学者中井晨指出《新领土》正是通过广泛译介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流的国粹主义倾向的刊物相对抗,“为了克服‘国家主义’,通晓‘国际主义的文学、文化基准以及动向’才成为必要”⑤中井晨『荒野へ―鮎川信夫と『新領土』(1)』、春風社2007年、10-11頁。。在战时言论统制日益严苛的情势下,《新领土》仍然译介了奥登的《西班牙》(1939年7月号)、《1939年9月1日》(1940年1月号)等名篇,并刊载了多篇斯彭特的奥登论。因此,在抗战时期被中日诗坛译介的奥登,将具有反侵略和国际主义意识的中日现代主义诗人联结在了一起。
五、结语
20世纪30年代是中日现代诗歌关系发生转折的重要时期。以此为节点,中日很多现代诗人的创作意识和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巨大转变。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现代诗在抗日战争期间收获了大量优秀的艺术成果,孙玉石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拓展期(1937-1949)”①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而日本则经历了现代诗歌艺术探索史上的“暗黑时代”②村野四郎「第一講 昭和という時代」『講座日本現代詩史3昭和前期』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12頁。。然而,小熊秀雄、金子光晴等诗人在战争时期的反抗为和平时期中日现代诗歌的交流留下了火种;世界性现代主义诗潮的历时性接收又使中日现代诗共同加入到“世界文学的精神循环”。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状况决定了两国诗歌未来的发展走向。因此,战争时期的中日现代诗歌比较研究是和平时期两国现代诗展开对话与交流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