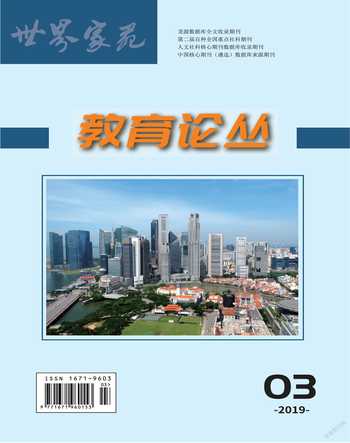偏见与孤独
吴晓静 闫盟
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
一个优秀的灵魂,即使永远孤独,永远无人理解,也仍然能从自身的充实中得到一种满足。
历史的记忆即便是一座古代的废墟也依然可爱。
——题记
说来颇为可笑,想也略有荒唐,我对于埃菲尔铁塔的认识,竟然源于张抗抗先生的散文名作《埃菲尔铁塔的沉思》。然而起初,这篇游记散文并没有给我以很大的心灵冲击和很多的思考感悟。作者张抗抗是谁?这到底是一篇怎样的文章?笔者归根结底要阐述和说明什么呢?出于教学的客观现实需要和教师的教书育人目的,我坐下来开始一字一句地研读。慢慢地,徜徉在墨色的文字当中;渐渐地,心也随着文字跳跃起伏。静静地,合上书本,不禁自觉,原来我是个很有偏见的人。正如题记所说,如果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不管是作者对于铁塔,还是我对于游记文章,都是如此。
这是一篇极其独特的游记作品,作者并没有像常见的游记散文那样,大手笔地对游览对象进行浓墨重彩、肆意渲染的描写,而是把兴奋点出人意料地放在了由登临埃菲尔铁塔所触发的心理感受和主体思考上面,从而使文章具有与众不同、独出心裁的艺术魅力,也展示了作者笔下埃菲尔铁塔独一无二、独树一帜的审美风采。
文章中在登塔之前,作者对埃菲尔铁塔充满了“无知的偏见和戒心”,对其并没有多少特殊感情和崇敬心理,正如文中所写,“在印象的底版中,它只是比一座电视塔略高些的大铁架;而在视线所及的图像中,它又淹没在巴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间……它也似乎只是一个小摆设,甚至,有那么一点被压抑的冷峻。”写到这里,不禁想起第三代诗人韩东在《有关大雁塔》中所写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由此可见,在作者张抗抗眼中的埃菲尔铁塔并无特别吸引人之处。
然而,在登塔之后,作者的思想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原以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无情的——我却发现你是一个不露声色的老父……”,曾經的“大铁架”变成了“一个永远矗立的丰碑”。不仅如此,作者还深切而严肃地告诉我们:“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这是作者登塔的收获和感悟,也是铁塔给作者的发人深省的启示,更是铁塔无形中对作者情感和心理的直接征服。这既证明了“百闻不如一见”的千年古训,更暗示出铁塔的无穷魅力和强大震撼力,它征服了一个怀有偏见和戒心的人,一个“唯独没有膜拜它”的孤高而冷傲的灵魂。作者克服偏见的过程,就是“我”被铁塔的魅力所征服、所吸引的过程。
作者情感变化的心路历程是颇有代表性的,也是耐人寻味、回味无穷的。埃菲尔铁塔由一个“曾经被保守的巴黎强烈排斥和憎恶”的“大铁架”一跃而变成了巴黎市的象征与标志的过程,由一个“标新立异的怪物”变成了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这座丰碑不光矗立在坚实的土地上,更是矗立在人们宽广而宏大的内心。
文章既表现了埃菲尔铁塔的雄伟壮观,也以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感受并抒写了它的孤独:“它雄奇,却也孤独。它没有对话者。只有风,只有云,只有飞鸟,是它寂寞的伴侣。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它冰凉的铁杆,它的内心却依然孤独。”作者运用拟人化的写作手法,独具匠心地表现了铁塔孤独而寂寞的心理世界。这是作者“沉思”的独特之处与深刻之处。从文中可以知道,一百多年前,埃菲尔铁塔“在一片嘘声里”诞生,它曾一时被视为“标新立异的怪物”而受到“强烈的排斥和憎恶”,今天,尽管它已经成为景象非凡的巴黎的象征,但依然有众多的人们,如登塔前的作者一般的人儿,对它存有“无知的偏见和戒心”。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它确确实实是孤独且寂寞的。
其实塔是如此,人又何堪?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现实社会中又有多少像铁塔一样高大坚韧而又孤独寂寞的人呢?一生中留下大量惊人画作的梵高,直到去世后才逐渐闯入人们的视野;创“日心说”的哥白尼,丰富发展哥白尼学说的布鲁诺,受到教会的惨烈迫害而处以残酷火刑;以及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机车的斯蒂芬孙,曾经一度遭到了人们无情的冷嘲热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爱国诗人屈原殉道汨罗江,“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不畏权势柳宗元被贬永州,“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旷世才子苏东坡被贬黄州等等,他们都是高大坚韧而孤独寂寞之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有在哲学、艺术、政治上有杰出成就的伟人,无不具有孤独而忧郁的气质。”他们因他人的偏见狭隘而凋零陨落,却又因各自的超群脱尘而孤独寂寞。因为孤独,所以伟大。正所谓“古来圣贤多寂寞,超尘脱俗留其名”。诚如周国平先生所言:“一个优秀的灵魂,即使永远孤独,永远无人理解,也仍然能从自身的充实中得到一种满足。”
然而令人沉思的是,作为旁观者芸芸众生为何总有那么多的偏见与狭隘?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不同”持宽容之态,为什么不能对“无知”保敬畏之心?不能也不敢设想,埃菲尔铁塔被摧毁,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吴哥窟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玛雅文化遗址被认为是落后愚昧。有如不能设想,几千年前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接合,宋版图书需要上塑封,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如此这般简直荒谬至极。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废墟》中写到“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令人遗憾的”,而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则是黯淡无光、让人绝望的。因为历史的记忆即便是一座古代的废墟,也依然可爱;而最重要的是,这份记忆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构建与传承。
(作者单位:南昌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