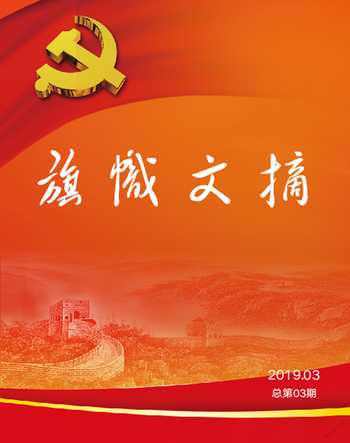新西兰南岛的奇幻旅程
张海律
列车漫悠悠地向前开,一个多小时后,窗景有了变化,黄色的野菊花,深绿色的树林,牛奶蓝的河水,灰褐色的山坡,白茫茫的雪峰……由近及远,一层层接力般地铺开。这雪峰景致感觉和我前不久在青藏高原看到的差不多,难怪2018年最新一部《碟中谍》电影中直升机大战和悬崖PK的戏份会选在新西兰。
最近有地质学家在经过严谨的调查后声明:“新西兰并不是几个孤零零的岛屿,而是沉没的西兰大陆(Zealandia)冒出海面的高原部分。”不少地理爱好者认为这纯属吃饱了没事干的研究——喜马拉雅还不是从海底冒出来的,那怎么不把太平洋也当成彻底沉没于海中的地球第一大陆呢?另外还有科学家说,如果没有风化侵蚀导致山体不断滑坡,太平洋板块和澳印板块的相互挤压,将把南阿尔卑斯山脉推向接近2万米的高度。
列车翻过山口,进入西岸大区,天气骤然放晴,彻底敞开的F车厢挤满了甘愿迎着寒风拼命自拍的乘客,两旁从农田到溪谷、从雪山到雨林的奇幻变化引得一群印度游客大呼小叫,吹起快乐的口哨,我觉得此时这种表达并不算失礼,面对此番胜景,就该高声发出赞美才是。
我的第—站是格雷茅斯以南12公里的棚户镇(Shantytown),这是一个“做旧”主题的小镇,试图复原19世纪淘金热时代的面貌。一列名为Katie的老旧火车,挂着冒烟的蒸汽机车头,等着将下一批游客运往淘金区的矿井。这列蒸汽机车1896年出产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一直在附近矿区工作到1969年,如今又作为一个环旧体验项目,负责把客人送到1.5千米外的伐木林区,再折返回中间的淘金区。向导老彼得打算向我们展示百年前的溜槽选矿工艺,电机喧嚣了5分钟后,他走出机房小屋,无奈地排摊手:“抱歉,这家伙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开始带领孩子们去用脸盆筛金,顺时针把河水、泥沙和石块晃出来,质量最重的金子就会留在盆底。我想,19世纪60年代,第一批远道而来的中国矿工,每天干的最多的活计就是扛运沙石和河水筛金吧。复原了教堂、药房、报亭、剧院的棚户镇,也在角落一隅展示了所谓的Chinatown,遗憾的是,和世界各地早期的中国移民一样,这些淘金者忙着赚钱养家,从未有过意愿和计划为自己在异域的存在留下任何证明,如今他们就象是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一样。
从棚户镇往南开40千米,是西岸树顶步道(West Coast Treetops Walkway)。这个玻璃步道位于雨林之中,距离地面20米,长450米,空中的视野特别好。林中的主要树种是红松和卡玛希树,也有不少珍奇鸟类。在20米高的瞭望塔顶眺望,西侧是连绵的雪山,脚下与雨林相连的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水域,我一度以为那就是塔斯曼海,查了一下手柳地图才发现原来是马希纳普阿湖(Lake Mahinapua),它曾经是一个渴湖,后来随着沙丘在岸边不断堆积,成为与大海相隔500米的内陆湖。
我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地,是南岛三大冰川之一的弗朗茨·约瑟夫冰川(Franz Josef Glacier)。西海岸的6号公路继续沿着紧挨大海的雨林南行,大部分时间都是车迹罕至、七弯八拐的山路,偶尔经过限速50千米的村镇,也罕有人迹。
观赏冰川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热门生意。沿途只要是有湖泊的地方,公路局都贴心地布置了车位充足的观景台,以及可以钓鱼、看星空、过夜的露营地。西岸国家公园北口外那个400多人口的小村已发展成为有着强大旅游接待能力的弗朗茨·约瑟火镇。我入住的雨林僻谷(Rainforest Retreat),在林间各处有十来套家庭别墅和三四十个青旅式宿舍间,可以仰望星空的户外温泉一直开放到晚上22:00,由于闻不到一丁点儿硫黄味,我估计这些温泉水是城镇和酒店将天然热泉统一过滤后打造出来的。
充足的降水,在高海拔处持续累积出近20米深的清澈冰面,并进一步推进到陡峭的山谷地带。在地球的气候变化过程中,这两条冰川如同一对共同进退的舞者,15000—20000年前的上一个大冰期,它们曾共同迈进到塔斯曼海海岸,之后又一度退缩到比现在还远的山谷深处;14世纪开始的小冰期,让这对舞者重新向海毕进发,1750年到达了这一时期的最远处,现在还能看到当时的印迹;后来又是小进大退,到了如今的位置。游客最多只能跟随向导,乘直升机落在肉眼所及的冰瀑前面,徒步穿过峡谷走到冰床上已再无可能。因为会给直升机观览带来严重威胁,整个冰川河谷地带也禁飞无人机。
我选择跟随向导徒步进入河谷,远观弗朗茨·约瑟夫冰川。在巨石林立的观景点,可以看到这条12千米长的冰川吐出来的舌头部分,蓝白桕间的冰川“舌苔”中央留有一大片灰褐色的石层,如同刚舔过巧克力一般。回程时,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步道旁边安插一块新的招牌,上面写着“1908年,冰川曾到此终止”。不过百年,已是沧海桑田。
顺6号公路往回赶了130千米,我在黄昏时分来到霍基蒂卡(Hokitika)城南的一块广告牌下,广告牌上白底黑字地写着“West Coast Scenic Watewavs”(西岸景观水道),我四下张望,只能看到不远处的大海,哪有什么水道。一辆皮卡停到我跟前,司机探出头来:“你是想参加水道落日航行体验的那位中国人吧?我叫Cavin。”Cavin将自家一栋两层的屋舍和周围的几间小屋打造成了民宿,他叫上小儿子和3条狗,拨开小屋旁的深草,发动起水沟边的一条河船,带我深入满布沼泽芦苇的河道。这条细长的水道一直通往马希纳普阿湖,水道北侧是136千米长的西岸荒野步径(West Coast Wilderness)的一部分,南侧有被改成了骑行道的一段铁轨,一百多年前这段轨道曾用于连接森林与海岸,运送新鲜砍伐的原木。Cavin说,这片水道、沿岸步道和废弃铁轨改的单车道,是新西兰仅有的30%非农用地的一部分。
天完全黑了,我来到霍基蒂卡北郊的一处萤火虫树林。前来感受“点灯”仪式的游客不少,一个个谨慎地慢慢走着,不敢说话,甚至不敢大声喘气,生怕惊扰了那些泛着微光的精灵。很多人没克制住掏出手机拍照的欲望,虽然屏幕上只有漆黑一片。
新西兰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宁静、安全的地方,但1941年这个峡谷附近的KOWhhitirangi村发生过一起连环命案,一个性格暴烈的男子持枪打死了5个邻居,后来又干掉了在家门口蹲守的两名治安官,新西兰举国震惊,在海陆空全方位立体搜索下,这名男子中枪、被捕、入院、死去。英国知名导演迈克·内威尔(代表作有《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和《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等)曾经来到这里,1981年他根据这个血腥的故事拍摄了电影《坏血》。
霍基蒂卡乡间的自然美景很多,不过在这糟糕的阴雨天,还是乖乖躲在城里的博物馆和画廊为好。这一带山里的树木与河边的翡翠吸引来不少巧手的工艺师,JimGordon从14岁开始就迷上了木雕,尤其喜歡红松发出的那种香味,他称其为“树之灵魂”,40年过去了,Jim Gordon始终和他的“灵魂”在一起,如今就守在霍基蒂卡工艺画廊的一角,等着和识货的客人聊上几句。Steve Gwaliasi开了一间名为“骨头与石头”(Bonz‘n’Stonz)的翡翠雕刻课堂,在作坊里练手的大多是附近的居民。
霍基蒂卡盛产新西兰绿玉普纳姆(Pounamu),当地人总是玉不离身,不过,根据毛利人的传统,普纳姆千万不能自买自戴,只能作为礼物赠予他人,否则会带来糟糕的霉运。无论是当年的欧洲殖民者,还是近年来大规模涌入的华人和印度人,每个喜爱普纳姆的人都相信毛利人的这一警告,只将它作为一个漂亮的礼物。
回到格雷茅斯,时间还早,我在一家咖啡店又重温了一遍曾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新西兰电影《钢琴课》。影片开头,霍莉·亨特饰演的丧夫哑女带着女儿从英格兰远渡而来,穿着纷繁的维多利亚式裙装,被船员踉跄着抬上沙滩,迎亲的夫君还没来,船长问调皮的女儿:“你妈妈要先跟我们去尼尔森吗?”女儿恶狠狠地说:“她说就算被土著煮了吃了,也不愿再上你那艘臭船。”而我正准备要登上干净清爽的城际大巴。顺着狂野西海岸的另一段,北上尼尔森。
(中国国家旅游 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