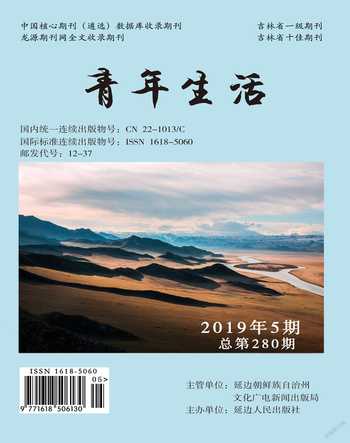基于村委选举探析非体制精英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
孙雨晴 张莹
摘 要:非体制精英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部分,对乡村生活起重要作用。在乡村选举过程中,三类非体制精英通过自身的社会地位参与或影响选举结果,通过选举产生的村委组织一种是以裙带关系为主,另一种则基于个人魅力,两种类型的基层组织受非体制精英的支持,在村内诸多事宜中与非体制精英共谋,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虽在形式上发生更替但在实质上仍受部分非体制精英操控。基层组织对上级政策的执行力度及对村内居民的支持力度大打折扣,两种力量主导下的村委在社会治理中都面临各自的困境,乡村社会治理任重道远。
关键词:非体制精英;乡村社会治理;选举
在我国发展阶段中,农村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建设及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内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可追述到20世纪30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认为必须以“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为主入手,改变乡村积贫积弱的现象。而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则深入农村,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写作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书,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同意权力、横暴权力等一系列概念为乡村治理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张厚安教授在湖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后撰写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等影响巨大的著作。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教授从研究的思路、方式、方法以及理论前景等方面对中国村民自治的相关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村民自治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发展前景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著作《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开创了中国村治研究的新局面。仝志辉与贺雪峰在《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中将乡村治理中的治理主体划分为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无政治村民。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非体制精英在村庄中有一定地位,为了解乡村社会治理是否受其影响,本文通过论述非体制精英对村委选举的影响及村委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展开论述。
一、非体制精英与基层选举
基层选举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方式,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依据实地调研可知,2017年10月份村委换届选举主要受三种非体制精英的影响:第一种是基于家族关系,同姓家族中所有人的选票都汇聚到一人手中该人决定选票去向。第二种是基于经济关系,非体制精英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购买”选民手中选票。第三种是基于声望,非体制精英通过个人魅力吸引选民选票,从而赢取村委竞选胜利。下文通过2017年前后的选举情况进行分析:
依据实地调查情况可知,2017年之前的选举中,时任村主任通过亲属及亲密伙伴的拉票与经济支持得以连任,并在任职期间通过土地拨划等方式“报答”投票者的支持。以经济及人脉关系为主的非体制精英在换届选举时对竞选结果起决定作用,而且在选举结束后共谋双方通过一定方式互相照应,共享竞选成功所得的资源。而2017年换届选举的现任主任在村民中声誉极高,其“自力更生、有闯劲、年轻、见识广”等一系列有点使其在乡村事务中拥有较高的的话语权,同时为其赢得2017年村委选举提供了充要条件,村民对现任村主任信任度极高。由此可见,村委竞选的得胜者作为非体制精英的典型代表,在不受政策限制的前提下,以经济、人脉为主的非体制精英更容易为竞选者赢得胜利,而以个人魅力为主的竞选者则存在较大的竞争压力,对选举环境的要求也较高。
以人脉和经济支持为主的竞选者在获胜后为报答非体制精英的支持,在管控管控村委后,通过一定方式履行竞选前对支持者的承诺,村民在竞选过程中将自己的票委托代投,代投者通过掌控大量选票与竞选者达成共谋,选举成功后村委主任动用公权力来回报支持者的恩情,村委主任“以公报私”的行为给村委蒙上“贪污勾结、腐败不堪”的面纱,进而引发公众对村委的不满。而造成这一状况最重要的一方面原因是村委竞选成功无法离开非体制精英的支持。因此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对于对少数群体利益的维护引发的不满。
而凭借个人魅力取得竞选胜利的非体制精英在村委治理过程中受到多方阻碍,竞选时的个人对村民的承诺在实际情况中难以兑现。同时,现任村主任在施政过程中被前任村主任的支持者加以阻挠,多项政策无法得到落实。由此可知,卸任后的非体制精英及其支持者在败选后会通过不合理手段给新主任制造问题,在没有处罚依据的情况下,村委无法对其行使处分管理,因为给村民留下“不作为、软弱无能”的印象。村委与落选者及其支持者的对抗关系使得村委在村务执行中面临更大问题,村委僵化迟滞的处理方式也引起村民的不满。
非体制精英参与或引导的选举在村落内部造成不合理的共谋行为和竞争行为,从而导致村委的公信力降低,村委乡村治理的开展与执行中面临多方阻碍。非体制精英利用自身的优势对基层选举进行直接干预,影响选举结果。在此情况下,村委的威望并非像科层组织一样附加在机构上,相反一直受到非体制精英的压制,在压力机制影响下村委在乡村社会治理中面临多种限制因素及困境。
二、村委与乡村社会治理
在非体制精英的影响下形成两类村委:一类是以经济和裙带关系为支撑主体的村委,另一类是以个人魅力为支撑主体的村委。上述两类型村委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有不同的模式,同时也面临各自不同的困境。
(一)裙带经济关系为主体的村委在乡村治理中的困境
裙带经济型村委在赢得竞选后,利用公权力回报支持者,在实际村务工作中却持相悖态度。竞选之初候选人与非体制精英共谋,已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在竞选成功之后,为兑现互相帮助的承诺,共谋双方利用公权力为自己谋利,当选者讨好支持者,支持者获得相应回报,双方通过利益交换稳固合作关系。
村民对于裙带经济关系为主的村委并不满意,但受到拉票时所获利益的限制,其相互关系无法中断。而非体制精英掌握大量选票及经济资源,为竞选者选举成功提供重要帮扶作用,所以村委在治理过程中继续维持原有的相互利益关系,村民得益后对非体制精英与村委的关系选择视而不见,乡村治理陷入维护少数群体利益的困境。村委在利益分配时无法绕过共谋方,其次如果无法维持共谋关系,后续村委竞选将面临新的挑战,所以乡村社会治理始终无法规避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多数民众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对非体制精英与村委的过分亲密关系感到不满又缺乏相应的约束办法,所以通过消极抗议等方式,试图阻止村委管理者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侵害,但是在不涉及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村民仍對村委与非体制精英的共谋关系持默认态度。非体制精英的利益成为村委首要维护的部分,这也成为裙带经济型为主的村委在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困境。
(二)个人魅力为主体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困境
作为非体制精英的个人通过合法手段及个人魅力赢得竞选后,试图对前任村委的消极行为作出改善,并兑现竞选承诺努力为村内做贡献,营造一种新的村委形象,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总存在不和谐的声音及破坏行为对其进行阻碍。
现任村主任在政策提议及村内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本身以村民利益为出发点,但部分村民对其政策表示反对并通过对修路工具的破坏等行为阻碍项目继续进行。实施破坏者与前任村主任关系密切,现任村主任对村内蓄意破坏行为既无追究源头又无处罚条例。而在这两种困境的支配下,村庄社会治理在很多方面被束缚多数政策无法施展开,这也导致村委被塑造为“软弱无为”的形象。现任村主任的成功竞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策的公平,其积极上进的行为促进竞选成功,在其实现了从非体制精英向体制内精英的转变后,以家族关系和以经济关系为主的非体制精英即刻对其产生隔阂态度,基于声望获取竞选胜利的村委在政策实施及项目建设等多个方面都遭到各方的阻挠,这种恶意的阻挠导致村民对村委“无能”的认识不断加深,现任村主任声望逐渐递减。
(三)村民对两类型村委的看法
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委民主选举是村民实行自治,选举自己心仪当家人的重要途径。而村民选举时,由于自身的限制因素,将自己的选票委托给亲属代投,这种委托机制在我国法律条文中只限与近亲之间,但是有人利用制度漏洞恶意收买选票,直接影响投票结果。村民在选举之初又过分重视眼前的利益,他们认为村主任不是个人的村主任,如果村委能力没有区别,村民默认的选举态度为是否对自身有利。
村民的相互推诿行为以及对结果的漠不关心使得村委选举的结果无法达到公平公正的要求。竞选者在村内大环境的影响下,动用非正式关系进行拉票并多次取得竞选的成功,而一旦政策要求严苛之后非正式关系无法动用,竞选结果则相应的发生变化,落选者为彰显自己的實力,通过消极抵抗的态度给新当选者及村民传递一种信号——“你能拿我怎么样,还是我说了算”。在此情况下,村民对相对公平情况下选举产生的新任村委逐渐产生抵触情绪,其态度倾向逐渐向传统的裙带经济关系主导的村委靠近,以维持自己当前可获利益。同时,村民在竞选村委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利益倾向型态度,他们对村委是否办事只存在口头上的议论,一旦自己无法用选票换取眼前的利益便心生不满,村委选举便始终与经济利益挂钩,村民所持的态度使非体制精英在村委选举的实际过程中享有更多操控机会,因而多种不合理的共谋行为频繁地发生在村庄内。
民主选举的本意要求是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把“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有本领、真心愿意为群众办事的人”选进村委会班子。也就是说,选出一个群众信赖、能够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村委会领导班子。但是在实际情况中,非体制精英动用自己的私权利,如经济支持、家族支持等,这种私权利直接左右了村委选举。并且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两种情况,竞选成功则与支持者共谋,竞选失败则与新村委抗衡。村民置身事外的态度使非体制精英实际享有更多操控机会,因而各种不合理的共谋行为频繁地发生在村庄内。
三、结语
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中最重要的一环,选举产生的村委是民众利益最重要的代表者,也是倾听民众诉求实施社会治理的管理者。非体制精英是乡村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内部事务的决策产生起关键影响作用。
在实际情况中,非体制精英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参与或引导竞选,而竞选所得的两种村委在治理过程中又面临不同困境。村委选举过程及选举后产生的矛盾正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最先应该改变的就是村民的观念,互相推诿、得过且过、重视利益是大家都有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得最应该公正透明的村委选举恶意被人操控。其次是监督机制的落实,我国的村委选举虽然有法规规定,但实际情况却与规定有较大出入,监管机制需不断改善加强。最后是村委角色的转变,村委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表者在处理与村民关系时始终以管理者的身份自居,但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将村民置于事外导致村民对村委项目产生排斥感,现阶段我国学术界对于乡村与民众关系的研究数不胜数,村委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用合理方式引导村内非体制精英及村民共同参与到乡村事务管理中,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和谐有序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乡村社会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参与者不仅限于村委,每个居民都身入其中。用积极正确的态度进行选举。在监督机制上也要着重加以落实,避免竞选者通过不当关系拉取选票。村委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表者在处理与村民关系时始终以管理者的身份自居,村内绝大多数事宜都是由村委制定加以实施的,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将村民排除在外,这种行为更加深了村民与村委间的隔阂,同时也使非体制精英有主导村委选举的机会,村委选举始终处于一个固定的模式,无法得到提升。乡村社会治理仅倚靠一方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多方参与共同配合才是最合理的方式。社会学家帕累托在精英循环理论中,以狐狸和老虎为类比对象,阐述了权力精英与非权力精英的流动循环,但是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二者都参与了日常事务的管理,并通过竞争机制相互促进。新时期如何引导非体制精英共同参与并构建良好的乡村环境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议题。
参考文献:
[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8-66.
[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3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26-153.
[3]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一一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57-158.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6-70.
[5]贺雪峰.乡村的前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5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