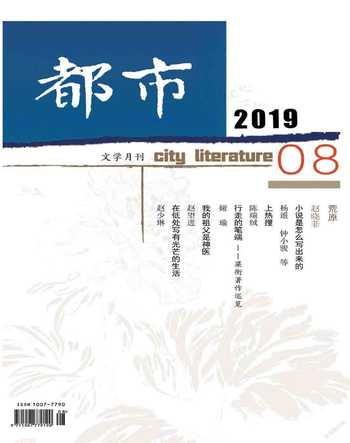内在性的诱惑
刘阶耳
无论“我走上街头”(《置身旷野》),还是“一个牙疼的人在屋子里踱步”(《一个牙疼的人》),诗人宋耀珍由“我”及“人”捕捉“走”的动势,总归将由“天空高远。一个人走着”(《悼念》)的无“我”之境所覆盖。诗人自1993~2013年间与诗神会多种机缘见其诗集《结局或开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如若不曾磊落,情采何以披沥?所以,“一年将尽的月份”及“元旦”不期而至的时序更替,“寒风”凛冽的季候时令,“太阳”落下的“黄昏”及“夜晚”,宋耀珍每每出离自身、“忧心”涌迫、为之恻然的,无非是对转瞬即逝的当下/“现在”所持守的平淡而峻切的追忆,然而这迥非海德格尔“绽出”式的运思习惯所能比拟!诗人藉此舍我其谁的诗学建树,很显然将会昭然若揭,引人唏嘘了。
诗人宋耀珍作诗廿年间,继“新诗潮”(1980年代)之后因多位“诗人之死”而牵动的诗学力量再集结的敏感神经,不止是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大命题李代桃僵般的鼓噪;迄今“乡愁”遍地,俯拾即是,各类“地方性”知识碎片攒聚,脱衣舞般轻浮、自满,虽然带动了“对他人的召唤和罢免”,可“除了对自身形象外没有其他欲望和超越的时候,才能如此充分地实现”“这种迷人的完美的超越”,仿佛“拟像”无穷的运演,似乎已然确信了海德格尔意义上“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但想象“同质化”的窠臼实在是乏善可陈,毕竟:“诗之言说不可漂浮于一种诗歌的风光描绘”。“我在星光下,悄悄披衣,再次背井离乡”(《西里峡谷的夜》)如果说是诗人羁旅(“走”)之思不复堕入“摇啊摇”“找呀找”的恶趣,抑或因“外婆桥”“小朋友”而窃喜,那么独自潜行于生命的“暗夜”的主体,毋宁是在“同一”与“他者”非排斥性的关联中,重申存在担承的职责;也就是讲,面向总体和无限所溢满的存在质问,总之不致因为焦虑从而引入虚无。———海德格尔“向死而在”存在论的设定,遭到二战之后法国思想家的挑战,不啻对我们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宋耀珍不断地与由此及彼的“潜行”相神会的,俨然揭穿了已然破碎、然却欣然把玩的各类所谓的“乡愁”理念自欺欺人的假象,毕竟“在以撕裂并重续了无限之脉络的现在为出发点的对存在的介入中,包含着一种张力和一种挛缩。”他有关“父亲”的慨怀可做如是观。
“我是不准备再归去了/也许,你会因此伤心”,“在异地的大街上/我是一名孤独的诗人”;直斥胸臆,让人感动,可“当我的身影在你的惦记里”,反向缱绻,斗转星移,接着反诘“我心存的最高荣誉”又作何解?是在求得“父亲”的宽恕,还是在向“父亲”献出“祝福”?过往不待,犹来者之可追,宋耀珍《父亲》一诗“对存在的介入”,与将作为主体的我确认联系在一起,为此存在安定感、陌异感及必要的担承的才会在相应的唤醒时,得到妥善的“置放”,因为“自由不是自我否定,而正是凭借他人的相异性,让自身的存在获得宽恕。”这也就是讲,诗人负疚的情绪意向,难能可贵地超逾了本雅明意义上“可技术复制时代”一般艺术品高度“刻奇化”自身的“展览价值”;惟其出自“人之子”自觉的伦理认同下的担当,毋宁在为艺术“此地此刻”的本真灵韵而倾情奉献着什么。
平静而怆痛的《天空》,无疑将宋耀珍与诗神会所把持的尺度予以了有力的阐扬。
该诗计6节,每节四行。开头两节及末节均由“天空空无一物”一句引出,第3、4节该句略有变化,“我”如何如何,“我”看到如何如何,分别出现在各节2、4行,唯第5节由反诘逆转其义:
谁能挣脱大地的羁绊
谁能在梦中愈见天空
使得诗后半部涌现的在“看”、在“凝望”、在“把沙哑的歌/送上天空”的“我”,历久弥坚,意志强悍;不消说,他为他的“大地”和“天空”着色,以至于所谓的“贫瘠”和“苦难”、“灵魂”和“幸福”洵非其“概念”化明确的意指意向所能图解。它们形近“明喻”的修辞格,其实涌迫的是雅各布森意义上以“相邻性”(而非“相似”性的)为历时性取向的“转喻”策略;其中涉及的“说明”与“讲清”的微言大义无非取决于:
隐喻的概念说明了症状的概念(一個能指被另一个关联的能指所取代),转喻的概念则讲清了欲望的起源(通过能指和能指间的组合连接,产生一种把这一过程延伸到未知领域的无限制的扩张感。
然而“我”仍活在“父亲”的惦记里,只是“他转过头来,像望着一个陌生人”———
我没想到,死亡带走了那么多的父亲
如果他们从石头上站起来
如果他们叫嚷着要回来
《和解》)一诗中阴阳相隔陌异的当下/“现在”,“我”与“父亲”意欲和解的邂逅,何尝流于一种乡愿的满足?就列维纳斯意义上由“面孔”呈显的伦理关爱维度而言,其邂逅莫过于一种辩证局面的昭示,这是因为“父亲对儿子的爱实现出与一个他者之唯一性本身的唯一可能的关系”,“每一种爱都必须近似于父亲的爱”。这样的爱欲创造并不“与受造物的自由相矛盾”,父子关系中兼容的“无数的将来”被生产出来的自我,同时既作为世界上的唯一者又作为众兄弟中的一员而实存。……因此自我作为自我就从伦理上转向他者的面容,兄弟关系犹同“博爱”而施予“面容”可辨识的关系本身;主体(被)拣选与平等,亦即他者对我的支配性,也同时造就。而正“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自我来衡量自我责任的程度”,“这当然就证明了……人类自我在兄弟关系中确立,……就使得爱欲性的事物涌向社会生活,”“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并不消失,而是被允诺给和被唤往善良”民胞物与,潜泳涵藻,宋耀珍由平淡的“荒诞”构图,穿越了那把“父亲”与“儿子”分离开的“死亡”的时间性铭记,引向与存在伦理性“和解”的峻切,与其“超逾了对限定者的悬隔”,毋宁敞视着“那写在瞬间内盛开的青春所具有的新颖,伴随着所有那些被体验的青春,已渐趋沉重。”(同前)
宋耀珍的《幻觉》分明也传递着类似的“新颖”与“沉重”。
他的诗所以总散逸着“那白色,那蓄满泪水的语言的芬芳”。(《少女》)
所以,当他“把一枝玫瑰/插在日常生活的花瓶中”,他业已意识到“时髦的田园诗人笔下的乡村/仅是一堆凌乱的意象”,因为他“谨慎地使用比喻”(《在新庄谈美》);又的确不致出乎意料!
抑或从小处讲,譬如他对“眼睛”作为喻体的使用,“像两家破產的银行”(《肖像》),“像两座兵工厂”(《四月》),出奇的想象拼接,一如他的名篇《一个牙疼的人》已经得到不少方家的称誉,在此就不叨扰了。我想发挥的是,当“眼睛”作为本体来使用时,作为循常的“看”的主体,再度践临“遇见”、“发现”之类戏剧性扭结的生活奇遇时,———《大街上》背着巨大的石块“长长的队伍”,被“熟悉人”所引领,处在“十字街头”的诗人“心里纳闷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不经意包含着对西西弗斯式的现代性处境的间离或反讽:是执迷不悟,还是坚韧地自我救赎?诗人旁观者冷眼掠过的多重能指铰链的“想象”厚度,不但是“让它作一次简单的病理记录”(《谈心》),同时还会转变与之神会的笔调,随轻逸的体温简约着繁育生产的丰韵;《叶子》《青花虎》《长篇小说》《往事》《春天》诸篇譬如霁日晴云,清醇健朗,确实都会别开生面。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历来看作美谈,但从庄周“齐万物,等生死”方面讲,儒家济世怀抱岂不也是落入“有待”,不可方物。然而欹正不器亦为仁,揆诸道家大小之辨,免于拘形役使之厄计,同样都似天钧骏发,以期去蔽。关于“玫瑰”,诗人多次慨怀,它可以“在正午的阳光中挺立”(《玫瑰》)所云,也可以是“孤苦的”,“站立在秋风中”,“站立在大地上”,“像盲目的少女终将失却青春”(《歌谣中的玫瑰》),更意味着“纯粹的玫瑰在远处存在着,我的目力不能/到达,我的纯粹也因此成为疑问?”(《空白》);一如诗人曾经诉诸“走”及当下/“现在”存在之介入的想象施为那样,饱满而深切;至若《歌谣中的玫瑰》末节的这般直接慨叹、呼吁:
歌谣中的玫瑰,是生命的玫瑰
是美好的玫瑰,到歌谣中来吧
这是大地上唯一永存的居所
一连串的“命名”翻新,犹同持续的“转喻”,如果参照本雅明有关普鲁斯特、卡夫卡的写作方式的品鉴,宋耀珍相关的“想象”取径的确非同小可。
或者这属于一种“具有挑衅性且喜怒无常的品性”;不但普鲁斯特,就是宋耀珍都喜欢那没完没了的“不是……就是”句式;它的语用属性无非是“从一个行为赖以存在的无数动机这一角度,极尽其详而又毫无生机地展现了这一行为,……透过这些并列的单元而显示出来的,即在知识上是超迈出世的,在审事时又是经受了考验的怀疑论者。”本雅明把这看作是普鲁斯特的“缺陷”与“天才”的齐凑,并归因于不给这“内在性的诱惑”以任何信任。
本着“内在性的诱惑”的宋耀珍如果神笃八荒,那也是通过频频的变化想象“凝眸”的角度,与其获悉想象“能指物”并置之所可以的隐秘。这样的话,其诗俨然接近卡夫卡《诉讼》中的族长———亚伯拉罕表现出“跑堂般的殷勤”那样难言的悲哀了;然而卡夫卡“只会透过形体姿态来理解事物,这个他无法破解的形体姿态就成了寓言中的晦暗之处。”宋耀珍与诗神会却不限于此。
《夏天》所以又不得不提。
它的起句尤其奇崛:“夏天在一枚果子上腐烂”;它的末句又格外霸气:“我侧身走进蓝色的天空”;但我更想追究的是,“大地上的一枚小小的果子”又究竟缘何“置放”在“夏季”这样的时令,然后令“我”陡然从澹远中获得其不平静的“与物神游”豪健的气魄?不消说,“腐烂”一变而为消极修辞的意指意向,岂不正蕴含着“结局”或“开始”的转瞬即逝间的辨证的“运动”?“他强大的精神有尝试自己力量的需要和快乐”,史蒂文斯如是称颂他的精神同道(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赞誉,揆诸宋耀珍一点也不为过。其形式外衣刻意平凡,但却饱含着诗的本质上的华丽。
宋耀珍《叶子》《土豆》《强权》以及《雪》,亦不例外。
一叶知秋,悲哉为气,“具有高怀能吊古,断无名士不悲秋”;不过5行的《叶子》揖别陈词滥调的修为,不能不引以为是!其前3行由外嵌内含的“叶子”、“好听”反复递进中组成;无外乎“叶子”被风粗暴地摘下来扔在地上,“叶子”的骨头被我们的脚踩碎:“声音很好听”。恰恰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反复地踩”。最后2行别出心裁地区别出“叶子”中另一类的当下际遇:“但有些叶子是自己腐烂的/这些死亡不关我们的事”,洵非同一、同质化的“腐烂”,如果必须上扬到“死亡”一侧而作比较的话,其筋骨思理,明显得益于其前3行“叶子”/“好听”反复吟唱邈远的风神气象;相异的时令物候牵涉出的“腐烂”意象,相去甚远,就不遑多言了吧?
计19行的《土豆》中有12行均从“土豆”引领的陈述组成,机智,洒脱,也不遑多言了。
围绕着“把”字句一顺布排的《强权》,更是将类似的话语“配置”推向了极致。它共计86行。其中含“单句”格式的不过8则;其他诗行,句式、句法异常繁复。各则先后堆垛,不拘一格,内在的“语义”牵连有讲对称而成排比之势,但不规则的参差构图又趁机占据了上风;因祈使语气所盘旋的语句主干形似“喻体”;若变换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却又分明属于“本体”辖制的想象领地,怪诞与反讽层出不穷,风格完全是《一个人的牙疼》的翻版,形同日常经验中“恶”的开具的明细清单;而话语祛魅偏偏又完全仰仗“暴力”美学者,甚嚣尘上,结果尽显其饕餮气象。
进而言之,宛若“把蚂蚁吊起来抽打”的《强权》,自然与《叶子》的轻逸、《土豆》的简劲相去甚远;其轻狂,蛮横,好比精心组织的一场轮盘赌,对馥郁的苍凉的“愿景”,———亦即前述所谓的“内在性的诱惑”予以了刻骨的仇视,语言承载想象的“边界”悠悠间得到了充分聒噪式的暴露。这是诗人“牙疼”美学发作后的登峰造极,诚如鲁迅所云:“并不拒惮……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雪》何尝不是这样?
简要地讲,《雪》中间几行“我知道”/“雪不知道”的逆转,于平行“并置”中兼有鲁迅《野草·雪》中对“朔方的雪”/“暖国的雨”迤逦的绎思。开头几行“雪字”连翩而出,不失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原野》奔涌的豪逸。至于首尾敞视的几处“飘落”(“落”)疏密相间的反复重奏,以及排比呈述,又俨然似徐志摩《雪花的快乐》浪漫而多情。而它最后的7行:
我们全部的智慧结合
抵不上一片雪花的重量。现在
我在屋子里注视着它,它飘落在
它的冬天里,只将一种感觉落在我的心上我体验到的已经不是一场真正的雪
我所写的诗篇也不能像一片雪花
走进冬天
诚如所云,他所“感觉”到的、“写下的”与“飘落”的,其实和所谓的时令物候全然无干。他的想象的生色活香,究天人之际,而成自家之言。他一如在他的“诞生地”(他一首诗的标题,亦标劲)担承着他的“存在”,他的“尖锐”,从“目睹真实的事物”中,从“已看到幻觉中的村庄”边,铭记着希望的“箴言”,因为———
一切被人视为虚幻的,必是真实的,
一切被人不忍抛却的,必是虚幻的。
“每一个有价值的灵魂都渴望过极致生活。”
佩索阿如是说。宋耀珍亦如此。
因为“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活出自己的生活”的极致,一如宋耀珍不可抵御的“内在性的诱惑”那样,总会在被延迟的焦虑中,产生令人赞叹的违抗,但“出现在这一超越之终点的,是一个渴求强力、渴望将强力神化并因此注定孤独的人。”列维纳斯又如是说。宋耀珍与诗神会的旅次见闻,概莫能外,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