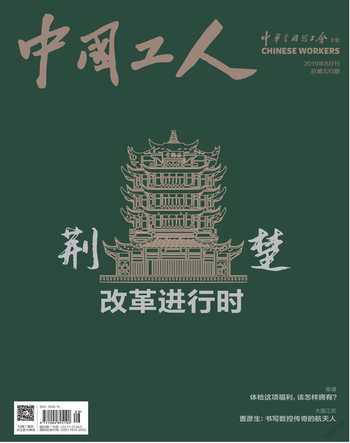为防文学放歌
阿莹

我曾经为话剧《秦岭深处》写过一篇创作谈,标题就是《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军工情结》。当我那天接到一部凝结着军工系统文学新人的作品集,沉甸甸的,墨香浓郁,心里便涌起一阵阵悸动,沉淀于脑海深处的记忆便一幕幕闪现出来,躲在厂房角落写诗作文的情形也清晰得如昨天一般了。
记得我在十八岁那年的春天,走進了古城东郊的一家兵器企业,吞吐铜坯的轧机,咣当轰隆的冲床,热浪扑面的退火炉,灯火通明的检验台……便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些闪烁着黄金般光泽的弹药筒,便浓缩成了我笔下永远的字符。
我是被军工人的生命张力所感染而开始业余文学创作的。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趴在窄小的工作室里,伴随着叮叮咣咣的机械碰撞声,一笔一画描写着满身油污的工友和披着蓝大褂的师傅,体会着他们的酸甜苦辣,感觉着他们的爱恨情仇。即使后来离开了那个企业,每每走过军工单位的大门,心里就想进去看个究竟,想知道那导弹、那飞机、那雷达今日的状态;每每与军工兄弟在噪杂的小店里划拳把盅,大碗菜端上来,筷子没动几下,便想脱掉衣服一醉方休;如今人们已经习惯用计算机敲打文稿了,对大大小小的印刷体已经麻木,没有了奇妙的感觉,而当年我是多么渴望那歪歪扭扭的手书能够变成铅字,至今我还记得处女作在刊物发表时奔走相告的情形。
那时候我常常吃过晚饭便要赶回厂里,躲在一间小屋里,趴在一张小桌上,舞文弄墨爬格子,从晚霞褪尽,到满天星斗,有时到太阳露头,却也一点没有疲倦,天刚亮钉好稿件就骑上自行车,进城给编辑部老师送去了;或是装进信封,贴上两张邮票,投进墨绿的邮筒,常常半天盯着还不.愿离开,满满的期待便萦绕在脑际了。所以,那时我非常渴望能有个园地展示军工人的文学耕耘。记得曾经有过一本反映军工人创作的《神剑》杂志,给爱好文学的军工人带来诸多憧憬,尽管那个刊物昙花一现,但薄薄的杂志带给人的激励持久地留在了记忆里。
然而,月真的很无奈,我已经懵懵懂懂走过好多单位,经历了难以言状的磨炼,面对许多事物也变得迟钝深沉了。但军工情结却是我不变的情怀,任何时候谈起军工,谈起国防装备我就像打了鸡血,常常会卖弄地把支离破碎的军工见闻一股脑儿显摆出来,惹得满屋人啧啧赞叹,心里的虚荣也就得到了满足。
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我即使离开军工企业多年,依然与基层的军工人保持着热络的联系,一年里若是没有跟他们见面坐坐,喝杯酒聊聊天,心里便感觉空落落的。有人半开玩笑说,现在你们还能有多少共同语言,是那些人找你有事要办吧?我说不是他们有事要找我,而是我的心灵需要他们的抚慰,思维需要他们的滋润。千万别以为他们说话粗俗冷噌,也别以为他们玩笑缺少分寸,其中的智慧和爱怜最为受用。一句话,与他们面对面,我感到踏实!
但是,匆匆掠过即将出版的《秦岭深处》这部书稿章章页页,便感觉有股热浪扑面,一个个字符就像安装了发射药的炮弹,生龙活虎地演绎起神秘的故事——有来自生产一线的诗作,那是机床边的浅吟,是试验场的低唱,是计算机里的音符,散发着并不遥远的豪迈和柔情;有来自工厂车间的美文,浸透着油污和汗水,如同经历了硝烟洗礼的捷报,可以感觉到苦涩和渴望;而最为新鲜的作品,是从厂房墙报上摘录的行行字符,吐着火,流着汗,散发着浓浓的机油味,让我恍如回到了青春岁月。
这些从生产线上流淌出来的作品,蕴含着军工人特有的质朴,任何有良知的人面对这些文字都会肃然起敬。尽管有些作品还显得有些稚嫩,而稚嫩正是卓越的萌芽,是作品真挚的活力,所有的成熟都是从稚嫩走来的啊。毋庸置疑,随着岁月年轮的增添,我们的军工人一定会愈写愈老辣,一定会为文坛增添一道道靓丽。
所以,我们应该为呵护军工文学的国防工会鼓掌!也应该为创造了卓越的军工人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