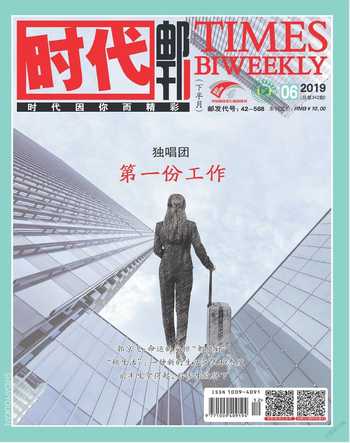山长水阔抵不过心怀微光
2019-09-10 07:22:44汪微微
时代邮刊·下半月 2019年6期
汪微微
我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写诗的。这一年,成绩并不算差的我留级了,因为父亲认为,盖房子打地基最重要,养孩子也一样,多上一年,学得自然更扎实。再学一遍自认为都会的东西,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于是,我有了大把的课外时间。
邻居老伯是收废品的,除了破铜烂铁之外,他还收过期的报刊和惨遭遗弃的书籍。我一得空便钻到老伯家,扒拉着找自己喜欢的书刊。路遥的《人生》便是我在这里挖出来的。那些天,吃饭、走路、上厕所我都捧着这本书,虽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爱情和人生,但阅读时不由自主投入其中的惦念、愤懑和悲悯,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阅读,让那些我好奇的故事和向往的人,像萤火虫一样晕出光来,我感到内心变得丰富又坦荡,饱满且柔软。我喜欢上那种书面的表达,开始有倾诉的欲望,我开始写诗,准确地说是通俗易懂的打油诗。在左邻右舍不遗余力地口口相传中,所有人都喊我“诗人”。我无所谓,与其说那是个不懂羞耻的年纪,不如說心怀微光的人总是勇敢得鲁莽。
直到有一天,我的文章出现在很多人家都会订阅的日报上。父亲装作很随意的样子说:“这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一边心虚地接过报纸,一边瞟了一眼父亲,他的脸上涨满了绷不住的期待。得知文章是我写的时,父亲只点了点头就出了家门。我抬头看见夕阳下他背影里深埋的喜悦,像塌方似的晚霞轰然而至,铺天盖地地渲染了整个天空。
多年后,我走过山长水阔的世界,写下清晰光明的文字,依然坚信老伯家堆满废旧书刊的院落和父亲那个塌方的背影,皆是我人生伊始最大的奖赏。
猜你喜欢
光明少年(2023年8期)2023-04-29 13:55:53
小学生作文(低年级适用)(2022年11期)2022-12-02 09:02:30
社会科学动态(2022年2期)2022-02-12 10:24:24
新世纪智能(高一语文)(2021年3期)2021-07-16 08:30:20
小资CHIC!ELEGANCE(2019年29期)2019-09-12 08:12:42
中国外汇(2019年6期)2019-07-13 05:44:02
小资CHIC!ELEGANCE(2019年14期)2019-05-20 02:51:14
学生天地(2017年9期)2017-05-17 05:50:12
草原歌声(2017年2期)2017-04-28 08:16:07
快乐语文(2016年10期)2016-11-07 09:44:46